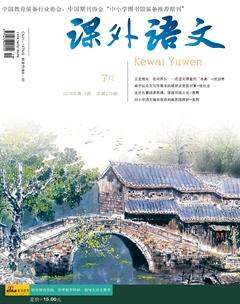庭中枇杷樹,何人所手植
【摘要】從文章結構和寫作手法分析,庭中枇杷樹為歸有光妻子所種更契合作者在文中抒發出的情感——對逝去妻子的懷念和功業未就的慚愧之情,同時也很好地解釋了作者在文末把枇杷樹一句單獨成段的結構意圖。
【關鍵詞】枇杷樹;文章結構;寫作手法;思念與愧疚
【中圖分類號】G623 【文獻標識碼】A
對于《項脊軒志》一文最后一段“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的翻譯,目前的教輔資料大多翻譯為“院中有棵批杷樹,是我妻子去世那年親手種植的”。此翻譯對于句中枇杷樹是何人所植的解釋是模棱兩可的,并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但枇杷樹是何人所植的確對于理解文章的主旨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文本內容、文章結構和作者相關資料的分析,本文認為庭中之枇杷樹應是歸有光的亡妻魏氏所植。
一、從文章結構分析
文中最后兩段無論是“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幾學書” “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等詳細追憶夫妻兩人生活中溫馨、和諧的句子,還是最后一段枇杷樹亭亭如蓋的描寫,這些都是歸有光回憶起與妻子生活的點點滴滴,抒發出作者對于亡妻的無限思念。那么既然兩段的內容相同,似乎沒有必要把枇杷樹一句單獨成段,而作者卻偏偏另起一段,顯然除了與上文所寫一樣追憶亡妻,抒發對亡妻的思念之情,作者還有更深的含義。
歸有光在另外一篇回憶妻子魏氏的文章《請敕歌命事略》中寫道:(先妻)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從妻子鼓勵的話語來看,妻子對歸有光的仕途是充滿信心的。翻看歸有光的年譜,他在20歲時中秀才,28歲時妻子病故,35歲中舉人,也就是說在補敘《項脊軒志》后兩段時歸有光仍然只是秀才,這與妻子的殷切期望還相去甚遠,怎能不心生慚愧之情?這種對于自己功業未就,未能達到逝去親人期望的慚愧之情貫穿于全文對于逝去的至親的思念之中,與全文“亦多可悲”的情感基調契合。
若枇杷樹為歸有光所種,只能表達出歸有光對逝去已久的妻子的思念,而另外一層深意卻未能體現。若枇杷樹為妻子所種,兩種情感的交織便有了合理的解釋——因為枇杷樹蘊含著妻子對歸有光的美好期盼。枇杷樹與院里雜植的蘭桂竹木不同,枇杷樹不僅能如蘭桂一般開花,而且還能結果,枇杷樹成熟時滿樹金黃,于是妻子在庭中種下一株枇杷樹,寄寓丈夫有日能像枇杷樹一樣“開花結果”,家族枝繁葉茂。睹物思人,歸有光看到妻子當年種下滿載希望的枇杷樹,如今已亭亭如蓋,想到自己而立之年仍功業未就,除了心頭涌起對亡妻的無限思念,也夾雜著自己多年過去仍未能實現亡妻美好希冀的慚愧之情,各種復雜滋味怎能不讓人悲從中來?
二、從寫作手法分析
黃犁洲在《張節母葉孺人墓志銘》中寫道:予讀震川(歸有光)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這表明歸有光善于通過人物生活中的細事來描寫人物,這一特點在《項脊軒志》中也有所體現,且看歸有光在回憶已逝親人的句段:“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大母過余曰……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妻)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這些句子無一例外是圍繞母親、祖母、妻子先前生活的言行舉止而展開的,皆為她們生活小事的記錄,描寫的主語是已逝的親人。如果枇杷樹是歸有光所種,那么“吾妻死之年”則變成了修飾歸有光植樹的時間狀語,這句話描寫的重點則變為了歸有光為紀念亡妻而植樹,人物的主次輕重關系就顛倒了,這顯然不是歸有光慣常的“每以一二細事見之”的寫作手法。
再者,文中寫親人的思念之情皆由一個具體的場景觸發,觸景而生情。當嫗說“某所,而母立于”時,對母親“叩門問食”的慈愛回憶頓時涌上心;瞻顧遺跡,祖母對自己的勉勵之景如在昨日,一幕幕呈現眼前。歸有光的這些描寫畫面感十足,描寫人物的鏡頭很真實,正如文中所說“如在昨日”,如在目前。根據前文行文習慣,歸有光對妻子的回憶應該依托一個具體的場景展開。當歸有光見到枇杷樹時,見物如見人,妻子當年植樹的場景便如泉涌般展現眼前,雖然下文沒有展開具體的細節描寫,但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而那些年與妻子生活的場景也歷歷在目。如果是歸有光所種,顯然沒有這樣豐富的畫面感和現場感。
基于寫作手法和《項脊軒志》文章結構的分析,枇杷樹應該是歸有光妻子所植,即“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枇杷樹為妻子所植的解釋既表現了歸有光對逝去妻子的深情和深深的懷念,睹物思人,同時也包含了歸有光對于自己功業未就,未能實現親人殷切期盼的慚愧之情。
作者簡介:戴泳洪,1993年生,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2017屆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語文學科教學。
(編輯:張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