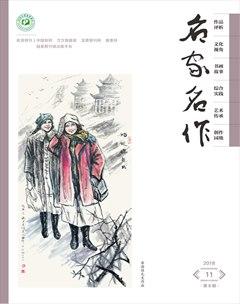論劉創詩劇《楚鳳飛騰兮》的意象圖式及審美空間
權曉燕 任先大
詩劇不僅具有詩歌的韻律和節奏,又具有戲劇的基本特征。“詩作為詩人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審美融合體,一方面既是時代、歷史的投影,另一方面又必然是詩人內心的寫真”[1],內含文本內容的蘊藉性與情感表現的內在張力。而“詩劇即戲劇體詩[2],是敘事詩與抒情詩的結合,其本質特征是詩與戲劇的有機融合,它以戲劇性為本體,將敘事詩的客觀性與抒情詩的主觀性、主體性熔鑄為嶄新的獨立的詩的第三種體裁。”[3]如此,詩歌所具有的詩性與戲劇所具有的戲劇特征都在“第三種”體裁中得以實現。意象在詩歌創作中能夠表現作家情感,實現文本意義,是詩人表現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載體。同樣,意象是詩劇文本表現的核心,作家利用豐富的想象與巧妙的創作結構在獨立的意象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由此形成獨特的意象圖式。詩劇《楚鳳飛騰兮》(2017年第11期《海外文摘》,劉創)以自身情感為主線,對各種不同意象進行組合,以此構建不同的畫面場景,進而傳達文本主旨。由此也可看出,文本主旨的傳達依賴于意象圖式的建立。
意象圖式屬于認知語言學的范疇,最初由Lakoff和Johnson提出,它依賴于我們對身體經驗、外在世界的基本認知,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構型。這就意味著意象圖式與我們的行為、身體、感覺、知覺活動緊密相連,如Johnson認為意象圖式乃“孕于身體的圖式”。他特別強調意象圖式的動態特征,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知會時刻發生變化,故而將其嚴格地定義為“具有類似意象的抽象結構和功能的一種動態模式”。在分析具體詩作顯現的意象圖式時,要熟知文本主要意象及輔助意象,意象的運用與文本主旨的傳達、意境的塑造緊密相連,甚至審美空間的構建都依賴于意象。文本對以主要意象為中心的多種意象的編碼與組合正是意象圖式的具體運用,它使文本的畫面感更為強烈。詩劇《楚鳳飛騰兮》主要涉及以下幾種主要意象圖式:始源—路徑—目標圖式,中心—邊緣圖式,容器意象圖式,系聯圖式。這四種意象圖式以“鳳鳥”為中心意象,通過橫向說明與縱向闡釋生成以上四種基本意向圖式。從審美角度而言,每種意象圖式自成一體,又可相互印證。意象圖式具有的體驗性、動態性、抽象性、象征性等特征構成不同的審美畫面,審美畫面的融合與交錯形成以“鳳鳥”為中心的審美空間。
一、 始源—路徑—目標意象圖式與色彩構圖之美
在客觀現實中,人類活動大都有其始源、過程及結果,也就是最終的目的地或想要達到的目標,如從家中去學校,或者從一個目的地到另一個地方,那么兩端正是一段旅程開始和結束的地方,正如人類的生命從降生時開始,到死亡結束,中間所經歷的就是人生的旅程。這正是現實世界中始源—路徑—目標圖式的真實表達。在詩劇《楚鳳飛騰兮》中,“百鳥朝鳳”正是楚之精神與信仰的緣起,“鳳鳥”的目標是等待新生,在崛起與新生之間是鳳鳥的成長過程。由此,“百鳥朝鳳—鳳的成長與變化—涅槃重生”構成始源—路徑—目標意象圖式,這一圖式本身說明鳳鳥的成長變化之路,由此映射出楚之精神文化的緣起與成長。
楚之精神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不僅需要漫長的時間,更需要楚文化的滲透與楚人九死未悔的浪漫品格。在楚文化中,最值得繼承和發揚的正是艱苦奮斗、九死未悔的精神,這是實現最終目標必要的經歷。“鳳凰涅槃”重生,象征楚之精神的綿長悠遠,實現這一目標楚人要擁有艱苦奮斗、九死未悔的執著和勇氣,這恰好與鳳鳥的成長之路相對應。
那么,作家又是如何在構筑意象圖式的同時體現文本的色彩構圖呢?詩劇中作家對意象特征進行了分析,從而形成色彩之間的交錯配合。在序幕“百鳥朝鳳”中,作家注重對審美場景的建構,又時刻關注意象本身具有的特征,二者的結合共同完成對審美場景的建構。如:“有鳳自遠方來/楚國人不亦樂乎/他們讓鳳鳥、彩虹/以及繽紛的花朵在一起/鳳在那個清晨飛臨/讓多少楚國人臉上泛起紅暈。”其中,涉及的意象有鳳鳥、彩虹、繽紛的花朵等等。這些意象本身就有美感,如彩虹具有七種色彩,繽紛的花朵也意味著多種色彩。同時“楚國人臉上泛起紅暈”,也有色彩渲染的痕跡。不同色彩的交相輝映正是楚人內心幸福之感的真實寫照。后來“一只在楚國土生土長的孤鳥留了下來/這只以楚國為家的鳳鳥/以高翔之羽翼,亮出一面不褪色的/楚國旗幟”,這正是楚之精神的緣起,同樣楚人以鳳鳥作為“楚國旗幟”,“不褪色”意味著楚國精神不滅,象征楚國精神悠遠綿長。
另外,作家在“風絕云霓”這一場中主要講述楚國音樂,即楚調。在詩人眼中“楚調如綿綿細雨”,溫和而充滿力量。它與“鳳鳥”“宋玉”和“采桑女”共同刻畫出一幅唯美動人的鳳鳥琴音圖。同時,作家對自然環境的細致描寫為其增添了獨有的意境之美。在詩作中作家對自然環境的描寫充滿詩的韻味,如:“旭日東升,開始照亮屋脊/萬道霞光涌動在她的身體里/輕輕的音樂,變得多么璀璨奪目/果園里長著零星的野草/燕雀紛紛飛離/只有她的影子還那么長。”這體現了自然環境與楚調之間的融合,實現了人、音樂、環境三者之間的互動與融合,又突出了審美畫面所蘊含的色彩之美。
二、中心—邊緣意象圖式與結構的動態之美
從身體經驗層面來講,我們的身體被分為中心部分和邊緣成分,中心部分指人體的軀干和內臟,而邊緣則指人體其他部分,如手、腳、頭發等等;從結構層面來講,則分為中心及邊緣,邊緣依賴于中心存在,而并非相反。這些體驗與感知投射到其他領域就形成了中心—邊緣意象圖式。
在詩劇《楚鳳飛騰兮》中,鳳凰意象是作家表現的意象中心,其他意象在此基礎上產生。文本中,“鳳鳥”作為意象圖騰,代表楚,又隱喻楚之精神;“鳳鳥”邊緣存在的其他物象則以其為中心存在。
此圖正是詩劇中心—邊緣圖式的體現和表征。在這一圖式中,鳳鳥及其隱喻意義作為圖式中心,其他意象及隱喻意義由其生發,并圍繞圖式中心存在,正說明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對意象的把控,又說明楚國的發展壯大需要更多具有價值和內涵的事物的補充和豐富,更需九死未悔的浪漫品格,如詩句中所說“多少人都已涉江而過/只有屈原,涉江一輩子”,這種不向命運妥協、不畏生死的決心與鳳凰涅槃時的決心和勇氣相一致。這正是“鳳凰意象”作為符號中心傳達的隱喻精神,為讀者審美閱讀營造了極大的空間。
從文本細節處著手,也可印證這一圖式。在文本中并非只存在一種意象,“鳳鳥”作為意象中心,是作家表現的核心,要體現結構上的變化與動態特征就必須與其他具體意象配合,如“青銅器”“雪花”“爐火”“糧倉”等等。同時,“鳳鳥”作為意象中心其身份和視角在不斷發生變化,時而作為楚本身,時而作為旁觀者。如“鳳鳥清清楚楚地看見”“鳳鳥驚異地發現/范蠡和西施對視的頃刻/一粒水稻變成一千棵水稻/一萬棵水稻”等等。“鳳鳥”則以旁觀者的視角來看楚。由此“鳳鳥”身份上的轉變使讀者在閱讀時的角度時刻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我們可理解為文本意義上的動態之美。
不僅如此,文本結構也能體現這種動態之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以戲劇的方式展開,具有獨特性,以符號化、宏大敘事的方式展開對楚之精神的敘述。在這一過程中,“鳳鳥”作為意象中心,其隱喻的意義是不斷變化的。由此文本結構也呈現出動態變化的特征。作家在表現這種宏大敘事時并非直接從大處著手,而是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來表現“楚之精神”這一主題。“小”即鳳凰圖騰,“大”即楚之精神。作家通過這種以小見大的方式使文本的情感表現得更為細膩。
三、容器意象圖式與意境的祥和之美
在人們的認知領域中容器代表中空,它可以容納其他東西,即“容器—內容”,表示“在……里”。它通過人對自身的認識得以建立,人體本身就是一個容器,在人體之內有各種臟器。生活中許多事物的出現正是根據這一原理生產出來的。如房子、車子等,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具象的容器,人們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對其進行填充,即“內容”。在此處“容器—內容”圖式是建立于現實意義之上。而在詩劇《楚鳳飛騰兮》則是對這一圖式的抽象反映。
鳳鳥意象形成的意義領域自成容器,它可以承載詩劇中“鳳鳥”意象的象征意義。那么,楚鳳的象征意義則為內容,形成抽象意義上的“容器—內容”。作家在文本中以鳳鳥為原型,將其與楚國相聯系,鳳鳥的成長變化對應楚國的成長與發展。鳳凰象征吉祥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因素。楚之精神、文化中不僅有九死未悔的浪漫品格,同時其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這正是文本意象的投射,形成容器意象圖式。
從這一圖式出發,以鳳鳥為中心并與其他意象相結合塑造出祥和的審美意境。在現代詩劇中,詩性體現依賴于意象的選擇和運用以及對意境的塑造。從詩性角度來看,意境的塑造離不開意象,不同意象的組合可以營造不同的意境畫面。從戲劇性的角度來看,意境與情境密切相關。詩劇中每一獨立劇場塑造的內容有所區別,并且每一劇場的畫面會時刻發生變化,這正是其動態性的體現。因此,意境的構造與結構的動態變化是相輔相成的。
詩劇第一場“鳳凰于飛”,作家塑造的是農耕生活場景,文中這樣寫道:“春天來臨/楚國人開始筑壩/他們引水灌溉良田/楚國的湖泊蛙聲遼闊/每個人的心思都是透明的/好幾條魚到達岸邊/鼓動潺潺的水聲/看著姑娘們白皙的胸脯,圓潤的臀/楚國的禾株就開始受孕。”在這一段文字中,有對時令、楚人、環境的勾勒,抽象意義上的鳳鳥已化為現實中的楚國。楚人在此安居樂業,對未來生活充滿信心和希望。“湖泊”“蛙聲”“魚兒”“禾株”等具體意象構成一幅祥和的畫面,“禾株受孕”則塑造出動態的生活場景,可見作者用詞之巧妙。在詩劇創作中,修辭手法的運用可以豐富文本意義,詩體語言要凝練、生動而又富有生命力,必須善用修辭手法。“修辭使語言展現出一種內斂、含蓄、曲折的藝術效果,同時又使語言的結構布局更為復雜化,這就避免了語言表述和情緒表現的直線傾瀉,為理性思維的滲透奠定了基礎。”[4]在文本中,作家正是利用擬人的修辭手法表現“禾株受孕”的動態畫面,也蘊藏著鳳凰意象的象征之美。
另外,在“鳳引九雛”這一節中,作家寫道:“在楚國出生的小鳳鳥/遠離塵囂,細細的羽毛/可以溫暖我們的視線和臉頰/看起來多么自由/它們讓我想起做仁愛的時光/以及從先祖那里遺傳獲得的靈感。”此處不同意象之間的相互交錯構成的意義場景更具有祥和之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語言細膩、情感豐富,所用的修飾語大都以體現希望、美好為主。“鳳臨方城”中,“鳳臨方城/仿如一只迷途羔羊/一轉眼便失去了蹤跡”。鳳鳥的迷失象征楚人在戰爭中的迷失與迷茫。“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又暗含作家對鳳鳥甚至對楚國的期望。信仰不滅,楚國的旗幟將不會褪色。
四、系聯圖式與“鳳凰”意象的象征之美
Lakoff 和 Johnson對意象圖式解讀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三種基本意象圖式,并且從身體經驗、結構成分、基本邏輯、隱喻等方面對其進行界定。從隱喻角度來講,他認為社會與人際之間往往具有某種關系,我們可以“建立關系”,也會有“家族關系”,如此關系雙方是兩個基本實體,二者可以獨立存在,但又具有某種聯系。比如,母親和嬰孩,人們將二者之間定義為血緣關系。
首先從文本整體出發,《楚鳳飛騰兮》中的“鳳鳥”是中心意象,也是作家論述的中心,鳳鳥所歸之處就是楚之精神到達之處。
鳳凰意象與楚之精神、信仰、楚人之間看似并無直接關聯,但“鳳凰”作為詩劇的意象核心,被作家賦予了基本的內涵,這一內涵與“楚國”這一實體相聯系,那么在“鳳凰”與“楚國”之間被詩人建立了某種聯系,建立了以“鳳鳥”為中心,以楚為本體的系聯圖式。詩人相信“鳳凰涅槃”意味新生命的開始,代表對未來的期望。作家在文中這樣寫道:“他們清晰地感覺到身體的異樣/心底有翅膀慢慢長出來/升騰的力量不可遏制。”這樣的力量究竟是何種力量,而這種力量即將噴薄而出的動力又是什么?正是“心藏翅膀”的向往和對未來的憧憬。
在文中,我們多次提到中心意象“鳳鳥”,中心意象及其象征意義的生成不僅依賴于作家的自身情感,又注重對理性的把握,反之文本將成為情感的宣泄。也就是說“創作富有藝術感染力的現代詩劇不僅要重視感性,還需重拾理性,跳出情緒傾瀉的漩渦”[5]。在詩劇《楚鳳飛騰兮》中,作家表現對楚國精神文化傳承的愿望時,并未采用一般的情感宣泄方式,而是將自身期盼訴諸于“鳳鳥”意象之上,通過尋找“客觀對應物”傳遞情感,而客觀對應物又與表達主旨之間具有內在聯系。由此意象組合、結構安排、情感表達之間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從文本部分出發,包含序幕、尾聲以及主要劇場。在文本主要劇場中,每一場內容詩劇都與楚有關,并有其特定的意義范疇,如“鳳凰于飛”象征楚國農耕之景,“風絕云霓”映射“楚之音樂”,“鳳鳥之文”指稱楚之文道,“鳳凰在笯”象征楚之困境,“鳳臨方城”映射楚之迷途,“鳳鳴楚歌”映射楚歌悲壯之美,“鳳凰涅槃”意味楚之重生。在七個主要劇場中,作家把“鳳鳥”與“楚”作為中心,不僅是對我們上一圖式的再次印證,同時又在意象與象征義、隱喻義之間建立了聯系,直接體現詩劇具有的象征之美。
《楚鳳飛騰兮》作為現代詩劇創作,不僅體現出現代詩劇具有的詩性、戲劇性,又具有抒情性與敘事性。作家以“鳳鳥”為中心,以詩化語言、戲劇性的結構對“楚文化”這一符號展開敘述。作家通過對“鳳鳥”這一中心意象及與其他意象的分析與重組,形成四個主要意象圖式。通過對意象圖式的分析進一步認識詩劇《楚鳳飛騰兮》具有的四種審美畫面。由此可見,詩劇中意象并非單純的意象,它與作家的審美情感緊密聯系,對表現文本主旨具有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吳曉. 槐華詩歌的藝術精神與審美空間[J].詩探索,1994(4):90-91.
[2]19世紀以前西方戲劇史中,戲劇大都以詩的樣式進行書寫,并被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別林斯基、維科等人稱為“戲劇詩歌”“戲劇體詩”。
[3]陳達紅. 中國現代詩劇審美藝術研究[D].福建師范大學,2006(1).
[4]董卉川.論中國現代詩劇的修辭藝術[J].齊魯學刊,2016(6):148.
[5]董卉川.論中國現代詩劇的意象藝術[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61(6):60.
作者簡介:權曉燕(1994—),女,陜西渭南人,湖南理工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任先大(1966—),男,湖南理工學院教授。
作者單位:湖南理工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