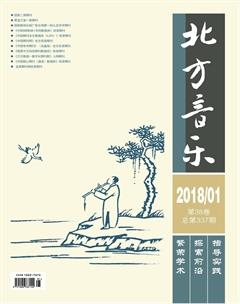滄源佤族民歌音樂形態(tài)特征研究
【摘要】佤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作為我國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佤族長期處于一種落后封閉的社會環(huán)境狀態(tài)。相對原始的生存環(huán)境,造就了佤族獨具特色的民族音樂形態(tài),尤其是佤族傳統(tǒng)民歌,原始、古樸、單純的氣息比較濃郁。本文針對較為原始的佤族民歌特征,簡要分析了滄源佤族民歌音樂形態(tài)特征。
【關(guān)鍵詞】滄源佤族;民歌音樂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作為佤族音樂文化重要材料,滄源佤族民歌旋律較為單純,音域較窄,曲式結(jié)構(gòu)、節(jié)奏節(jié)拍、調(diào)式調(diào)性等散發(fā)出古樸、單純、自然的原始?xì)庀ⅰ?/p>
一、滄源佤族的歷史淵源
佤族,中國少數(shù)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南部的山區(qū)與半山區(qū),滄源、 瀾滄、 孟連、 雙江、鎮(zhèn)康等縣佤族人口居多,另外,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傣族西雙版納自治州境內(nèi)也有一些佤族人民居住。佤族有自己的語言,過去佤族沒有文字,處于一種較為原始的生存狀態(tài)。由于佤族人民生活在邊遠(yuǎn)山區(qū),交通阻隔,與漢民族文化交流比較少,所以,佤族沒有文字傳統(tǒng),佤族族源的歷史也不可考究。根據(jù)唐代以后漢族人民的記載,佤族人民的主要生活來源就是采集和狩獵,當(dāng)時部分佤族人民也有過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萌芽階段,到了明清時期,一些地區(qū)的佤族人民,逐步從采集狩獵的生活方式,過渡到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生活方式。在20世紀(jì)50年代之前,佤族人民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主要分為三種,一種是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經(jīng)濟(jì),一種是原始公社經(jīng)濟(jì)模式,一種是封建領(lǐng)主社會經(jīng)濟(jì)模式。佤族傳統(tǒng)的宗教信仰就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人們崇拜 “木依吉”, 相信萬物有靈,并將“木依吉”看作是萬物的神靈。除了原始自然崇拜之外,自20世紀(jì)以來,也有部分佤族人民信仰基督教或佛教。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佤族雖然沒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佤族人民卻創(chuàng)作了豐富的民間音樂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中,佤族人民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美術(shù)、音樂、舞蹈等歷史文化遺產(chǎn)極其豐富,尤其是佤族的民間歌舞,佤族民歌種類比較豐富,勞動歌、習(xí)俗歌、情歌、獵頭歌、愛情歌、山歌種類十分豐富,佤族民歌在我國原生態(tài)民間藝術(shù)中占據(jù)重要地位。
二、滄源佤族民歌音樂旋律形態(tài)特征分析
(一)滄源佤族民歌音樂中的核心音程
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受民族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環(huán)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各民族不僅有自己獨特的音樂文化表演形式,音樂風(fēng)格也有很大不同,雖然許多民族的民族音樂都使用相同五聲音階,然而,由于各民族方言不同,語言表達(dá)發(fā)音方式不同,所以,民歌音樂表現(xiàn)形態(tài)也會有所不同。其旋律進(jìn)行中的骨干音,特定的終止式,裝飾骨干音的方式,旋律特色,核心音級、裝飾音等也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特征。滄源佤族民歌核心音程是以四、五度音程為主,兩個旋律音程6—3 或 6—2進(jìn)行,在旋律中,以原位或轉(zhuǎn)位方式出現(xiàn)。滄源佤族民歌構(gòu)成約有一半以上是612 或 613 三音列,這兩個核心音程幾乎貫穿完整的羽調(diào)式民歌歌曲始終。其他音主要起到填充與裝飾這個音程的作用。例如民歌《SI VOG GAH NDING》,主要是采用612 三音列構(gòu)成,具有羽調(diào)式的色彩特征,并且結(jié)束也落于羽音上。這首歌曲的核心音程是歌曲開始處出現(xiàn)的四度大跳,填充完這個音程內(nèi)部之后,整首歌曲又下行回落至 B 音上,在 B—E 或者 E—B 的基礎(chǔ)上,建構(gòu)出來比較完整的歌曲。
在我國傳統(tǒng)音樂中,類似兩、三個音構(gòu)成的音樂也比較多,從人類發(fā)展的角度看,也體現(xiàn)了人類音樂的最初形態(tài),一張嗓子唱出完整音階,對于古人來說很難做到。滄源佤族民歌中,二音、三音或四音音樂比較多,這與佤族人民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地處山區(qū),缺少與外界交流,交通閉塞、經(jīng)濟(jì)落后等原因,不僅影響者佤族的文化發(fā)展,也影響著佤族人民音樂藝術(shù)的進(jìn)步。當(dāng)然,這也是佤族民歌之所以能夠保持原始風(fēng)貌的主要因素。在滄源佤族民歌中,雖然也有許多五聲音階構(gòu)成的旋律,但是,這些旋律大部分是從二音、三音音樂發(fā)展而來。佤族民歌旋律的基本特征,就是這些原始的二音、三音音樂構(gòu)建。我們分析這些原始的五聲音階民歌,可以看出旋律進(jìn)行的核心仍然是四、五度音程。例如《EEB BID DAEH MAI SI NBOU》,每兩個小節(jié)形成一個樂匯,D—A 兩個音是旋律的核心音程,第二小節(jié)結(jié)尾處都用相同的 D—A 的下滑, D音下滑至 A 音之前,對 D 音進(jìn)行上方裝飾,形成核心音程的轉(zhuǎn)位。在第三小節(jié)上行音階中,D 音再次被推出,到了第四小節(jié),又回到了第二小節(jié)相同的音節(jié),末尾下滑至 A 音。隨后,又從A 音下跳至 D 音與一、二小節(jié)相似,第五、六小節(jié)再次下跳至低一個八度 A 音,由 A 音經(jīng)過 C 音后,第七、八小節(jié)又到達(dá) D 音,采用相同的方式結(jié)束。在旋律中,核心音程以不同的風(fēng)貌呈現(xiàn),即充分發(fā)揮了骨架支撐作用,有時候還隱藏于其他音裝飾之中,給人一種回味無窮之感。
(二)滄源佤族民歌音樂中的旋幅
在歌曲旋律中,音程在最高音與最低音之間的變化就是旋幅。由于佤族民歌屬于原生態(tài),多數(shù)為自然人聲演唱,所以,佤族民歌的旋幅都比較窄,許多歌曲都是一個八度,當(dāng)然,也有十度、十一度的歌曲,除音域較窄外,佤族民歌音區(qū)偏低,旋律進(jìn)行多數(shù)是級進(jìn)下行,民歌的旋幅都比較窄。
(三)滄源佤族民歌音樂中的裝飾音
在滄源佤族民歌中,許多民歌的音樂表現(xiàn)形態(tài)大多以原始風(fēng)貌呈現(xiàn),對音樂在流動的過程中的腔化處理不太重視,許多民歌的音樂旋律比較質(zhì)樸,使用裝飾音的民歌只有極少數(shù)。在滄源佤族民歌中,使用最多的裝飾音就是前倚音與下滑音,一般情況下,在歌曲的結(jié)束處出現(xiàn)下滑音。使用上波音的時候更少,簡潔質(zhì)樸的旋律,更有利于表現(xiàn)佤族民歌古樸原始的風(fēng)貌。
(四)滄源佤族民歌音樂中的終止式
在滄源佤族民歌中,許多歌曲都是封閉型終止,即在主音上終止,并且一些歌曲采取“加尾”式的補(bǔ)充終止,這種末尾處歌曲終止方式獨具特色,快要結(jié)束時,主音出現(xiàn),一般情況下,為倒數(shù)第二小節(jié)左右出現(xiàn)終止,然后,演唱者通過某個支持音進(jìn)向主音結(jié)束。例如:羽調(diào)式多數(shù)為徵音到羽音,下主音進(jìn)向主音,566 的方式結(jié)束,在羽調(diào)式中,一級支持音是角和商,徵音為二級支持音,通常情況下,宮音離得最遠(yuǎn),宮音很少起支持作用,一般情況下,宮音只作經(jīng)過音運用。然而,在滄源佤族民歌中,其末尾終止處,不僅有566 樣式,也有166 的結(jié)束方式,并且在佤族民歌中這種方式比較常見。另外,還有一種主音反復(fù)的方式,特別是在羽調(diào)式中,在末尾處,通常反復(fù)2—3 個6 音作為其主音出現(xiàn),即 666 的樣式,歌曲結(jié)尾處采用566 的方式,極具佤族風(fēng)格特點,給人一種為了鞏固其終止的之感。當(dāng)然,采用開放式結(jié)束的歌曲也有一些,較常見的方式是終止在其屬音上,音調(diào)從主音下滑至屬音后結(jié)束。滄源佤族民歌,結(jié)尾處采取意外終止方式的也有一些,即本應(yīng)該結(jié)束在主音上,卻出乎意料地在該調(diào)式以外的其他音上截止。例如歌曲《KAOX MAG LI BLIX DAI SI VEUI》本應(yīng)該結(jié)束在 A 音上,但卻結(jié)束在 B 音上,意外地以上跳七度的方式,給人一種嘎然而止的歌曲演唱效果。當(dāng)然,多數(shù)佤族民歌都以下滑音收束,由主音下滑至最低音結(jié)束,這種方式,可能與語調(diào)比較低沉的佤族方言有關(guān)。
三、滄源佤族民歌音樂節(jié)奏節(jié)拍分析
滄源佤族民歌源自于滄源佤族人們的日常生活,佤族人民生活節(jié)奏簡單而悠閑,這種生活節(jié)奏,反映在音樂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就是節(jié)奏較舒緩,演唱起來有平穩(wěn)之感。滄源佤族民歌節(jié)奏型多為均分的八分音符,也有一些節(jié)奏類型是前八后十六。滄源佤族民歌歌詞有的是兩字一拍,有的是一字一拍,這種節(jié)奏,既表現(xiàn)出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也體現(xiàn)了佤族人們的自身氣質(zhì)。滄源佤族民歌多為單一節(jié)拍,變換節(jié)拍的現(xiàn)象較少,一般情況下,都是2/4 拍, 演唱特點是歌者即興發(fā)揮。滄源佤族民歌一些結(jié)束音會自由延長,在某個長音上有時候會出現(xiàn)節(jié)拍變換的現(xiàn)象,歌曲演唱之初弱起進(jìn)入,形成不完整小節(jié),歌曲結(jié)束卻能夠?qū)崿F(xiàn)完整小節(jié)結(jié)束,民歌生活化的特點在這里獲得了充分體現(xiàn)。滄源人民在民歌演唱時在曲首習(xí)慣加一句甩腔,有時候,習(xí)慣曲尾加一句襯腔,甩腔、襯腔導(dǎo)致了節(jié)拍的變化,這種音樂節(jié)奏節(jié)拍,具有隨意性演唱的特點。例如《HMOUNG EX LUAH HING DINGMENG GA》,此曲音樂節(jié)奏節(jié)拍于 2/4 拍與 3/4 之間變化,在曲首加了襯詞,歌曲節(jié)拍發(fā)生了變化,為了整合開始的弱起小節(jié),在歌曲的末尾處用 3/4 拍記譜,后半拍弱起的節(jié)奏,增添了演唱的隨意性。
四、滄源佤族民歌音樂調(diào)式調(diào)性分析
中國民歌的音樂表現(xiàn)形式,主要的調(diào)式音階為五聲音階,當(dāng)然,也有一些較原始的民族在音樂作品創(chuàng)作中并沒有遵循五聲音階,調(diào)式音階不完整的現(xiàn)象依舊存在。滄源佤族民歌調(diào)式音階不完整的現(xiàn)象就比較嚴(yán)重,滄源佤族民歌中,二音、三音或四音音樂占一半以上,在滄源佤族民歌中,約四分之一左右民歌為612 三音列,滄源佤族民歌完整的五聲調(diào)式,主要調(diào)式音階為羽調(diào)式,徵調(diào)式和宮調(diào)式也比較多,出現(xiàn)變音的民歌只有少數(shù),在旋律中形成特殊的小二度,在歌曲演唱中,變音的出現(xiàn)是由于即興演唱所至,所以,在演唱過程中,這些變音不屬于調(diào)式內(nèi)的變音,并不能形成六聲或七聲音階,但可以形成裝飾性變音。例如《GRAX DOU EX GRAX NJEE ROMSAENG》,樂曲演唱時向下滑產(chǎn)生的變音屬于裝飾性的變音,不屬于調(diào)式內(nèi)的變音,只是一種嘆息般的語氣,并不能形成六聲或七聲音階。滄源佤族主要的調(diào)式特征就是單一調(diào)式,轉(zhuǎn)調(diào)的現(xiàn)象非常少,這與演唱民歌時比較隨意,民歌本身結(jié)構(gòu)短小有很大的關(guān)系。
五、滄源佤族民歌音樂曲式結(jié)構(gòu)、演唱形式分析
滄源佤族民歌音樂曲式結(jié)構(gòu)比較顯著的特征就是結(jié)構(gòu)短小,主要為一段體,由于其演唱的即興性,樂句構(gòu)成可由一個樂句、兩個樂句或者是許多樂句構(gòu)成,樂句的小節(jié)數(shù)多為非方整型,即4 或者 4 的倍數(shù),樂句與樂句之間以對比結(jié)構(gòu)居多,為非對稱的形式,單樂段多為上下句對應(yīng)式,復(fù)樂段一般由兩對上下句構(gòu)成,演唱者在此基礎(chǔ)上作小有變化反復(fù)。如果僅僅看表面,似乎這些樂句很即興,但仔細(xì)分析可以感受到同質(zhì)性對比的特點,可見,樂句之間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例如,仔細(xì)分析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一些民歌節(jié)奏型相同、結(jié)音方式相同、局部使用的音樂材料相同,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細(xì)節(jié)是采用頂真的方式來粘連的,并且在滄源佤族民歌中,這種方式是經(jīng)常使用的連接方式。滄源佤族民歌演唱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一領(lǐng)眾和的演唱形式,一種是獨唱形式,演唱過程中,領(lǐng)部的即興性較強(qiáng),其余跟隨的和部則較固定。如果遇到喜慶節(jié)日,還要配以打擊樂伴奏,或者即興配以簡單的舞蹈動作。滄源地區(qū)巖帥的玩調(diào)從始至終以同一速度演唱,有齊唱或二部、三部輪唱形式,演唱時歌聲此起彼伏,營造了一種熱烈歡快的氛圍。
六、結(jié)語
滄源佤族民歌音域較窄,多數(shù)旋律較為單純,在節(jié)奏、調(diào)式、曲式等方面,單一化特征也比較突出,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獨具特色的佤族傳統(tǒng)音樂才更加富有魅力,散發(fā)出古樸、單純、自然的原始?xì)庀ⅲ拖褚欢錁闼氐男』ǎ谖覈姸鄠鹘y(tǒng)音樂中,散發(fā)出獨特而別致的芳香。
參考文獻(xiàn)
[1]張宗紅.佤族民間音樂文化傳承中的積極因素[J].云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7(01).
作者簡介:張承林(1983—),男,云南省昭通市人,本科,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音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