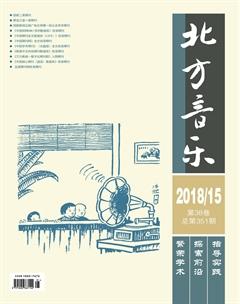論音樂中的再現性
【摘要】本文運用符號學的相關理論,結合音樂示例,首先分析了再現、指謂在音樂符號方面的表現,從表現手段上證明再現應用于時間藝術的抽象性;其次,探討音樂再現性現實主義的認識誤區,并借助再現性體裁與表現性體裁的比較研究,進一步闡釋再現性現實主義的實際內涵;由于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間的類似,最后本文對二者的聯系與區別進行了分析,以揭示音樂再現的獨特藝術地位與審美內涵。
【關鍵詞】再現;抽象;現實主義;語言描述
【中圖分類號】G229.24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再現”一詞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就已經圍繞“再現”這一概念進行過深入探討,諸多爭論持續至今。其中,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王朝聞先生從反映事物的主客觀特征方面為再現和表現做出了判斷依據,強調再現著重反映客觀性特征,而表現著重反映主觀性特征;程金城先生則因為再現派現實主義過度強化客觀事實,曾一再解釋現實主義文學不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原因等。藝術再現性研究似乎是一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學問,沒有客觀標準而言。一部藝術作品再現或不再現也許并不重要,但若從藝術哲學、藝術美學的角度來看,對再現做出判斷就顯得尤為重要。據“中國知網”主題字“再現”搜索,可查出相關論文一萬六千多篇,其中有五千六百多篇分布在語言文字、美學、哲學等文學學科,而音樂類僅有600篇。關于音樂再現性,研究者們的焦點主要聚集在兩方面:一是把再現理解為作曲家的一種創作手法,是關于調式調性、音型、和聲、主題等具體客觀反映的研究,旨在探索再現在曲式結構層面的重要意義。如大量奏鳴曲、敘事曲體裁類作品的曲式結構分析,又如楊儒懷在研究再現之于音樂發展的積極表現過程中,得出再現為大多數曲式結構成形、演變和變化基石的結論;二是基于作品演奏,以樂譜文本——音響文本的轉化過程為研究對象,把從風格、情緒、音量、音色到情感等方面的演奏最大程度上忠于原作的“音響文本”視為再現。如“再現意味著對符號化樂譜轉為動態音響結構的絕對忠實”(杜晶2015年)。
不同于以往研究,筆者結合實踐分析法與理論研究法,把視角轉移到符號學意義上的再現,即研究音樂符號對對象的再現,客體對主體的再現。文中先后對再現的含義、音樂再現的抽象理論展開闡釋,為有關音樂再現性現實主義的幾個誤區做出區分,并將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進行比較研究,揭示了音樂再現的內涵及藝術價值,以期為今后音樂符號研究提供努力新方向。
一、何為再現
(一)何為再現
“在任何對符號在藝術之中或之外起作用的方式的哲學考察中,都需要先來研究再現的本質。”[1]再現比之于舞蹈、繪畫、雕塑等藝術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然其在音樂藝術研究領域卻并未獲得足夠多的關注度。音樂中究竟有沒有再現?若有,那么再現又在音樂藝術中承擔了怎樣的角色?筆者針對上述問題展開研究,并將結果整理如下。當然,首先是關于再現評判標準的討論。
1.再現不是相似
相似具有對稱性和自反性,即若A與B相似,則B也相似于A,就像我們看到的一對雙胞胎兄弟間的相似,一條生產線上的汽車的互為相似。但再現不是對稱的,也不是自反的。一幅蘇里科夫的畫作《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再現了兵變失敗的近衛軍在莫斯科紅場臨刑前的悲壯畫面,但臨刑現場并不再現這幅畫;舒伯特的《魔王》再現了黑夜中父親帶著被魔王引誘的兒子在森林中疾馳的場景,但無論從父親、兒子還是森林來看,都無法再現這段音樂。因此,無論相似程度有多深,都不構成再現的必要條件。
2.再現不是復制
兩個關于模仿的訓喻誤區是“要制作一幅符合實際的圖畫,就是盡可能地將那個對象復制的如其所是”“復制的東西是對象存在或看上去的一個方面、一種方式”。拿破侖·波拿巴,是一個人,是法學家,是布里安萊沙托軍校被人嘲笑的學生,是細胞聯合體;達維特的畫作《拿破侖穿越阿爾卑斯山》塑造出現世英雄之形象,但看不到拿破侖對務實主義的信奉與否;披頭士樂隊用搖滾唱著所生活的世界,但不是全方位的世界;肖斯塔科維奇寫下了《第二鋼琴協奏曲》,回憶與孩童時期的兒子玩兒玩具兵的童趣畫面,但鋼琴的音響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玩具兵的發聲。你無法真正刻畫出一個事實的全部方面,你如何去看待事實和你所看到的事實都受到耳鼻口舌、大腦、過去等的制約,而倘若你真的做出了一個如此這般的事實,那也不過如出售禮物一般,并非藝術。
3.再現是主動獲得說明或解釋,是對對象的一種刻畫
藝術的模仿理論正方興未艾,藝術創作中對于對象的再現過程無外乎是通過模仿獲得某種說明和解釋而不是復制一種說明或解釋,而這種獲得即成為藝術作品的藝術創新、藝術價值所在。在主動獲得解釋的再現過程中,攝影師劉易斯·海因在社會紀實照片《10歲的紡織長工,北卡羅來納棉紡廠》中顯示出自己的藝術成就;保加利亞“夜鶯式”的無伴奏多聲部合唱成為了世界合唱領域的一朵嬌艷奇葩。
(二)何為指謂
指謂是再現的核心。就像是對一個對象進行描述的段落,一個作品若再現了對象,那么它就指謂這個對象。指謂有單個指謂、復合指謂:文學作品中講“狗”是真誠的朋友,既不是哈士奇狗,也不是比熊狗,既不是白色皮毛的狗,也不是棕色皮毛的狗,當然也不是從整體上指示狗這一類別,而是一般意義上的狗——有四條腿,會汪汪叫,有尾巴;《成語詞典》上的插圖“蛇”,既不指謂某只蛇,也不總體指謂蛇這一類別,它是一般意義上的蛇。指謂還可以是零指謂:中國當代華人音樂家譚盾為弦樂四重奏和琵琶所作的《鬼戲》就是零指謂再現。在驅魅和復魅的反復中,聽到鬼的哭泣、鬼的呼吸,然而卻從來沒有真正的鬼。
人們在欣賞藝術的過程中總是伴隨著“求知”的,繪畫雕塑作品也好,音樂作品也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人以感性的沖擊,但是也總會伴隨著人類的理性思考。所謂的理性思考,就是不斷地去“求知”,求有所得便轉化為一種快感 。什么是求知?這幅畫指謂這個事物,這部音樂指謂這個對象,正如高小康在《人與故事》一書中所說:“我們看見那些圖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為我們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斷定某一事物是某一事物”。[2]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是,藝術終歸是與審美需求相伴的。因此,圖像的種類不應以作品的指謂決定,而應視圖像本身的種類決定它的指謂;音樂更應視其本身所具有的這樣或那樣的審美特征為類別劃分標準。
(三)音樂再現的抽象理論
上文在何為再現的討論中提到,再現是對對象的一種刻畫與分類,是獲得解釋與說明。藝術價值產生于創作,創作需要有影響力的再現,而有影響力的再現又需要發明——對原型的所有存在方式和所有屬性不停地刪減、遺棄、組合,獲得新表達。這一過程表明了再現過程中的主動性。畢竟所有未被再現或即將被再現的對象絕不會順從地待在那里,露出其鋒芒,而藝術者們既不會再現出對象存在的所有方式,也做不到讓其所有存在屬性都不顯現。音樂藝術當然也不例外。音樂是有再現性的,如舒伯特《魔王》的例子,肖斯塔科維奇《第二鋼琴協奏曲》的例子,但是音樂作為一種時間維度藝術,又是如何再現四維空間的呢?再現在音樂中的地位較之于繪畫、雕塑等是否還是顯得尤為重要?針對上述疑問,筆者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說明。
1.抽象化的再現性手段
余建章、葉舒憲曾在《符號:語言與藝術》一書中對藝術進行分類,第一類是四維空間的形體類藝術,如舞蹈、儀式表演等。這一類藝術因為有空間和時間的四維展示,因此對對象(即原型)的刪減,或者說抽象的方面較少。因此,從人類的感官和思維上來講,是更容易聯想和還原對象的。第二類是舍棄時間維度的空間造型藝術,如雕塑、陶器、建筑、繪畫等。這一類藝術雖說沒有了“時間”的“敘述”,但還是有物理維度支撐你去想象。第三類是則是時間維度藝術,如音樂、詩歌、民間文學等。至此,所有再現僅能依靠你的內心表象去建立,如果詩歌還是有眼睛參與的話,音樂則僅能依靠耳朵去聽見聲音、 “看見”畫面和“讀出”故事。從四維空間藝術再到時間藝術,音樂中的再現手段無疑是最抽象的。
2.抽象化的再現性表達
表達之抽象,一方面體現在音樂符號表征對象的一般性上。叔本華說:“(音樂)在某種程度內可以說是抽象地、一般地表示這些情感的本質上的東西。”[3]意思就是說,音樂要表達的所有的情緒既不是這樣的快樂,也不是那樣的痛苦,而是從無數種快樂和痛苦中抽象出來的一般意義上的快樂和痛苦本身。音樂要表述的情況也不是具體上或這樣或那樣的情況,而是從各種情況中抽象出來的激發最原生感覺的表述。列維·斯特勞斯對此也發出過“音樂不依賴于任何模仿卻使人歡喜”[4]的言論。再現性表達之抽象一方面還體現在音樂表征對象的“不準確”上。斯美塔娜《我的祖國之沃爾塔瓦河》中,作者用長笛、單簧管分別指代沃爾塔瓦河的兩條源流,用圓號再現狩獵號角的回音,用木管象征城堡等。可是如果沒有標題,你能確定音樂中的河流是沃爾塔瓦河的源流嗎?又或者你能判斷這是溪流的歌唱嗎?同理,你又能否僅從木管主題得出所再現的城堡是紅磚建筑還是白磚建筑的結論?這些自然是無法準確識別的。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音樂在再現表達上的巨大抽象性,才給耳朵的獨立發展帶來了可能性,讓音樂擺脫了理性的束縛,從而獲得更大意義上的自由與音樂審美體驗。
二、音樂再現的現實主義
(一)再現性現實主義的認識誤區
關于再現的現實主義標準,一直以來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判斷。一種認為再現現實主義由作品的欺騙性所決定;另一種則認為由作品發出的信息數量所決定。欺騙性觀點的持有者認為,作品只要能產生成功的幻象就是現實主義,即只要能夠讓欣賞者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它所再現的東西或所再現東西的特征就是再現的現實主義。其實,反駁這一觀點并不困難。以譚盾的《鬼戲》為例,音樂再現了鬼之哭泣與哀嚎,然實質是情感需求的完全解放,重在自我感受,是表現主義音樂而非現實主義。畢竟只要場景設計充分,就足以讓非現實主義音樂具有欺騙性。就像用炸油條的聲音充當淅淅瀝瀝的雨聲完成一段電影配樂,這段配樂目的在于渲染內心的靜謐卻并不是再現雨天。另一種信息量決定再現現實主義的觀點,同樣有充分的理由給予否定。聯系信息傳達的編碼和解碼理論,一部分已被公認的現實主義音樂,如能重新建立符號系統,讓新的編碼與舊的編碼一一對應,比如讓大調(即明亮)代替小調(即陰暗)、讓高音表示淺吟而不是低音等,只要這一編碼成為解碼者的常規習慣,那么非現實主義的音樂也就與現實主義音樂產生了同樣的信息。可能你會說上述的例子絕不可能發生,但誰又能否定這是你長久以來養成的解碼習慣的結果呢?
(二)再現的現實主義標準
再現的現實主義標準既不是欺騙性也不為信息量所決定,而在于成功解碼的難易程度。這與再現模式的固定性及解碼系統如何通行是緊密聯系的。對這一標準進行解釋實則并不容易,因此,筆者要再一次重申符號學的編碼和解碼理論。人類信息傳達的過程就是表達者編碼、理解者解碼的過程。表達者的編碼需要經歷制碼和發碼。“制碼是使訊息符號化……發碼是符號形式的呈現。”[5]作曲家貝多芬想傳達“告別”這一信息,于是把這一信息在大調式體系中按照大三度、純五度、小六度的下行音程排列,組合成號角的聲音用以表達告別,完成制碼;當貝多芬完成《降E大調奏鳴曲》(Op.81a)這一作品,進行演奏時,發碼成功。接下來就是接收者的解碼過程,即理解符號信息的過程。接收者從貝多芬的音程下行進行感受到了結尾,從音程度數的變化中聽出了“狩獵號角”,并聯想到宮廷貴族生活,于是最終將這段音樂指謂高貴浪漫的告別。至此,解碼結束,一條浪漫的告別信息得以傳播。這當然是一條理想的交際傳播鏈,編碼者貝多芬掌握了大家習慣和認可的編碼規則,解碼者的聯想、推理與編碼者剛好一致。然而,在更多交際過程中,編碼者對信息符號化之后,解碼者卻未必得到相等的信息,也就是說會產生誤解。受到生活方式、專業修養、地區文化、時代特點的影響,編碼者形成了與其一一對應的編碼規則,而解碼者卻只能按照人們早已約定俗成的解碼習慣,即“根據編碼的符號能指形式進行一定的聯想和推理,從而獲得關于該能指形式的所知訊息”,當表達者與理解者符號規則不統一時,誤解便也產生了。
現在,再回頭看再現的現實主義標準,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再現的現實主義不受欺騙性和產生信息量的影響,在于解碼過程的容易程度,即表達者的編碼規則為眾人熟知和習慣,理解者可以輕松地用已知的解碼規則對作品進行解碼。因此,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講:再現是關于編碼規則選擇方面的問題,準確性是關于解碼信息的問題,而現實主義是關于習慣性的問題。習慣是根深蒂固的,但隨著經濟、文化、政治生活的變化也會發生改變并重新養成。從這一點來看,現實主義是相對的,現實主義的標準遷移也是非常迅速的: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現在看來當然可以是現實主義的,因為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判斷音樂符號的意義,但是在當時卻一度為長期習慣古典主義符號解讀的世人所不解。19世紀美國人眼里的爵士音樂不同于現代的美國人,也不同于20世紀的英國人,鄉村音樂、布魯斯音樂也是同樣的道理。沒有任何永恒的現實主義。
(三)音樂中再現的現實主義體裁
1.再現性現實主義的體裁及其來源
音樂中最具代表性的再現性現實主義體裁當屬敘事曲,敘事曲又分為聲樂敘事曲和鋼琴敘事曲兩種。傳統的敘事曲主要指歐洲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四國的敘事曲,這四國的敘事曲雖然有各自的獨特之處,但都以分節歌的形式或敘述英雄史詩、或講述民間愛情、或講述古代神話。聲樂敘事曲、鋼琴敘事曲建應在傳統敘事曲的創作方式之上,再現出亦幻亦真的內容,并在作曲家手里得以發展壯大。不過,說起敘事曲就必須談及敘事詩。敘事詩是一種集民族性、戲劇性為一體的詩節式結構的對話敘述藝術,以民間故事為原型,詩作者注重刻畫人物性格、人物對話和動作,故事的陳述相對客觀。作曲家以這種敘事詩為載體創作了聲樂敘事曲,又以聲樂敘事曲和敘事詩為原型創作出鋼琴敘事曲,其原型敘事詩的客觀再現性決定了敘事曲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了再現性。典型的聲樂敘事曲——舒伯特的《魔王》就是這樣一部再現性現實主義作品。舒伯特在該敘事曲中用到了不同的音區音調、柱式和弦、快速并貫穿全曲的三連音節奏型等多種手法(也就是符號學意義上的編碼),再現父親為了拯救被魔王引誘的兒子在黑夜里騎著馬疾馳,最終兒子還是不幸死亡的故事。簡言之,敘事曲這種再現的現實主義體裁在民間故事-敘事曲-敘事詩-聲樂敘事曲-鋼琴敘事曲的過程中產生。不過,在音樂巫術說方面,也對敘事曲的體裁來源有一定解釋:“接觸巫術-轉喻功能-象征意義-音樂的敘事性。”[6]正如我們在多部故事傳說中所聽,接觸巫術往往借助于人的頭發、衣物、指甲等對人施行巫術,這是因為接觸巫術暗含著部分代替整體的規則,認為相近事物間有著相對強烈的影響作用。在這樣的原則下,接觸巫術對原始符號實現了轉喻功能性的操作,以部分象征整體。在接觸巫術之后是雨后春筍般林立的神話傳說,一個個關于祖先、神靈的英勇事跡成為部落文化的象征,化身為藝術創作之典型,構成敘事曲再現性現實主義的原型。
2.再現性體裁與表現性體裁的區別
與再現性音樂體裁的來源不同,表現性體裁如幻想曲、狂想曲等,來源于模擬巫術,發揮隱喻的功能作用,以意向間的相似性實現意向轉化,以音樂表達作曲家內心情感;與再現性音樂體裁的規整結構及內容上的陳述性相區別,表現性體裁以抒發情感為主,結構多以片段化存在;與再現性音樂體裁的單一動機不同,表現性體裁往往發展多個主題,形成意向的組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再現性體裁重在富有邏輯意義地講述事情的原委,而表現性體裁依賴多種創作手法將事件加工,完成音響意向的組合。
三、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
從表達模式的含義來講,“音樂作為一種高度抽象化的復雜的聽覺符號系統”,[7]既相似于語言符號,又與語言符號相區別。
(一)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的共通之處
音樂再現需要讓音樂符號和對象這二者間具有指謂關系(第一章已論述),指謂一個對象,就要描述這個對象;語言對對象的描述同樣要指謂這個對象。音樂再現和語言描述共同歸結于指謂之下,因此,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就產生了極大的關聯。
1.音樂再現與語言描繪都要經歷選擇、變形的抽象過程,完成對對象的解釋和說明,并彼此間相互影響
沒有經歷選擇和遷移,音樂與語言就不能被稱為藝術。同理,音樂再現和語言描繪作為人類藝術表達的重要手法,就必須經過剝絲抽繭,對被表征客體的某些特點進行詮釋。在此進程中,若藝術家們通過慣有的符號體系去再現事物未被發現的新方面,或者將事物早已被認知的一面用非傳統的符號去組織和展現,那么此時的音樂再現或語言描繪便成為了富有藝術價值的創新性藝術。畢加索采用新奇而不被習慣的“土著面具式”象征符號為美國文學家、詩人格特魯德·斯泰因所作的肖像,曾一度被人評價為最不像斯泰因本人的畫像,其與女主人氣質之高度相似直到數十年后才得以為業界所正名;貝多芬在序曲《艾格蒙特》中用激烈的和弦再現西班牙朝廷的陰險;“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詩人白居易寥寥幾句就寫出鶯歌燕舞、繁花似錦的早春景象,從“漸欲”和“才能”二詞之中,我們更是看出此番春景是詩人主觀選擇的結果,是詩人個人對所見之春的解釋說明;同樣是描寫春日,宋朝晏殊一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卻深深道出詩人惆悵之情。無論是畢加索的變形、貝多芬的遷移,還是白居易、晏殊的選擇,它們都是作者用來對對象進行解釋說明的手法,并在此之后成為當之無愧的永恒藝術之作。
2.音樂與語言大多時候通過表征客體本身進行分類,偶爾又可以根據客體與對象間的指謂關系,即單一指謂模式、復合指謂模式或零指謂模式進行分類
表征客體即將事物藝術性再現的載體符號,按此標準執行劃分后,音樂中的可分類別有敘事曲、革命曲等,語言中的可分類別如詩歌、散文、小說等。而按照指謂關系進行劃分的實例如下。吳祖強、杜鳴心先生創作的《水草舞》,在引子部分再現了纖細柔軟的水草在水中微微擺動的場景,而這水草既不是指生長在云南的水草,也不是長或短的水草,而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水草,是一種復合指謂;三國時期的曹植用“髣髴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再現虛擬人物——體態婀娜的洛神,是一種零指謂;小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是一種單一指謂,仿佛描繪出了多瑙河河面上的躍然靈動。
3.每一種音樂再現和語言描述的應用或分類,都有與其相對應的符號系統——編碼、解碼系統,而符號系統的選擇是相對自由的
各個時代的藝術家們運用自己所熟悉的藝術符號,將情感或真實的世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完成個人的編碼,并最終在人們的欣賞與求知中獲得普通的解碼,這一點毋庸多言。
(二)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的差別
符號體系同時包含了符號本身及其對對象的釋義,音樂再現、語言描述二者之間,除了符號體系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音樂再現是一種經過自我選擇的再現,傾向審美性功能;語言的具體與確切使得語言描述不得不承擔再現客觀世界的任務。以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與歌德《艾格蒙特》戲劇的比較為例,貝多芬在眾贊歌響起,再現英雄艾格蒙特之死之后,并沒有結束整段音樂,而是加入頌歌,象征真正的英雄永垂不朽,繼續活在世人面前;而在歌德的戲劇中,艾格蒙特伯爵最終因反抗壓迫被處以死刑,離開了現實世界。“原始人類或許用過前音樂聲音,可能是一種準音符的形式出現的,用以表達情感;還或許用過周期性的聲音結構,用以在各式各樣的身體動作之中確保同步性。但是,只有在這些聲音之結構被賦予了抽象的、無涉的意義之時,這些聲音結構方才成為音樂。”[8]漢森所講正可以說明,音樂再現在經歷高度抽象之后便產生因無序而高度凝華的審美性。然而,盡管語言符號一樣需要抽象,但傳達結果終歸是具體的,也因此語言符號需要更多地承擔描述客觀世界的任務。
以上是筆者對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所作的區分,當然,當前也有不少學者因音樂再現過程中對語言描述的依賴(音樂再現最終還是要以語言為“媒介的媒介”來解釋與傳播),認為音樂再現的本質就是語言描述,意即二者并無本質上的差別。不過,就像音樂再現需要音樂符號而語言描述依賴語言符號一樣,音樂再現與語言描述一定存在本質上的差別才造成二者在一般意義上的不同,不過其本質差異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結語
再現在藝術領域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從舞蹈形體、啞劇等四維藝術,再到雕塑、建筑、繪畫的空間藝術,從詩歌、文學再到音樂,再現總是伴隨著藝術的成長與變遷。人們在尋找再現的過程中滿足自己的審美需求,在對符號與對象指謂關系的求知中,獲得快感。音樂信息大多時候無法直接告訴人們任何具體的形象,其再現也無疑是最復雜的、最抽象的。本文運用符號學相關原理,在音樂實例的基礎上,對包括再現、指謂、現實主義在內的一系列概念進行了探討。通過比較研究,找出了現實主義體裁的來源及其特點,并對再現與語言描述的聯系及區別做了初探,以便為今后的音樂符號研究提供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美]納爾遜·古德曼,彭峰.藝術的語言——通往符號理論的道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06).
[2][美]高小康.人與故事——文學文化批判[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42).
[3][德]叔本華,石沖白.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印刷館,1982:361.
[4][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顧嘉琛.看·聽·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85).
[5]黃華新.符號學導論[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36).
[6]李小諾.音樂表述中的表現性——以幻想曲、隨想曲、狂想曲為例[J].音樂藝術,2010(04).
[7]張國良.傳播學原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105).
[8] Finn Egeland Hansen. Layers of Musical Meaning[M].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06(28).
作者簡介:江俊葉(1995—),女,深圳大學音樂與舞蹈專業2017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音樂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