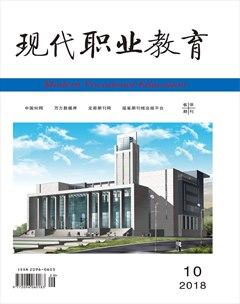積極心理學視角下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研究
鄧晨曦
[摘 要] 網絡影響著高職學生生活的各個方面。網絡既有消極影響,又有積極影響。積極心理學視角下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引導途經包括從自我實現的價值觀促進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從網絡道德品質角度引導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通過情感認知的加強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這些途徑對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促進具有十分積極的影響。
[關 鍵 詞] 積極心理學;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
[中圖分類號] G715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2096-0603(2018)29-0136-01
積極心理學自20世紀以來,取得了心理學家的廣泛認可,他們將更多的心理學課題放在積極心理學的視角下進行研究,其中利他行為是社會心理學家廣泛研究的一項課題。網絡利他行為的相關研究始于信息時代,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網絡上的利他行為更具有現實意義。對高職學生來說,他們接觸網絡的時間較長,網絡利他行為對其道德品質的塑造和人生價值觀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積極心理學視角下,對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關注,能夠從發展和解決問題的眼光入手,培養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以及個人價值的實現,在教育管理中具有重要意義[1]。
一、積極心理學視角下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現狀
積極心理學的研究最早從個體主觀幸福感研究開始,關注個體自身的積極個性品質,強調自我管理和沉浸體驗等內容,在心流當中體驗到持續的幸福感。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網絡已經融入個體生活當中的方方面面。對高職學生來說,他們每天都在接觸不同的網絡環境,網絡社交已經成為他們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與以往的利他行為相比,網絡利他行為對高職學生具有重要意義。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主要表現在網絡的易得性,他們將網絡作為一種手段,提高了利他行為的效率。另外,網絡信息的匿名性為高職學生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更有利于他們表達真實的想法,同時對其他人進行幫助。如在校園論壇等網絡平臺上開展的學習互助、健身互助、情感互助、重大災難互幫互助等,都是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常見表現形式[2]。
總之,高職學生將網絡作為利他行為的一個新媒介,新的媒介使利他行為更易于發生,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同時給他們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傳播速度快且影響范圍大。
二、積極心理學視角下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引導
(一)從自我實現的價值觀促進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
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在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滿足的前提下,個體會尋求歸屬感的人際交往中實現需要,而最高層次的需要即是自我實現的需要。高職學生階段,通過網絡上的交往能夠獲得人際交往中歸屬感等需要。同時在網絡當中的利他行為,能夠體現個人的自我價值,在幫助他人的過程當中,高職學生更能夠發現自我的閃光點,與以往時期的教育經歷相比,這更能幫助他們提高自尊、自信,促進其自我實現[3]。
(二)從網絡道德品質角度引導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
與傳統思想道德品質培養相比較,網絡道德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網絡交往具有匿名性,缺乏相應的限制,因此應對高職學生的網絡道德進行規范。而有關網絡道德的培養,越是限制的內容越容易引起學生的注意,疏導不如引導,因此可通過鼓勵學生進行網絡利他的角度來培養學生的網絡道德。網絡道德品質的塑造又能夠促進高職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發生。
(三)通過情感認知的加強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
通過情感對行為的促進作用,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通過無形的精神獎勵等方式,對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進行積極強化。或者對具有榜樣作用的個體進行專題宣傳等活動擴大影響,引發其他高職學生的模仿行為[4]。
(四)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
通過對積極個性特質的培養,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在積極心理學視角下,優秀的個性品質具有重要意義,諸如奉獻、愛、責任等。通過這些積極品質,促進和鼓勵高職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對高職學生優良個性品質的培養也具有重要意義。此外,網絡利他行為能夠給高職學生提供沉浸體驗和積極的情緒,為后續網絡利他行為的發生提供基礎[5]。
總之,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網絡利他行為對于高職學生道德意識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高職學生在網絡利他行為中不僅能夠形成積極人格,同時也能強化自身社會責任感,從而促進高職學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梁芹生.積極心理學視角下青少年的網絡利他行為研究[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7,37(23):24-26.
[2]鄭顯亮,丁亮,袁淺香.網絡利他行為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J].中國特殊教育,2017(8):80-87.
[3]楊欣欣,劉勤學,周宗奎.大學生網絡社會支持對網絡利他行為的影響:感恩和社會認同的作用[J].心理發展與教育,2017,33(2):183-190.
[4]鄭顯亮,王亞芹.青少年網絡利他行為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一個有中介的調節模型[J].心理科學,2017,40(1):70-75.
[5]劉勤為,徐慶春,劉華山,等.大學生網絡社會支持與網絡利他行為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心理發展與教育,2016,32(4):426-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