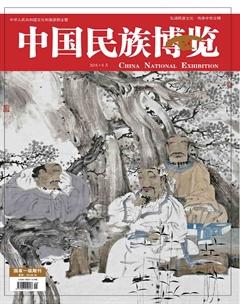淺談意象首飾與虛構(gòu)體驗(yàn)
李一平
【摘要】當(dāng)代首飾材料的選擇和使用讓首飾具有使觀者產(chǎn)生意象聯(lián)想的特征。這些特征體現(xiàn)在對材料的部分截取上、材料結(jié)合的多樣性上以及形態(tài)的抽象概括上。這種材料結(jié)合所制造出的“陌生感”是使觀者產(chǎn)生虛構(gòu)想象的最主要原因。如同詩歌對語言的重塑與解構(gòu),首飾運(yùn)用材料的方法是一種將約定俗成的意義打破、重新體驗(yàn)事物的嘗試。因而,首飾借由材料引發(fā)了觀者產(chǎn)生基于自身經(jīng)驗(yàn)的虛構(gòu)想象,促發(fā)并推進(jìn)了虛構(gòu)體驗(yàn)的過程。
【關(guān)鍵詞】首飾;虛構(gòu)體驗(yàn)
【中圖分類號(hào)】TS9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首飾材料的運(yùn)用十分廣泛,當(dāng)代首飾展作為對一類藝術(shù)作品的展現(xiàn),所呈現(xiàn)的材料種類之多,相比其他藝術(shù)類別的展覽是突出的。例如,《十年·有聲——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與國際當(dāng)代首飾展》所展出的65位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材料種類據(jù)筆者統(tǒng)計(jì)有43種之多,平均每1.5人用到的材料與別人不一樣。又如歐洲規(guī)模最大的首飾廊MARZEE于2015年舉辦的國際首飾畢業(yè)作品展中,共100位參展學(xué)生中使用的材料種類甚至超過了100種。這種面貌讓首飾與材料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非常微妙,當(dāng)我們看到兩種被特意組合在一起的材料時(shí),未知的選材的理由使得它們的關(guān)系撲朔迷離。表達(dá)物質(zhì)材料自身的特點(diǎn)成為當(dāng)代首飾創(chuàng)作的方式之一。
當(dāng)代首飾如此注重創(chuàng)造新材料的現(xiàn)象或許基于首飾從屬于工藝美術(shù)的歷史背景。就近60年來首飾制作者對首飾“自主性”的“民主化”開拓過程而言,這種現(xiàn)象顯得很自然。特別是在現(xiàn)階段中,當(dāng)代首飾還屬于一個(gè)肇始之初的藝術(shù)領(lǐng)域,材料的廣泛實(shí)驗(yàn)的確是一種富有成效的藝術(shù)探索。所以,發(fā)揮出新材料所能傳達(dá)的更多藝術(shù)表達(dá)的愿望也使得首飾的表現(xiàn)形式給與了材料一個(gè)廣闊的舞臺(tái),使之成為主角。
當(dāng)代首飾對材料具有特殊的表現(xiàn)方式與能力。首飾多在一個(gè)相對精微的空間里構(gòu)筑和雕塑形態(tài),這對材料提出了特別的要求,材料需要獨(dú)特且耐看。往往材料呈現(xiàn)自然之狀態(tài)的前提是它需要有一定規(guī)模的積累,因?yàn)樵谧匀恢校鳛槿说母兄蛯χ車澜绲亩攘砍叨纫欢ㄊ谴笥趯κ罪椀挠^察的,所以,當(dāng)材料被提取或濃縮之后,相繼會(huì)失去部分人在正常認(rèn)知尺度中所感知的材料的特質(zhì),例如,泥土在地表的龜裂、礦物原生狀態(tài)下的簇狀結(jié)構(gòu)、木頭完整的回紋紋理、毛發(fā)的披散狀態(tài)。因此,當(dāng)代首飾對材料利用的廣泛性以及對體積的要求使得材料普遍經(jīng)歷了去粗取精的過程,對現(xiàn)成品的利用也多解除了其使用慣例。由于體積較小,首飾的形態(tài)不容易受到重力的牽制而變化多端,同時(shí)材料本身也將啟發(fā)形態(tài)的變化與落定,這就使材料不容易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物像,從而開始走向意象化。
意象意指一種具體可感的物象,類似于詩歌中的喻象。赫伊津哈稱:“存在與理念之間的永恒鴻溝只能靠想象架起虹橋。言不盡意的概念總是與生活的激流不相適合。因此,只有意象創(chuàng)造或修辭語匯才能表達(dá)事物,同時(shí)給它們沐上理念的光輝:即理念與事物在意象中統(tǒng)一。”意境是經(jīng)歷意象的結(jié)果,如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到的“神與物游”,又例如元代戲曲作家馬致遠(yuǎn)的《秋思》中“枯藤、老樹、昏鴉”將被概括為讀者內(nèi)心想象的形象,更像是一種象形。
再者,材料的異質(zhì)結(jié)合也是造成首飾材料陌生感的原因之一,例如,荷蘭首飾藝術(shù)家夏聶爾(Lucy Sarneel)用日用器具與手工部件拼貼結(jié)合的作品(見圖1、圖2)。由于作品中各元素都來自幾乎不相干的系統(tǒng),如我們習(xí)慣所劃分的:葫蘆來自植物、噴漆來自顏料或繪畫材料、一個(gè)被概括的簡單形態(tài)可能來自兒童玩具或者工業(yè)零件。這樣的異質(zhì)結(jié)合致使它們失去了慣常的敘事語境,紛紛來到了一個(gè)無名的舞臺(tái)之上,而讓自身的材質(zhì)、顏色、紋理等物質(zhì)特征得到彰顯,開始在彼此間尋找新的適配關(guān)系。這就像一個(gè)人脫離了原來生活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和接受的秩序習(xí)慣來到新的國家,在全新的環(huán)境構(gòu)成中他便會(huì)將外界與自己聯(lián)系起來,而這種連接對于環(huán)境、對于此人自己而言都是全新的。由此作品賦予了日常物品以新的生命,使它成為了某種意象。這樣的作品并沒有給定一個(gè)情節(jié)模式,所有被串聯(lián)的物件等待被觀者代入自身經(jīng)驗(yàn)去理解。它們幾乎平等地面向不同的人,由觀者“拿起”其中某個(gè)與其他物件聯(lián)系想象。
在后戲劇劇場的實(shí)踐中,同樣出現(xiàn)了類似的表達(dá)。20世紀(jì)50-60年代的歷史先鋒派對傳統(tǒng)古典主義戲劇構(gòu)作的破除中運(yùn)用了拼貼的手法。90年代的后戲劇劇場代表人物威爾森(Robert Wilson)用燈光、顏色、互不相襯的符號(hào)與物體構(gòu)成舞臺(tái),做出了不表示任何同質(zhì)空間的嘗試。這樣的實(shí)踐破除了劇場的整體闡釋性,使得空間具有夢幻般的特質(zhì),它消除了劇場構(gòu)成的等級性,所有物質(zhì)都是同時(shí)并列呈現(xiàn)的,并且形成了每個(gè)單元的意指都取決于最終的整體觀看方式,而不是每個(gè)單獨(dú)部分拼加起來所構(gòu)成的一種整體效果。這種存現(xiàn)和展示本身不傳遞任何信息,主題是物品自身,需要觀眾自我選擇和理解信息。在夏聶耳的作品中,物體同樣通過并置的方式構(gòu)成了一個(gè)后戲劇劇場,也正是這種對材料非正常狀態(tài)的呈現(xiàn)讓材料彼此間的交流回歸于物性,變得更加細(xì)膩。
當(dāng)代首飾放棄了材料所能被立即認(rèn)知的呈現(xiàn)狀態(tài)而開拓了新的內(nèi)容。當(dāng)一種人們不認(rèn)識(shí)的材料呈現(xiàn)在眼前時(shí),對材料認(rèn)知的模糊性將帶領(lǐng)觀者經(jīng)歷他們自己的世界,這種體驗(yàn)是屬于觀者自己的。創(chuàng)作者細(xì)膩精準(zhǔn)的感受被材料展現(xiàn),觀者也將從單純的質(zhì)感、形態(tài)、顏色上深入想象。這種旅程比一個(gè)說服邏輯的解釋來得更“身臨其境”。首飾對材料運(yùn)用的這種特點(diǎn)對于首飾傳達(dá)抽象感受的意義是很重要的,材料不再被輕易辨認(rèn)出來,所以,材料組建的首飾對于觀者來說將是一種全新的認(rèn)識(shí),呈現(xiàn)在觀者眼前的顏色、體塊和質(zhì)感以重構(gòu)的方式被想象和理解,這與詩歌重構(gòu)語言的原理十分類似。詩歌的閱讀也更加有助于破除語言的隔閡。“蕭勒斯(R.Scholes)在談到詩歌的陌生化時(shí)說:‘人之所以為人是通過語言。而語言的獲得使人不同于其他任何語言所命名的事物。名稱是事物的替代物,在命名過程中,它便取代了該事物。因此語言最終甚至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障礙。我們大部分的詩歌都是為了改變這一情形而寫的。詩歌是用來揭開那使所有事物具有一種虛假的熟悉感的面紗……”當(dāng)代首飾解除了觀者對材料的預(yù)先認(rèn)知,事物間的關(guān)系需要觀者自己去建立,這樣的陌生感同樣可以從詩歌的特征中感受到。赫斯特(Hester)稱:“在非詩歌的語言中,符號(hào)的任意性和約定俗成性使意義和感覺盡量保持最大的距離,而詩歌使意義和感覺形成了某種‘融合(fusion)。意義和感覺的結(jié)合傾向于產(chǎn)生一個(gè)完全封閉的事物,與日常語言及其完全的指稱特點(diǎn)不一樣。”束定芳將詩歌中的語言看作一種物質(zhì),系統(tǒng)為構(gòu)成其整體的部分重新定義。語言的指稱被歧義完全改變,所以,詩歌所被欣賞的詩意并不是修辭手段的作用,而是所有話語的組成成分得到了重新認(rèn)知,進(jìn)而詩歌是詩人將語言作為材料的創(chuàng)作結(jié)果。“藝術(shù)的形式就是訴諸感官的形象。”詩歌中的每一個(gè)詞都能對人產(chǎn)生不同的意象,意象不斷產(chǎn)生且被讀者不斷經(jīng)歷,并往往以物象的方式被感知,是一種以各種不同形象出現(xiàn)的物化情感。若從詩歌創(chuàng)作機(jī)制的理解角度看待當(dāng)代首飾,當(dāng)代首飾則是藝術(shù)家借助材料形成自我語言的一種表達(dá)方式,首飾的部件是一種對形象的概括(圖3),其對于材料的發(fā)掘以及建構(gòu)特點(diǎn)在許多方面更廣泛地涉及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機(jī)制。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表示,詩歌語言能夠表達(dá)出一種虛擬經(jīng)歷,這種經(jīng)歷是一種對形象拼合的想象。
所以,當(dāng)代首飾與詩歌都體現(xiàn)出一個(gè)特點(diǎn):使現(xiàn)實(shí)中已被賦義的事物經(jīng)過重新編排組合脫去舊有意義,讓原本完整可讀的事物支離后再拼合成新的面貌。而這種相同的虛構(gòu)體驗(yàn)恰恰是首飾對材料的特殊轉(zhuǎn)換而實(shí)現(xiàn)的。在觀看一件意象化呈現(xiàn)的首飾時(shí),就如同在經(jīng)歷詩歌中詞語形象的拼合過程,它需要不斷地從自己已有經(jīng)歷中尋找能與這個(gè)陌生事物相聯(lián)系的感覺。在這個(gè)過程中,不斷憑借的就是被重新組建的形象,這些被概括后的形態(tài)便形成了觀者虛構(gòu)想象世界的憑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