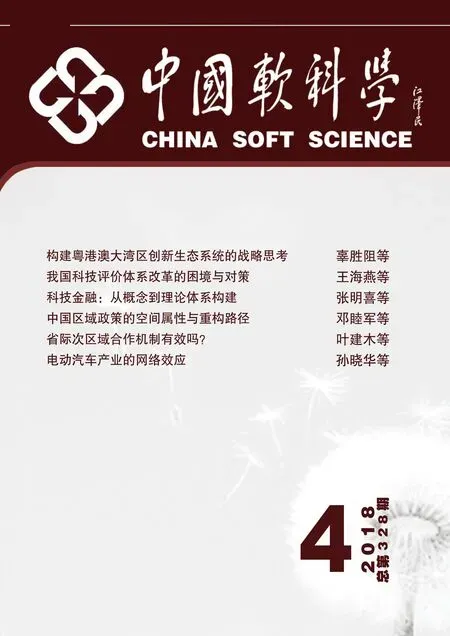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有效嗎?
——空間結(jié)構(gòu)與治理模式的聯(lián)合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
葉建木,張 帆,熊 壯,張 權(quán),張 超
(1.武漢理工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0; 2.合肥工業(yè)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全球化、區(qū)域合作一體化大背景下,次區(qū)域合作越來越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共識。亞洲的大湄公河次區(qū)域合作、東盟增長三角、圖們江次區(qū)域等都是要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從而推動次區(qū)域合作的開展[1]。“次區(qū)域”(sub-region)或者“亞區(qū)域”這個詞最早見于亞洲開發(fā)銀行的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不同學(xué)者在學(xué)科出發(fā)點和研究角度上的差別,使得“次區(qū)域”的內(nèi)涵區(qū)別很大。跨疆界的自然經(jīng)濟領(lǐng)土(Robert Scalapino,1992),都市的延展地區(qū)(T.G. Ma Gee,1992)在一定程度上描繪了“次區(qū)域”。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主要關(guān)注洲際層面或國家級層面的次區(qū)域研究,而聚焦一國之內(nèi),省際、市級層面的次區(qū)域研究僅僅處于醞釀階段。關(guān)于次區(qū)域合作的較早研究主要是次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問題,隨后研究熱點延伸到次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的非經(jīng)濟效應(yīng)、非經(jīng)濟影響因素及非經(jīng)濟領(lǐng)域合作等(Hiroyuki Taguch,2014;Nicholas N Ngepah,2014;王鐵,2008;張玉新,2012;倪超軍等,2008)[2-4]。就中國而言,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發(fā)展取得巨大進步,開創(chuàng)了“中國模式”,但發(fā)展過程中依然存在諸如整體發(fā)展快而局部不平衡,中心發(fā)展快而邊界不平衡等瓶頸問題。經(jīng)濟社會資源過度集中于區(qū)域中心地帶,而以地緣為載體,由兩個及以上相互毗鄰的省際邊界地域,往往成為“被遺忘的角落”、“經(jīng)濟發(fā)展的洼地”[5-6]。因此,針對省際次區(qū)域這一空間主體形態(tài)的合作發(fā)展研究,有益于提升省際邊界地帶聯(lián)動合作發(fā)展的效率,對于邊界地區(qū)加快城市群規(guī)劃建設(shè)、探索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從內(nèi)涵來看,以區(qū)域為參照系來界定“次區(qū)域”,缺乏科學(xué)性和嚴(yán)謹(jǐn)性,“次區(qū)域”的概念依然不清晰(李鐵立,2005;梁雙陸等,2012)[7-8]。從內(nèi)容來看,除經(jīng)濟合作外,以其他角度為切入點來界定“次區(qū)域合作”也顯得尤為必要。因此本文認(rèn)為,省際次區(qū)域是指在區(qū)域一體化的現(xiàn)實背景下,兩個及以上省際毗鄰地區(qū)由于地理區(qū)位、行政區(qū)劃、資源條件、文化習(xí)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展階段等原因聯(lián)結(jié)而成,具有一定同質(zhì)性的特定地理空間[9]。其特點包括:(1)明顯的邊界效應(yīng);(3)同質(zhì)性和異質(zhì)性并存的“共軛關(guān)系”;(3)強烈的一體化需求等。而所謂“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是指“省際次區(qū)域”在一體化進程中,為了穩(wěn)定與發(fā)展等需要而開展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環(huán)境、安全等領(lǐng)域的綜合性合作,從而實現(xiàn)1+1≥2的加和與積增效應(yīng),合作內(nèi)容具有廣泛性,其本質(zhì)上是一種地區(qū)主義的表現(xiàn)。“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區(qū)”,同其它合作組織一樣,其有效運行都需要相應(yīng)的合作機制來維系和保證。目前,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運行效率如何?合作機制之間表現(xiàn)出怎樣的關(guān)系?執(zhí)行機制的約束力和規(guī)范性如何?
從“空間結(jié)構(gòu)—治理模式”二元維度來看,邊界“屏蔽效應(yīng)”與制度壁壘對于我國省際邊界地區(qū)空間主體的分割或合作抑制現(xiàn)象非常普遍。“屏蔽效應(yīng)”限制了過境的客貨流、商品流、信息流、資本流等要素,對跨邊界合作產(chǎn)生一定的阻礙作用(Lopes,2003;Rose&van Wincoop,2001)。而附加調(diào)控功能的制度壁壘,間接影響了經(jīng)濟地理分布,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加劇了地方競爭或區(qū)域合作抑制,同時,地方官員晉升錦標(biāo)賽模式亦在合作空間分布的一般市場過程中打上行政印記,導(dǎo)致基于地緣空間結(jié)構(gòu)的省際次區(qū)域間的合作關(guān)系、合作模式變得愈發(fā)復(fù)雜(周黎安,2007;Peter Huber,2011;Coughlin&Novy,2013)。但同時,地理連續(xù)性減少了空間距離和運輸成本,邊界“中介效應(yīng)”使邊界地區(qū)作為域內(nèi)外經(jīng)濟、社會、文化聯(lián)系的重要口岸,增大了過境需求,進一步活躍了邊界兩側(cè)的要素流動(Lin Shaun,2012;李天籽,2014;何勝等,2014),從而提高合作效率。那么,“空間結(jié)構(gòu)—治理模式”雙重制約下的省際次區(qū)域?qū)Φ貐^(qū)合作體現(xiàn)的主要是“屏蔽效應(yīng)”還是“中介效應(yīng)”?顯著性如何?另一效應(yīng)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如何?
從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來看,經(jīng)典的“中心—外圍”空間結(jié)構(gòu)與地區(qū)分工與合作緊密相關(guān)(Krugman,1991;范劍勇,2013;趙勇,2015)[10],往往表現(xiàn)為“中心地區(qū)聚焦管理和研發(fā)功能,外圍地區(qū)聚焦制造和加工功能”(Duranton&Puga,2005;張若雪,2009;趙勇等,2012)。產(chǎn)業(yè)分工會擴大中心與外圍地區(qū)差距(Baldwin et al.,2003),地區(qū)差異引發(fā)梯度勢能釋放從而帶來溢出效應(yīng)和互補效應(yīng),促進地區(qū)合作加劇,并從對比關(guān)系角度影響合作模式;但有部分研究證明產(chǎn)業(yè)分工不會加劇地區(qū)差距(Head&Mayer,2006),同質(zhì)化的聚集規(guī)模效應(yīng)加強了地區(qū)間合作的強度。總結(jié)來看,在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的初期階段,梯度勢能和互補效應(yīng)使得區(qū)際合作空間得以釋放,但當(dāng)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達(dá)到某一臨界值時,隨著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的深化、同質(zhì)性的降低,規(guī)模效率損失會導(dǎo)致區(qū)際合作空間壓縮。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基礎(chǔ)上形成的“中心—外圍”格局與地區(qū)合作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guān)系嗎?如果存在,這種關(guān)系在邊界效應(yīng)作用下的省際次區(qū)仍然成立嗎?如果成立,省際次區(qū)域目前處在倒“U”型曲線的哪個階段?
從區(qū)域合作政策來看,相較于中心、重點區(qū)域,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政策相對滯后,而且主要適用于指令型的縱向治理模式。行政干預(yù)經(jīng)濟要素分布,宏觀調(diào)控地區(qū)差距、協(xié)調(diào)區(qū)域發(fā)展(陸銘等,2011;魏后凱,2014),這種政府主導(dǎo)的縱向治理結(jié)構(gòu)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地區(qū)合作的空間格局,并對其演變產(chǎn)生了顯著影響。因此,在弱化政府干預(yù)(范子英等,2010)、“軟化”制度壁壘,強化市場主體,減少行政邊界導(dǎo)致的效率損失的同時,要發(fā)揮“上級政府”在協(xié)調(diào)地區(qū)競爭、促進地區(qū)合作中的作用(Kline &Moretti,2014),通過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方式拓展省際次區(qū)域的橫向治理結(jié)構(gòu)。那么,一系列包括規(guī)制、投資、信貸、土地、產(chǎn)業(yè)、補貼、稅收、基建和環(huán)境等政策在內(nèi)的框架協(xié)議對以“空間結(jié)構(gòu)—治理模式”為基礎(chǔ)的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有何影響?如何評價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有效性?如何合理界定縱向指令與橫向框架協(xié)議界限,有效建立網(wǎng)絡(luò)化治理結(jié)構(gòu),適應(yīng)地區(qū)合作規(guī)律,提升地區(qū)合作效益與效率?
綜上所述,目前較少有文獻(xiàn)從省際、地區(qū)層面對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有效性及其內(nèi)在關(guān)系進行假設(shè)檢驗,同時也缺乏空間結(jié)構(gòu)、治理模式、產(chǎn)業(yè)差異、合作模式和區(qū)域政策等因素對其關(guān)系影響的實證分析,一系列相關(guān)問題有待回答。所以,本文將進一步探討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響應(yīng)性、協(xié)調(diào)性和互補性,揭示次區(qū)域合作在制約因素下的演化態(tài)勢,討論相關(guān)次區(qū)域合作政策能否有效支撐合作機制的正常運行,并為提升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效率、實現(xiàn)合作戰(zhàn)略目標(biāo)提出相應(yīng)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假設(shè)
(一)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響應(yīng)性與互補性
次區(qū)域合作的低行政成本和高度開放性使各方之間聯(lián)系日益緊密、專業(yè)化生產(chǎn)日益深化、各行為體的行為更區(qū)域化。一體化帶來旺盛過境需求的同時,促使行為主體在更大范圍內(nèi)拓展市場和尋求生產(chǎn)要素,而這些行為主體主要是各方的政府、企業(yè)和非政府組織等;動力是導(dǎo)致事物發(fā)展的原始力量,是次區(qū)域合作的根本原因,其形成與作用過程是揭示次區(qū)域合作規(guī)律、解決次區(qū)域合作問題、制定次區(qū)域合作戰(zhàn)略和政策的內(nèi)在機理。動力按來源不同可分為內(nèi)生動力和外生動力,其中內(nèi)生動力是次區(qū)域合作的決定因素,但內(nèi)生動力與外生動力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可以相互轉(zhuǎn)化;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利益共享與補償機制,能夠給予次區(qū)域合作足夠的“刺激”,“獎優(yōu)懲劣”,并實現(xiàn)利益轉(zhuǎn)移及合理分配,是次區(qū)域合作的保障性因素[2,11]。
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1:主體因素、內(nèi)部動力因素、外部動力因素和保障因素是次區(qū)域合作協(xié)同發(fā)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和組成部分,四項合作機制的聯(lián)合響應(yīng)與互補,將共同影響次區(qū)域健康發(fā)展,制約次區(qū)域合作效率。此外,合作機制在不同地區(qū)的響應(yīng)性與互補性將表現(xiàn)出顯著差異。
(二)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空間結(jié)構(gòu)—治理模式”二元性
次區(qū)域合作的結(jié)構(gòu)組織表現(xiàn)出“空間結(jié)構(gòu)—治理模式”二元維度,其運行效率會因二元交互的調(diào)節(jié)作用而有所差異。從空間結(jié)構(gòu)來看,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存在2種空間關(guān)系:地理鄰接和地理跨越;從治理模式來看,省際次區(qū)域合作也存在2種空間關(guān)系:省域內(nèi)合作和省域間合作。前者僅考慮了地理距離與運輸成本,后者還涉及了邊界效應(yīng)的影響——邊界閉合阻礙要素過境而表現(xiàn)為“屏蔽效應(yīng)”,邊界開啟促進接觸和交流而表現(xiàn)為“中介效應(yīng)”。地理距離與運輸成本的衰減會降低次區(qū)域合作交易成本,而邊界效應(yīng)通過信息對稱性、交易成本和制度壁壘影響次區(qū)域合作效率。同時,兩個次區(qū)域間是存在交叉區(qū)域的,即存在地區(qū)k∈S-Ri∩S-Rj(S-R表示次區(qū)域),次區(qū)域內(nèi)合作和次區(qū)域間合作締結(jié)成了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交叉區(qū)域”是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中資源聯(lián)系、共享和中轉(zhuǎn)的核心紐帶,其關(guān)鍵性取決于這種交叉地區(qū)在不同次區(qū)域內(nèi)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次區(qū)域間的“中介”作用的相對強弱[12-13]。
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2:地理跨越和制度壁壘會阻礙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構(gòu)建與演化;地理鄰接的省域內(nèi)合作將更有利于合作區(qū)的形成;“交叉區(qū)域”的“過境”和“中介”作用會弱化次區(qū)域制度壁壘,成為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中的“空間結(jié)點”,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次區(qū)域的空間拓展。
(三)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
功能分工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是影響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方之間博弈與協(xié)同多寡、競爭與配合強弱的關(guān)鍵因素。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分工、專業(yè)化水平和空間結(jié)構(gòu)能有效代表“中心聚焦管理和研發(fā)功能,外圍聚焦制造和加工功能”的格局。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專業(yè)化聚集帶來的規(guī)模效應(yīng)與空間異質(zhì)性演化產(chǎn)生的產(chǎn)業(yè)梯度勢能、互補性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在相對均質(zhì)的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初期,產(chǎn)業(yè)潛能異化帶來的梯度勢能與專業(yè)互補效應(yīng)大于專業(yè)化聚集的規(guī)模效應(yīng),次區(qū)域合作空間加快釋放,同時,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化能有效降低核心產(chǎn)業(yè)區(qū)的擁擠成本,使核心產(chǎn)業(yè)區(qū)的合作向心力進一步增強,從而擴大核心產(chǎn)業(yè)區(qū)與配套產(chǎn)業(yè)區(qū)之間的合作范圍與密度,體現(xiàn)出較強的空間依賴性;但是隨著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的逐步演化,空間異質(zhì)性過度導(dǎo)致要素資源的遷移速度不匹配、空間錯配,進而產(chǎn)生效率損失,將會不斷累加交易成本和協(xié)調(diào)成本,使得次區(qū)域合作的規(guī)模效應(yīng)降低,異質(zhì)性帶來的梯度勢能和互補效應(yīng)逐漸被不斷加大的交易成本和協(xié)調(diào)成本所抵消,次區(qū)域合作空間進一步被壓縮,特別是核心產(chǎn)業(yè)區(qū)的合作向心力有向合作離心力轉(zhuǎn)化的趨勢,導(dǎo)致次區(qū)域合作能力下降[14-15]。
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3:省際次區(qū)域合作與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不同次區(qū)域分處于U型曲線兩側(cè)。
(四)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模式的差異性
“中心-外圍”的空間結(jié)構(gòu)帶來地區(qū)差異,從對比關(guān)系角度影響了地區(qū)合模式。從合作雙方的對比關(guān)系角度,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模式有三種類型:強強型(S-S)、強弱型(S-W)和弱弱型(W-W)[16]。強強型合作,存在于兩側(cè)經(jīng)濟都相對較發(fā)達(dá)的地區(qū),為實現(xiàn)更大的次區(qū)域發(fā)展目的而選擇深層次的融合,在行政、經(jīng)濟、民政等多個方面進行權(quán)利再分配,并在貿(mào)易之外的文化、自然等“非經(jīng)濟領(lǐng)域”開展深度合作,以進一步發(fā)展和維護地區(qū)利益。因此,強強型合作的層次最深,也更容易開展,“長三角”、“珠三角”內(nèi)部副中心地區(qū)間廣泛合作以及發(fā)達(dá)國家間國際貿(mào)易的頻繁開展說明了這一點;強弱型合作,邊界兩側(cè)呈現(xiàn)較強的條件差異性。差異性是形成此類合作的出發(fā)點和重點,即“優(yōu)勢互補”:合作條件好的一側(cè)具有較強的技術(shù)、資金優(yōu)勢,另一側(cè)具有人工成本低、資源豐富等優(yōu)勢,從而促使其形成相應(yīng)的產(chǎn)業(yè)分工。尤其是對于具有“中心—外圍”結(jié)構(gòu)的次區(qū)域而言,邊界中心城市的發(fā)展與其輻射區(qū)域的發(fā)展具有緊密的互動關(guān)系,例如上海地區(qū)與長三角副中心城市間的合作;弱弱型合作,兩側(cè)均為較不發(fā)達(dá)地區(qū),故多以概念性合作為主,實質(zhì)性合作為輔,這種不以直接提高商貿(mào)為目的合作模式不太利于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形成[17-18]。另外從政治錦標(biāo)賽角度考慮,經(jīng)濟實力越是接近的邊界地區(qū),經(jīng)濟位次越模糊,政治競爭序列越接近,官員晉升競爭對合作發(fā)展的影響越不利,反之,地區(qū)實力差異越大,經(jīng)濟位次越清晰,政治競爭序列越疏離,聯(lián)合開發(fā)受官員晉升競爭的影響越小[19]。
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4:強弱型的地區(qū)合作模式因“中心—外圍”結(jié)構(gòu)的“互補優(yōu)勢”、“輻射—承接”效應(yīng)以及在政治錦標(biāo)賽中的“趨利避害”,更有利于次區(qū)域合作的開展。強強型地區(qū)合作模式雖然受制于政治錦標(biāo)賽,但要素稟賦的“空間規(guī)模效應(yīng)”亦能促進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形成。
(五)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有效性
區(qū)域合作協(xié)議是我國區(qū)域發(fā)展與治理實踐中出現(xiàn)的一種新型獨立的公法治理規(guī)范。不是簡單的行政契約或者具有軟法效力。其復(fù)雜性,特殊性及合作與績效共享的理念,明顯有別于傳統(tǒng)的政府治理模式。通過地區(qū)間戰(zhàn)略合作框架協(xié)議,將次區(qū)域合作制度化,可以進一步降低或消除邊界屏蔽效應(yīng),進一步開放、減少或消除交易成本,對一體化及次區(qū)域合作更深入發(fā)展提供制度保障[20]。如《內(nèi)地與香港更緊密的經(jīng)貿(mào)安排》的制定,打開新型深入合作關(guān)系,為香港、澳門、內(nèi)地產(chǎn)業(yè)升級優(yōu)化、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更優(yōu)化的運行環(huán)境。但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框架協(xié)議無論在內(nèi)容細(xì)化,推行時間和治理空間上都尚不成熟,制度文本過于“年輕”,并且在官員晉升考核中所能發(fā)揮的積極協(xié)調(diào)作用有待觀察,其政策有效性尚需進一步論證與檢驗。
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5:省際次區(qū)域的合作框架協(xié)議并不能“立竿見影”,對邊界屏蔽效應(yīng)和制度壁壘的“削弱”和“軟化”作用有限,對政治錦標(biāo)賽的協(xié)調(diào)作用不明晰,尚不能成為次區(qū)域合作區(qū)形成與演化的重要“推手”。
三、研究設(shè)計
針對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發(fā)展的制約因素、合作模式以及運行環(huán)境的特點,從合作機制、合作模式及運行環(huán)境等方面設(shè)置變量,運用面板回歸模型探討相關(guān)變量之間的影響關(guān)系及內(nèi)生機理[21-24]。
(一)研究樣本
根據(jù)上文理論剖析,結(jié)合次區(qū)域合作的空間組織形式和結(jié)構(gòu)特征,本文將省際次區(qū)域界定為內(nèi)地各省沿邊地區(qū)及其毗鄰的周邊地區(qū),并以中部省際次區(qū)域為例。《“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在推進長江經(jīng)濟帶發(fā)展中,明確提出建設(shè)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合作區(qū);《促進中部地區(qū)崛起“十三五”規(guī)劃(2016)》中指出要深化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地區(qū)合作,推進湘贛開放合作試驗區(qū)等省際毗鄰地區(qū)合作發(fā)展;《長江中游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2015)》提出促進省際毗鄰城市組團發(fā)展,加快建設(shè)“咸寧—岳陽—九江”等產(chǎn)業(yè)協(xié)作區(qū)、合作示范區(qū)[5-6,25-28]。綜合以上分析,本文界定了7個具有典型特征的中部省際次區(qū)域,詳見圖1。同時,通過制約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主體因素(Sub)、內(nèi)部動力因素(Int)、外部動力因素(Ext)和保障因素(Sec)的綜合得分Zi,t=f(Subi,t,Inti,t,Exti,t,Seci,t),來反映地區(qū)之間合作條件的強弱*地區(qū)合作條件的綜合得分指標(biāo)體系共4個二級指標(biāo),16個三級指標(biāo),由于篇幅所限,詳細(xì)測度過程略去,具體指標(biāo)參見表1。。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部地區(qū)7個典型省際次區(qū)域,包括20個地級市、6個縣(區(qū))及1個縣級林區(qū),從次區(qū)域和地區(qū)兩個空間維度確立樣本。需要指出的是,縣與地區(qū)規(guī)模不相當(dāng),為統(tǒng)一數(shù)據(jù)口徑,將重慶六縣假設(shè)為“渝東地區(qū)”,宜昌、神農(nóng)架林區(qū)假設(shè)為“宜神地區(qū)”,都視作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的一個地區(qū)。
(二)模型構(gòu)造及變量描述
1.基礎(chǔ)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多個地區(qū)的樣本配對問題。根據(jù)理論假設(shè),以地區(qū)間經(jīng)濟聯(lián)系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主體機制、內(nèi)部動力機制、外部動力機制和保障機制的合作差異性指數(shù)為解釋變量,建立面板回歸模型。為了增強回歸的穩(wěn)健性,采用逐步回歸和分區(qū)域回歸方法進行檢驗,對數(shù)化的處理是為了保持?jǐn)?shù)據(jù)的平穩(wěn)性和消除異方差。次區(qū)域合作是一種動態(tài)演變過程,同時考慮到運行環(huán)境因素與地區(qū)合作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guān)系,建立以下形式的動態(tài)面板回歸模型①:

圖1 7個典型的中部省際次區(qū)域



(1)
(2)
式中,i、j代表次區(qū)域或地區(qū);t代表年份;α0-αθ為待估參數(shù),εijt為殘差項;GDP為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Dij為i、j兩地之間的空間距離,主要通過次區(qū)域或城市之間直線距離來度量,距離來自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Google Earth的測量;G為引力常數(shù),一般為1;[ln(H-tCPij,t)]2為二次項,反映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在不同階段對地區(qū)合作的影響②;Xijt為一組控制變量。
2.模型改進
以上基礎(chǔ)模型掩蓋了次區(qū)域間合作模式的異質(zhì)性,忽略了地區(qū)間的相對關(guān)系。交叉地區(qū)是兩次區(qū)域間資源聯(lián)系、共享和中轉(zhuǎn)的核心紐帶。此外,不同的地區(qū)合作模式,對次區(qū)域合作形成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因此,本文以弱弱型合作為參照,將區(qū)域交叉性以及次區(qū)域內(nèi)合作模式的差異性引入模型中,將模型調(diào)整為:
(3)
式中,i、j代表次區(qū)域或地區(qū);t代表年份;α0為常數(shù)項,α1-αθ,β1和γ1、γ2為待估參數(shù),εij,t為殘差項。全部解釋變量設(shè)置見表1[29-32]。
② 金融發(fā)展指數(shù)=金融機構(gòu)存貸款余額之和÷GDP。

表1 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回歸模型變量設(shè)置
(三)數(shù)據(jù)來源

四、計量檢驗與結(jié)果分析
在進行回歸之前,本文首先對面板數(shù)據(jù)進行了Hausman檢驗。經(jīng)檢驗,回歸均支持采用固定效應(yīng)模型。針對上述改進的模型與相關(guān)變量指標(biāo),本文采用Eviews8.0軟件進行估計,得出模型整體的擬合優(yōu)度較好,模型總體顯著性較強,同時在模型中對所有變量做了滯后一期處理,并對回歸結(jié)果進行了穩(wěn)健性檢驗。表2至表4為詳細(xì)的模型參數(shù)估計結(jié)果。
(一)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回歸分析
1.合作機制的響應(yīng)性與互補性對于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影響
本文分析認(rèn)為,從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研究結(jié)果看,動力機制中內(nèi)源機制和外源機制的互補性較好地解釋了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成因,而且這兩個變量無論在“次區(qū)域”層面還是在“地區(qū)”層面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尤其是內(nèi)部動力機制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但主體機制和保障機制的互補性顯著性不強,未能通過檢驗,說明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主體機制和保障機制的同步性較低,存在互動脫節(jié)現(xiàn)象。所以,本文進一步考察主體機制和保障機制之間的互補性對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影響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為此,引入二者的交互項,結(jié)果表明,地區(qū)間保障機制的系數(shù)仍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主體機制和保障機制交互項顯著為負(fù),由此可得,當(dāng)前主體機制對保障機制的提升效應(yīng)不足,響應(yīng)機制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優(yōu)化。
由分域回歸的結(jié)果可得,各次區(qū)域的標(biāo)準(zhǔn)化系數(shù)和t統(tǒng)計量以及顯著性水平具有較大差異,說明在作用方式、作用方向和作用強度上,四項合作機制及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對各次區(qū)域地區(qū)合作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主體機制與內(nèi)部動力機制的互補性不強,行為主體對次區(qū)域合作進程中內(nèi)部市場活力的釋放有限,進一步說明,政府等合作行為主體未能充分發(fā)揮主導(dǎo)作用;而不斷深入的市場化改革使得這一活力得以充分釋放,由此產(chǎn)生的對次區(qū)域地區(qū)合作的正向促進作用比較突出,內(nèi)部動力機制在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地區(qū)合作發(fā)展中扮演了關(guān)鍵角色;次區(qū)域的民營經(jīng)濟發(fā)育不良,市場發(fā)展滯后、不健全,對外開放程度偏低、缺乏吸引力,實際有效利用外資規(guī)模不足,導(dǎo)致外部動力對次區(qū)域合作的拉動乏力,有效的外部動力合作制尚未形成,需要進一步整合對外資源,以促進合作區(qū)形成與發(fā)展;保障機制應(yīng)對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地區(qū)合作產(chǎn)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未證實這一假設(shè),可解釋為,現(xiàn)階段中部省際次區(qū)域激勵和約束機制尚未成型,存在機制真空地帶,使得保障機制對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產(chǎn)生的促進作用尚不明確。
2.邊界效應(yīng)、資源配置效率與制度壁壘
在地區(qū)邊界效應(yīng)因素上,變量Bor顯著為負(fù)(1%水平顯著),表明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強烈受到邊界“屏蔽效應(yīng)”的影響。行政區(qū)劃使得中部地區(qū)地方政府更為關(guān)注本轄區(qū)內(nèi)的合作發(fā)展而忽略了地區(qū)間合作的互動。引入邊界效應(yīng)與外部動力機制的交互項進一步解釋了阻礙跨界次區(qū)域合作有效推進的根源在于資源要素在區(qū)域間再配置存在障礙,尤其是外部資源在本地區(qū)的配置效率明顯被邊界削弱。這就要求行政制度、管理制度等制度變革和合作利益共享與補償機制設(shè)計等政策創(chuàng)新。本文又考察了地區(qū)間的制度壁壘因素,而這恰好又是現(xiàn)階段限制制度變革和政策創(chuàng)新的重難點,模擬結(jié)果顯著為負(fù),說明由于行政干預(yù)的存在,制度變革乏力、政策創(chuàng)新缺失,從而阻礙了合作機制在跨省份次區(qū)域的形成和發(fā)展,省域內(nèi)次區(qū)域合作效率明顯高于省際間,而這也進一步形成“倒逼機制”,迫使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空間演化亟須由傳統(tǒng)行政區(qū)劃治理結(jié)構(gòu)向跨行政區(qū)合作治理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

表2 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全域回歸結(jié)果
注:***,**,*分別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nèi)為t值。
3.地理鄰接性、空間交叉性與空間拓展性
列(3)中,對于地理鄰接效應(yīng)的估計結(jié)果為3.464,并表現(xiàn)出1%的顯著性水平,反映出地理鄰接效應(yīng)有助于次區(qū)域合作的形成與發(fā)展。地理鄰接相較于地理跨越產(chǎn)生的運輸成本下降與規(guī)模效益遞增,是次區(qū)域合作演化的重要內(nèi)在機制。本文中,地理鄰接性既可表現(xiàn)為省內(nèi)相鄰亦可表現(xiàn)為省際相鄰,由上文分析可知,次區(qū)域合作空間邊界拓展過程中,往往會受制于邊界的屏蔽效應(yīng)和制度壁壘的阻隔,使得次區(qū)域合作空間組織形式“沿邊痕跡”明顯。然而,當(dāng)開啟的邊界表現(xiàn)出“中介效應(yīng)”時,制度壁壘被軟化,勢必會出現(xiàn)一個次區(qū)域向相鄰次區(qū)域拓展的趨勢,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的交叉,使得“交叉地區(qū)”成為次區(qū)域間資源聯(lián)系、共享和中轉(zhuǎn)的“空間結(jié)點”,弱化了邊界的閉合功能而強化了過境功能。因此本文進一步引入變量Cro來考察這一交叉性的影響程度。由列(1)可以發(fā)現(xiàn)次區(qū)域交叉性變量顯著為正(2.491),表明邊界地區(qū)的空間交叉性能正向促進次區(qū)域間的合作能力,弱化了邊界屏蔽和制度壁壘的阻隔作用而進一步論證了本文的上述觀點。然而這一影響系數(shù)較低,顯著性也并不強,說明盡管空間交叉的邊界地區(qū)在次區(qū)域合作形成過程中存在一定的中介作用,但對邊界屏蔽和制度壁壘等不利因素的抑制作用有限。
雖然如此,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的“空間結(jié)點”對合作關(guān)系影響的關(guān)鍵取決于“交叉地區(qū)”在不同次區(qū)域內(nèi)扮演的“角色”以及“中介效應(yīng)”的相對強弱。如位列合作強區(qū)的交叉地區(qū)(岳陽和九江),由于存在不同次區(qū)域間的合作會引發(fā)經(jīng)濟地位改變的可能性,使得地方對于鄰近次區(qū)域有正向溢出效應(yīng)的合作決策激勵不足,因此交叉地區(qū)的“中介”作用相對較弱,其空間邊界拓展趨勢并不明顯;而“由弱變強”的交叉地區(qū)(黃岡、安慶和荊州)迫切尋求提升經(jīng)濟地位、加強合作參與,表現(xiàn)為更積極的拓展決策傾向,這也符合錦標(biāo)賽理論的觀點。因此,從加強資源流通、共享與整合角度出發(fā),有必要對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空間拓展性做進一步的政策引導(dǎo)與加強。
4.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與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倒“U”型關(guān)系
回歸結(jié)果中,列(1)至列(5)表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為正,而其二次項的回歸系數(shù)則為負(fù),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與次區(qū)域之間合作以及次區(qū)域內(nèi)部的地區(qū)合作呈倒“U”型關(guān)系,即隨著區(qū)域間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的演化,次區(qū)域間合作以及次區(qū)域內(nèi)地區(qū)合作效應(yīng)會顯著提升,但空間異質(zhì)性跨過轉(zhuǎn)折點后,區(qū)域合作效應(yīng)會呈現(xiàn)縮小趨勢。進一步測算得出,次區(qū)域樣本中,僅有7個處于拐點右側(cè),地區(qū)樣本中,僅有60個處于拐點的右側(cè),表明大多數(shù)樣本仍處于區(qū)域合作會隨著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擴大而進一步提升的階段。
5.制度壁壘、合作框架協(xié)議治理與邊界重塑
區(qū)域合作協(xié)議是區(qū)域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制度形式,是合作主體重塑邊界的重要范式之一,從屬于我國區(qū)域發(fā)展總體戰(zhàn)略框架,其推手或締結(jié)者往往是該區(qū)域內(nèi)的相關(guān)政府或政府職能部門。如三大經(jīng)濟圈等都簽訂了數(shù)量龐大的各類合作協(xié)議,由此產(chǎn)生的示范效應(yīng)使得中部省際次區(qū)域也簽訂了一批類似框架協(xié)議。為了描述這種框架協(xié)議治理約束帶來的邊界重塑對次區(qū)域合作的作用機理,本文將CFA變量引入模型,結(jié)果顯示合作框架協(xié)議治理約束對于次區(qū)域合作的正向作用并不理想,僅僅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邊界重塑效果不佳。這可以解釋為次區(qū)域內(nèi)治理約束形成初期,僅僅表現(xiàn)為一種行政契約或者僅具有軟法效力,很難形成比較有效的政府合作或績效共享溢出效應(yīng)。再引入其與制度壁壘的交互項,來識別其與“硬法”的相互作用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合作框架“軟約束”對于制度壁壘“硬約束”的軟化作用顯著為負(fù),進一步論證了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效力局限性。但不這并不意味著這種邊界重塑范式不能改善次區(qū)域合作的“沿邊痕跡”,協(xié)議的“落地”、“生根”和“發(fā)芽”需要一定時間,需要一系列持續(xù)的政策創(chuàng)新,這也符合當(dāng)前國家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改革的要求。
(二)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地區(qū)合作模式的探討
從空間結(jié)構(gòu)來看,次區(qū)域內(nèi)的地區(qū)組合可以更有效地形成地區(qū)合作,然而這可能僅是一般性的結(jié)論,為繼續(xù)挖掘次區(qū)域內(nèi)地區(qū)合作模式的演化方式,本文把地區(qū)合作條件相對強弱屬性引入模型(按合作條件綜合得分50%分位數(shù)劃分強區(qū)與弱區(qū)),并將弱弱行合作模式作為參考,在模型中分別引入2個虛擬變量(Coop1和Coop2)與S-R的交互項來做進一步探究[16]。全域回歸結(jié)果表明,同一次區(qū)域內(nèi),強強型合作區(qū)(S-S型)與強弱型合作區(qū)(S-W型)的綜合系數(shù)均顯著為正,相比較而言,強弱型合作區(qū)的綜合系數(shù)較高(2.247),而強強型合作區(qū)的綜合系數(shù)較低(1.820),顯著性也弱。說明強弱型與強強型較弱弱型都能促進次區(qū)域合作的形成,但強弱型模式更有利于次區(qū)域合作開展。為了進一步解釋究竟是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還是政治錦標(biāo)賽阻礙了“強強聯(lián)合”、促成了“強弱搭配”,引入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與合作模式交互項。回歸結(jié)果可得,在產(chǎn)業(yè)異構(gòu)顯著性下,強弱型合作模式與產(chǎn)業(yè)異構(gòu)交互項顯著為正,而強強型與產(chǎn)業(yè)異構(gòu)交互項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產(chǎn)業(yè)異構(gòu)情形下,強弱型合作模式較強強型與弱弱型更能促進地區(qū)合作,可推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相似不是阻礙“強強聯(lián)合”或“弱弱組對”的因素,更加合理地解釋是政治錦標(biāo)賽影響了地區(qū)合作模式的格局。

表3 地區(qū)合作模式全域回歸結(jié)果
注:***,**,*分別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nèi)為t值。
通過分域回歸可以發(fā)現(xiàn),強弱型合作模式的有效性更加明顯。由“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的合作模式回歸結(jié)果中可知,強強型合作模式均對次區(qū)域合作無顯著性影響,而強弱型合作模式的影響具有較高顯著性,表明岳陽和九江“強強聯(lián)合”的空間結(jié)構(gòu)效應(yīng)并不能促進該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形成與發(fā)展,而“岳-咸”和“九-咸”的“強弱對話”則提升了次區(qū)域合作的整體質(zhì)量,從這一點來看,地區(qū)合作模式的分區(qū)域回歸結(jié)果與全域回歸結(jié)果是相吻合的。
(三)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演化趨勢及政策有效性
從上文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空間拓展模式來看,中部地區(qū)7個典型次區(qū)域的合作仍然處于區(qū)域內(nèi)部拓展階段。因此,本文側(cè)重于研究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域內(nèi)拓展。為此,本文分別對中部地區(qū)7個典型省際次區(qū)域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結(jié)果見表4。
1.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的演化路徑
四項合作機制均正向顯著的次區(qū)域為“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和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說明這2個次區(qū)域已經(jīng)形成了有效的內(nèi)部合作區(qū),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第一階段構(gòu)建基本完成,本文將其認(rèn)定為“次區(qū)域合作示范區(qū)”。同時,這兩個次區(qū)域均形成了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與地區(qū)合作的倒“U”型關(guān)系,經(jīng)過測算,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已經(jīng)邁過拐點,進入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縮小有利于次區(qū)域合作區(qū)提升的階段,“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接近拐點,其跨越拐點的時間不會太長;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黃河金三角次區(qū)域、環(huán)大別山次區(qū)域和“九-黃-黃”跨江次區(qū)域四項合作機制中至少有一項未能響應(yīng),本文將其認(rèn)定為“次區(qū)域合作推動區(qū)”,其中最有可能形成合作示范區(qū)的是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除保障機制以外的其它3項合作機制均正向顯著。因此,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應(yīng)著重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從而完成向合作示范區(qū)的轉(zhuǎn)換。其它4個次區(qū)域合作推動區(qū)合作機制均不健全,也未呈現(xiàn)出明顯的邊界重塑趨勢,所以要針對各自缺失的合作機制進行“精準(zhǔn)提升”,全面促進合作示范區(qū)的形成;而“九—安—池—景”經(jīng)濟次區(qū)域合作機制均未通過檢驗,將其認(rèn)定為“次區(qū)域合作滯后區(qū)”,說明有效的合作機制尚未形成,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缺失,合作區(qū)建設(shè)仍停留在理論論證或政策醞釀階段,需要更具體、更精確的“孵化”和“培育”措施。

表4 分區(qū)域回歸結(jié)果
注:***,**,*分別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①-⑦分別代表黃河金三角次區(qū)域、環(huán)大別山核心次區(qū)域、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合作次區(qū)域、“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九-黃-黃”跨江次區(qū)域、“九-安-池-景”經(jīng)濟次區(qū)域和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
2.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有效性
從合作框架協(xié)議有效性來看,控制變量CFA在黃河金三角次區(qū)域、“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和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均正向顯著,但引入CFA與制度壁壘的交互項后發(fā)現(xiàn),均顯著為負(fù),表明合作框架協(xié)議對于相應(yīng)次區(qū)域合作發(fā)展具有拉動力,但動力不足。如《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區(qū)域合作規(guī)劃(2014)》、在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構(gòu)建上,針對外部機制與保障機制的制度設(shè)計和政策創(chuàng)新不足,使得這2項因素制約了該次區(qū)域從合作推動區(qū)向合作示范區(qū)的轉(zhuǎn)換。《湖南省岳陽市、江西省九江市、湖北省咸寧市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2012)》和《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區(qū)規(guī)劃2012》推動了“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和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合作示范區(qū)的形成,但對于制度壁壘的削弱并未達(dá)到重塑邊界的“高級階段”,制度壁壘帶來的影響依舊顯著,所以應(yīng)進一步加強這些地區(qū)之間以及同次區(qū)域外部地區(qū)的聯(lián)系,進而促進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邊界向域外拓展,由合作示范區(qū)向合作邊界重塑階段演化。相比之下,其它4個次區(qū)域的CFA變量及其同制度壁壘的交互項均顯著為負(fù),據(jù)此可推斷:三峽生態(tài)經(jīng)濟合作區(qū)所推行的“宜昌試驗”尚未處于推廣階段,惠及整個次區(qū)域的合作框架協(xié)議并未具體出臺;《推進大別山革命老區(qū)振興發(fā)展戰(zhàn)略合作框架協(xié)議(2015)》和《關(guān)于共同支持九江市與黃岡市跨江合作的框架協(xié)議(2013)》對于環(huán)大別山次區(qū)域合作推動區(qū)和“九-黃-黃”跨江次區(qū)域合作推動區(qū)的促進作用有待加強;“九—安—池—景”次區(qū)域合作滯后區(qū)缺乏針對各自制約因素的合作框架協(xié)議,屬于區(qū)域合作框架的真空地帶。
五、結(jié)論及建議
(一)提升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機制的響應(yīng)性和互補性
由于“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形成是多項內(nèi)外部機制協(xié)同合作的結(jié)果,因此,需要統(tǒng)籌“四項機制,產(chǎn)業(yè)布局和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戰(zhàn)略組合,提升主體機制,特別是保障機制在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合作中的響應(yīng)性[33]。其次是要明確各個次區(qū)域中,不同機制在合作過程中的功能定位,根據(jù)其功能差異,進行“精準(zhǔn)完善”。主體機制與動力機制、保障機制間的互補性是提升省際次區(qū)域合作水平的又一關(guān)鍵問題,實證檢驗中,主體機制與動力機制的互補性一般顯著,有待進一步提升,而與保障機制之間未體現(xiàn)出互補性,因此有必要加強合作機制間的橫向聯(lián)系:第一,建立地區(qū)聯(lián)席會議制度和次區(qū)域合作工作推進制度,定期召開,集體協(xié)商、統(tǒng)一部署合作機制中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第二,通過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治理模式,促進政府主體機制完善[34];第三,積極承接區(qū)域外部 “合作示范區(qū)”的示范效應(yīng);第四,完善激勵與約束機制,通過法律、法規(guī)、政策等制度安排規(guī)范“游戲規(guī)則”,做到“獎罰分明”;第五,“無縫銜接”利益共享與補償機制,協(xié)調(diào)利益矛盾,豐富、創(chuàng)新多種利益分配與補償手段,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問題;第六,加快中部地區(qū)次區(qū)域合作中融創(chuàng)機制建設(shè),尤其在合作開發(fā)項目的形成、投融資、風(fēng)險管控、驗收獎勵機制上要敢于創(chuàng)新。
(二)市場主導(dǎo),行政推動,積極合作,有序競爭
“次區(qū)域合作區(qū)”是跨區(qū)域的空間組織形式,存在較大的制度性障礙,不利于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的開展。因此,對于“跨省域次區(qū)域”發(fā)展,建議由國家級行政機構(gòu)牽頭設(shè)立跨省級層面的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而對于“省域內(nèi)次區(qū)域”,建議由省級政府牽頭設(shè)立跨市級層面的協(xié)調(diào)機構(gòu),通過“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弱化行政區(qū)劃界限與制度壁壘,強化橫向?qū)优c聯(lián)系[35]。堅持注重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營造“統(tǒng)一開放、競合有序”的市場氛圍,加快完善商品和要素市場體系,保障市場公平,規(guī)范市場秩序,降低合作交易成本,積極發(fā)展跨地區(qū)的商會、行業(yè)協(xié)會等非政府組織,強化其主體地位,為跨地區(qū)經(jīng)貿(mào)活動的開展提供支持和服務(wù)。與此同時,理順政府與市場關(guān)系,市場無法有效解決的重大基礎(chǔ)設(shè)施、公共服務(wù)等,依然需要通過行政的力量來推動,推動方式應(yīng)是市場經(jīng)濟手段而非行政指令,以人為本,合理引導(dǎo)市場力量,避免“矯枉過正”,讓市場機制和價值規(guī)律始終貫穿于合作發(fā)展的全過程。通過“市場主導(dǎo)、行政推動、積極合作、有序競爭”的次區(qū)域合作治理結(jié)構(gòu),不斷改善資源空間配置效率[36],協(xié)調(diào)好次區(qū)域之間及次區(qū)域內(nèi)部的收益和成本分擔(dān)補償,實現(xiàn)帕累托改進,全面推進省際次區(qū)域的追趕式發(fā)展。
(三)重塑邊界,編織空間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
次區(qū)域合作的空間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演化是一個逐漸由簡單向復(fù)雜、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fā)展的過程,空間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演化不僅是合作方內(nèi)部要素的增加和空間范圍的拓展,更重要的是系統(tǒng)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功能的優(yōu)化升級。借鑒長三角、珠三角的成功經(jīng)驗,對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進行高水平的頂層設(shè)計,破除次區(qū)域“原有邊界”的封鎖和壁壘,修補市場分割導(dǎo)致的“沿邊痕跡”,重塑邊界,在確定7個典型的中部省際次區(qū)域作合作區(qū)基礎(chǔ)上,繼續(xù)擴大次區(qū)域合作承接地范圍,實現(xiàn)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有效空間拓展:如構(gòu)建“‘長株潭’-‘新宜萍’”湘贛開放合作區(qū),將安慶納入“咸-岳-九”小三角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等。同時,充分認(rèn)識各節(jié)點的比較優(yōu)勢、缺陷短板和成長機會,處理好節(jié)點成員之間的角色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空間交叉”在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中的功能定位,使得九江、岳陽等城市不僅作為“窗口”和“貿(mào)易通道”,更是工業(yè)和服務(wù)業(yè)集聚中心[11]。加強“空間交叉”地區(qū)之間以及與其他地區(qū)間的多元化、專題化、常態(tài)化的“互動,互訪,互進,互助”。并且將省際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示范效應(yīng)擴散至整個中西部地區(qū),形成合理、密集、交錯的次區(qū)域合作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
(四)優(yōu)化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格局,形成最優(yōu)合作“勢差”
本文研究證實,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次區(qū)域已經(jīng)邁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的拐點,進入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縮小更有利于促進次區(qū)域合作的階段。針對這類次區(qū)域合作區(qū),應(yīng)更多地開展產(chǎn)業(yè)鏈內(nèi)的產(chǎn)品精細(xì)分工合作,而對于正在接近或距離拐點仍有距離的次區(qū)域合作區(qū),仍要以產(chǎn)業(yè)鏈分工為主。中部省際次區(qū)域,應(yīng)主動承接具有外部示范作用的武漢城市圈、皖江經(jīng)濟帶等區(qū)域中心釋放的產(chǎn)業(yè)梯度勢能,打造優(yōu)勢產(chǎn)業(yè)集群,推進跨次區(qū)域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與承接,建立產(chǎn)業(yè)協(xié)同發(fā)展機制。同時,“次區(qū)域合作示范區(qū)”應(yīng)憑借完善的基礎(chǔ)設(shè)施、優(yōu)越的地理條件、較好的工業(yè)基礎(chǔ)、較高的生產(chǎn)要素集聚,成為次區(qū)域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合作的溢出中心,而“合作推動區(qū)”和“合作滯后區(qū)”則應(yīng)積極承接產(chǎn)業(yè)鏈和人才鏈的雙轉(zhuǎn)移,利用溢出中心帶來的正外部性不斷完善自身的產(chǎn)業(yè)合作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合作“勢差”。
(五)完善官員激勵,協(xié)調(diào)地區(qū)發(fā)展,探索適宜合作模式
由地區(qū)合作模式實證結(jié)果可知,“強弱搭配”更有利于次區(qū)域合作的形成,而“強強聯(lián)合”的效果并不強,產(chǎn)業(yè)異質(zhì)性并不能較好地解釋,很可能是由于地方經(jīng)濟考核的晉升機制負(fù)面效應(yīng)在次區(qū)域合作中有所體現(xiàn),而這一阻礙作用更多來自于省級層面,因此改善以地方經(jīng)濟績效為標(biāo)準(zhǔn)的省級官員激勵機制,有利于邊界合作模式的豐富。此外,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往往是經(jīng)濟欠發(fā)達(dá)、發(fā)展不平衡、集中連片貧困、民族聚集或生態(tài)脆弱敏感地區(qū),所以協(xié)調(diào)區(qū)域發(fā)展,加快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信息化和城鎮(zhèn)化的同步進程,落實中部地區(qū)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shè),成為有效支撐次區(qū)域合作、降低區(qū)域發(fā)展差異的首要任務(wù)。現(xiàn)階段,中部省際次區(qū)域呈現(xiàn)大、中、小城市“混搭”的格局,應(yīng)根據(jù)本區(qū)域的實際,統(tǒng)籌規(guī)劃新型城鎮(zhèn)化和城鄉(xiāng)一體化,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區(qū)合作路徑:對發(fā)展困難的小城鎮(zhèn),可采取與大城市同城化合作發(fā)展模式,如“九江-小池”地區(qū),是“以大帶小,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代表;區(qū)位不利的地區(qū),可積極探索就近城鎮(zhèn)化;此外,對于產(chǎn)業(yè)同質(zhì)地區(qū),也可以從資源互補和優(yōu)勢互補角度,形成具有“競合有序”的合作關(guān)系,實現(xiàn)“共贏”。
(六)落實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支撐網(wǎng)絡(luò)化治理結(jié)構(gòu)
中國經(jīng)濟增長階段的轉(zhuǎn)換,使得次區(qū)域合作與分工的宏觀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進一步要求建立完善合作與協(xié)調(diào)的橫向治理結(jié)構(gòu),使次區(qū)域發(fā)展由行政指令性的縱向治理結(jié)構(gòu)為主,向縱橫向交錯的網(wǎng)絡(luò)治理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地區(qū)間戰(zhàn)略合作框架協(xié)議即是在對一體化與網(wǎng)絡(luò)治理結(jié)構(gòu)提供制度保障的客觀需要條件下產(chǎn)生,成為次區(qū)域間進一步開放市場,打通制度壁壘,減少或消除交易成本的制度文本。然而,本文實證結(jié)果證實了之前的理論假設(shè),即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尚不能有效支撐次區(qū)域合作區(qū)的進一步“升級”,其邊界重構(gòu)效應(yīng)不顯著,因此,要進一步提升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政策有效性,促進協(xié)議的“落地生根,開花結(jié)果”。第一,加強次區(qū)域內(nèi)和次區(qū)域間的互聯(lián)互通,降低時空距離對次區(qū)域一體化合作與分工的制約;第二,細(xì)化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內(nèi)容條款并監(jiān)督落實,建立協(xié)議政策有效性的科學(xué)評價機制和“行政—績效”的雙重考核機制;第三,以“一帶一路”和邊界開放開發(fā)為帶動,通過積極參與區(qū)域合作,消除邊界分割,加快推進次區(qū)域橫向治理結(jié)構(gòu)的構(gòu)建;第四,從法理角度出發(fā),將次區(qū)域合作框架協(xié)議推演為一種走向合作與共享的新型公法治理模式。
參考文獻(xiàn):
[1]Hanson G H.U.S.-Mexico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es:evidence from border-city pair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1(50): 259-287.
[2]Yu Xiao Jia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J]. Energy Policy, 2003 (31) :1221-1234.
[3]Taguch H, Oizumi K. Trade Integration of yunnan and guangxi with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re-visited[J]. China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14,3(1):1-14.
[4]Ngepah N 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ub-region[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4,31(3): 494-514.
[5]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長江中游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Z].2015-04.
[6]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促進中部地區(qū)崛起“十三五”規(guī)劃[Z].2016-12.
[7]李鐵立,姜懷宇. 次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機制研究:一個邊界效應(yīng)的分析框架[J]. 東北亞論壇,2005,14(3):90-94.
[8]梁雙陸,陳 瑛. 次區(qū)域國際經(jīng)濟一體化中的產(chǎn)業(yè)地域性聚集機理研究[J]. 南方經(jīng)濟2012(9):143-155.
[9]Oehlers, Alfred.A critique of ADB policies towards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06,36(4):464-478.
[10]Mukherjee K.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14 (4) :373-381.
[11]Batjargal, Hitt, Tsui, et al.Institutional polycentrism,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4):1024-1049.
[12]Jacobs,Joren. Spatial planning in cross-border regions: A systems-theoretical perspective[J].Planning Theory,2016,15(1):68-90.
[13]牛沖槐,張 帆,封海燕. 科技型人才聚集、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聚集與區(qū)域技術(shù)創(chuàng)新[J]. 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29(15):46-51.
[14]謝呈陽,周海波,胡漢輝. 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中要素資源的空間錯配與經(jīng)濟效率損失[J]. 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14(12):130-142.
[15]Gomez G, Teresa, Gualda, et al. Reporting a bottom-up political process: local perception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ern portugal-spain region[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2016,23(3):468-480.
[16]周黎安,陶 婧.官員晉升競爭與邊界效應(yīng):以省區(qū)交界地帶的經(jīng)濟發(fā)展為例[J]. 金融研究,2011(3):15-26.
[17]Pysz K, Joanna. Opportunities for cross-borde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a cluster model exemplified by the polish-czech border region[J].Sustainability, 2016,8(3) :21.
[18]Lee C, Fukunaga Y. ASEAN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competition polic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4 (35): 77-91.
[19]周黎安. 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biāo)賽模式研究[J]. 經(jīng)濟研究,2007(7):36-50.
[20]Han Cai Zhen, Shi Yin Hong. Bottle neck s in east asia’s regional cooperation[J]. CIR ,2014,24(3):29-37.
[21]李天放,馮 鋒. 跨次區(qū)域技術(shù)轉(zhuǎn)移網(wǎng)絡(luò)測度與治理研究——基于共生理論視角[J]. 科學(xué)學(xué)研究, 2013,31(5):684-692.
[22]游士兵,蘇正華,王 婧. “點-軸”系統(tǒng)與城市空間擴展理論在經(jīng)濟增長中引擎作用實證研究[J]. 中國軟科學(xué), 2015(4): 142-154.
[23]龔勝生,張 濤,丁明磊,等.長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機制研究[J]. 中國軟科學(xué),2014(1):96-104.
[24]Lin Shaun.Dynamics of cross bord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mekong sub-region: a case study of thailand[J].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012,33 (2) :270-281.
[25]中共中央,國務(wù)院. 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綱要[Z].2016-03.
[26]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區(qū)域合作規(guī)劃[Z].2014-04.
[27]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洞庭湖生態(tài)經(jīng)濟區(qū)規(guī)劃[Z].2014-04.
[28]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大別山革命老區(qū)振興發(fā)展規(guī)劃[Z].2015-06.
[29]趙永亮,才國偉. 市場潛力的邊界效應(yīng)與內(nèi)外部市場一體化[J]. 經(jīng)濟研究,2009(7): 119-130.
[30]徐維祥,陳國亮,舒季君等. 基于空間連續(xù)性的“四化同步區(qū)”形成與演化機理研究[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15(5):18-31.
[31]郝景芳,馬 弘. 引力模型的新進展及對中國對外貿(mào)易的檢驗[J]. 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shù)經(jīng)濟研究, 2012(10):52-68.
[32]周念利.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國雙邊服務(wù)貿(mào)易流量與出口潛力研究[J]. 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shù)經(jīng)濟研究,2010(12):67-79.
[33]陳 昕. 大湄公河次區(qū)域東西經(jīng)濟走廊發(fā)展研究與借鑒[J]. 管理世界,2012(12):179-180.
[34]Nonthapot, Sakkari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panel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J].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2014,5(1):44-51.
[35]趙 勇,魏后凱.政府干預(yù)、城市群空間功能分工與地區(qū)差距——兼論中國區(qū)域政策的有效性[J]. 管理世界,2015(8):14-29.
[36]張玉新,李天籽.國際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背景下中國沿邊城市經(jīng)濟空間分布與影響因素[J].管理世界,2014(10):17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