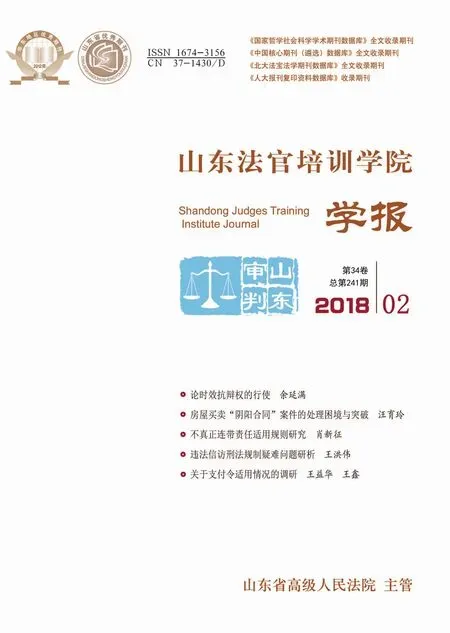房屋買賣“陰陽合同”案件的處理困境與突破
——以《民法總則》通謀虛偽表示的新規則為契機
汪育玲
近年來,房價不斷攀高,國家為了抑制房價,通過稅收、金融等政策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但實踐中出現房屋買賣當事人為了規避稅費或多獲取貸款而簽訂“陰陽合同”的不法現象,并逐漸演變成一種業內“潛規則”。當事人簽訂“陰陽合同”,不僅損害了國家的稅收利益,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也破壞了社會對合法交易、誠信履約的信心,給合同雙方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隱患。
一、現狀剖析:房屋買賣“陰陽合同”問題之重
所謂“陰陽合同”,又稱“黑白合同”,是指合同的當事人出于規避政府管理或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而對同一單交易所簽訂的兩份內容不一致的合同,其中一份提交給相關部門查驗和備案,但合同當事人并不實際履行,稱為“陽合同”;而另一份僅為合同當事人所掌握,但約定照此實際履行,稱為“陰合同”。a參見白彥鋒、張靜:《“陰陽合同”與我國二手房稅收收入流失的治理——以北京市為例》,載《創新》2012年第2期。“陰陽合同”最早出現在建設工程領域,后在房地產交易中大肆盛行。在房屋買賣中,“陰合同”顯示當事人的真實成交價格,“陽合同”則根據使用需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做低房價,以便在房地產交易中心過戶時少交稅款;另一類是做高房價,以便向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更多的貸款。實踐中第一類情形更為常見。
(一)房屋買賣“陰陽合同”現象頻發
為了對實踐中房屋買賣“陰陽合同”現象進行初步掌握,筆者以“房屋買賣”“陰陽合同”等為關鍵字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進行搜索,結果顯示自2009年至2017年上半年,全國共有289份相關裁判文書,詳見圖1。b此處數據僅供參考,鑒于搜索關鍵字的單一性、裁判文書公開的有限性以及訴訟手段的最終救濟性,實踐中“陰陽合同”簽訂量遠不止這個數據。

圖1 2009年—2017上半年全國房屋買賣“陰陽合同”案件數量統計
從圖1可見,近幾年我國房屋買賣領域“陰陽合同”案件數量迅猛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穩定房價,打擊“炒房”行為,國家通過稅收、限貸政策加強調控,當事人需要繳納更多的稅費,且購房現金壓力也增大,故通過“陰陽合同”以少納稅或多貸款的現象多發;二是當事人簽訂“陰陽合同”后,由于房價上漲或其他利益考慮而反悔,不愿意按照雙方先前約定履行合同,因此以“陰陽合同”為由提起訴訟意圖解除交易或者多得利益,導致了案件量急劇上升。

圖2 2009年—2017上半年房屋買賣“陰陽合同”案件多發省份統計
從圖2可見,我國房屋買賣“陰陽合同”案件數量與經濟發展程度緊密相關,經濟大省的房地產市場交易火爆,房屋買賣交易量大,隨之引發的糾紛案件也“水漲船高”,而其中“陰陽合同”案件量也就更多。
(二)原因分析:當事人只顧眼前之“利”
“陰陽合同”屢禁不止,與我國稅收制度不完善、執法手段不健全、當事人法律意識淡薄、社會誠信缺失等因素不無關系,但究其根源,還在于“利”字,在于當事人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
在房屋交易中,稅費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支出。根據現行稅法規定,無論是買方需繳納的契稅,還是賣方需繳納的增值稅、個人所得稅以及房改房的土地出讓金,計稅依據均為房屋的交易價格,即房屋價格越高,所納稅款越多。因此,部分當事人意圖通過簽訂“陰陽合同”,以減少稅費,降低交易成本。以廣州為例,如果一套房屋的實際成交價是300萬元(“陰合同”),當事人為避稅將網簽合同填低為200萬元(“陽合同”),即合同差價為100萬元。若該房屋不是買方的唯一住房,且賣方取得該房產權證書后未滿2年即出售,則當事人需要交納契稅3%、增值稅及附加5.6%、個人所得稅1%,若是房改房還需交納土地出讓金1%,共計稅率10.6%,則“陰陽合同”避稅達到了100萬元×10.6%=10.6萬元!
通過“陰陽合同”來避稅,對買賣當事人來說,似乎是個“共贏”的結果。就賣方而言,雖然實踐中一般要求實收款項,讓買方承擔所有稅費,但為了交易成功,也會同意另行簽訂價格較低的“陽合同”,而賣方并不因此實際受損。就買方而言,降低稅費是其重點考慮問題,低價的“陽合同”可以直接減少大筆稅費支出,因此買方會積極尋求簽訂“陰陽合同”。在通過“陰陽合同”多貸款的情形,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要根據備案合同價格來評定貸款發放數額,因此簽訂價格較高的“陽合同”也是當事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三)風險重重:當事人忽視潛藏之“害”
在利益的驅動下,買賣雙方不惜鋌而走險,抱著僥幸心理簽訂“陰陽合同”,并希望房屋交易得以順利完成。然而,無論當事人是填低房價以期規避稅費,還是抬高房價以超額貸款,實踐中常常“事與愿違”,“陰陽合同”的存在給雙方當事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隱患和法律風險。
1.賣方部分房款收不回或者增加額外支出的風險
在買賣雙方簽訂“陰陽合同”避稅的情況下,賣方面臨買方要求按照價格較低的“陽合同”履行的法律風險。實踐中,買方可能以存在“陰陽合同”為由,要求按照備案的價格較低的“陽合同”支付房款或者要求賣方退還“多收”的房款,甚至通過訴訟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主張。即使最后法院判決認定“陰合同”為真實交易價格,買方應當按照“陰合同”支付房款,賣方也面臨著合同難以實際履行以及利息損失風險。同時,賣方在訴訟中所花費的時間、精力、費用等成本支出,也是難以估量的。
2.買方多支付房款或者貸款被取消、減少的風險
如果買方為了獲取超額貸款而簽訂一份價格較高的“陽合同”,首先,便面臨賣方要求按照高價格的“陽合同”支付房款的法律風險。如果賣方因房價上漲或其他原因反悔,還可能以“陰陽合同”違法為由威脅要求加價或者解除合同。其次,買方還面臨銀行等取消或減少貸款的風險。銀行主要是根據房屋備案價格來確定貸款數額,一旦銀行發現備案的“陽合同”是虛高房價,可能解除貸款合同,即使同意按照實際成交價格的“陰合同”發放貸款,由于價格較低也無法貸到足夠款項來履行合同,存在交易失敗的風險。
3.買賣雙方被追繳稅款、高額罰款甚至刑事處罰的風險
買賣雙方為了少交稅款,以“陽合同”約定的較低價格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違背了如實向征稅機關申報與納稅的義務,屬于偷稅行為c《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一旦被稅務機關發現,將受到追繳稅款、滯納金以及少繳稅款50%以上5倍以下罰款的行政處罰。如果偷稅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符合逃稅罪d詳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五十七條規定。構成要件的,還將受到刑事處罰。
二、審判困境:同類案件裁判標準不同、結論各異
通過搜索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有關房屋買賣“陰陽合同”案例,從中挑選出典型案例進行歸類分析,筆者發現各地法院在審理房屋買賣“陰陽合同”案件中,大多認定“陰合同”符合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在認定“陽合同”效力時,各法院的裁判依據及結論則大相徑庭,主要有以下四種裁判類型:
(一)“陽合同”系惡意串通,合同無效
【案例一】e詳見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終6878號民事判決書。2015年4月27日,王某與龍某簽訂《房屋買賣協議》(“陰合同”),將其房屋以800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龍某。同日,王某的委托代理人陳某又和龍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陽合同”),將同一套房屋以500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龍某,并辦理了房屋產權過戶手續。后王某訴至法院,請求撤銷金額為500萬元的房屋買賣合同,并將房屋產權過戶到王某名下。
法院審理后認為,成交價為800萬元的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成交價為500萬元的合同并非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系雙方惡意串通為避稅而簽訂,應當認定為無效合同。故對王某主張撤銷該合同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二)“陽合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價格條款無效
【案例二】f詳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01民終1165號民事判決書。2016年2月3日,吳某與程某簽訂《購房合同》(“陰合同”),約定吳某購買程某的一套房屋,總價款91.5萬元。后雙方協商將總房價變更為93萬元。2016年5月25日,吳某、董某與程某簽訂《南京市存量房買賣合同》(“陽合同”),約定該房屋價款為123萬元,并辦理了房屋產權過戶手續。吳某、董某按房屋價款123萬元交納了契稅,并向銀行申請貸款80萬元。后銀行將80萬元貸款匯入程某的帳戶,程某未向吳某、董某返還30萬元。吳某、董某遂起訴要求程某返還購房款30萬元及利息。
法院經審理認為,91.5萬元的購房合同內容明確具體,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對雙方均有法律約束力。雙方就涉案房屋交易價格的真實意思表示僅為變更原交易價格91.5萬元為93萬元,后續合同中約定的價款123萬元僅是為了套取銀行貸款所作的約定,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該條款無效。吳某、董某基于房屋買賣合同中無效條款的約定,向程某支付30萬元購房款,程某應當予以返還。
(三)“陽合同”損害國家利益,價格條款無效
【案例三】g詳見河南省鄭州市管城回族區人民法院(2016)豫0104民初6715號民事判決書。2016年7月25日,湯某與董某簽訂鄭州市存量房買賣合同(“陽合同”),約定董某將其房產以48萬元價格賣給湯某,當天湯某以該價格交納了稅費。后查明,2016年6月22日,就涉案同一房產,湯某之妻肖某與董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陰合同”),約定房屋價格為53萬元。后湯某訴至法院,要求董某履行房屋買賣合同,并為湯某辦理過戶手續。
法院經審理認為,2016年7月25日備案合同系雙方為逃避稅收而簽的價格虛低的“陽合同”,以此辦理產權過戶,損害了國家利益,相應價格條款應認定無效。6月22日所簽“陰合同”應為各方真實意思表示,從維護交易安全的角度,該合同應當繼續履行。故判決湯某向董某支付剩余購房款,董某向湯某交付房屋并配合辦理過戶手續。
(四)“陽合同”非真實履行,效力不予評論
【案例四】h詳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1民終3882號民事判決書。2015年12月27日,薛某、甄某與黃某簽訂編號為424號的《存量房買賣合同》(“陰合同”),約定黃某向薛某、甄某購買涉案房屋,成交價款為93萬元。2015年12月30日,薛某、甄某的委托代理人譚某與黃某簽訂編號為127號的《廣州市存量房買賣合同》(“陽合同”),約定涉案房屋總金額為115萬元。后薛某、甄某以黃某未按127號《合同》支付全部購房款為由,起訴要求黃某支付購房余款。
法院經審理認為,424號合同應為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為合法有效,雙方均應切實履行。現黃某已實際按424號合同轉賬支付93萬元房款,涉案房屋亦實際過戶至黃某名下。127號合同并非薛某、甄某與黃某之間真實履行的合同,故對于合同效力不予置評。
三、立法檢討:現行法律缺漏造成審判實踐不一
(一)目前立法無直接依據可援引,不可類推適用
針對房屋買賣“陰陽合同”問題,目前我國立法并無作出系統性規定,缺乏直接處理依據。然而,在建設工程領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根據”,雖然最高院未對合同效力進行直接判斷,但實際上已明確了作為備案登記的“陽合同”有效,而體現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陰合同”無效。因此,有學者認為此種認定標準可類推適用到房屋買賣“陰陽合同”領域。這種觀點甚至得到了個別法院判例的支持,認為備案合同雖不一定是交易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但由于其與辦理過戶手續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的公示公信力,對房產交易當事人以外的其他人而言,足以相信備案合同載明交易價格即為交易雙方的真實價格。故對涉案房產轉讓價格的認定應以備案合同約定的為準。i詳見江蘇省丹陽市人民法院(2014)丹民初字第1569號民事判決書。
對于上述觀點和判例,筆者不敢認同。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簡單類推適用相關規定和案例,畢竟房屋買賣領域與建設工程領域是不同的兩個立法對象。無論是根據傳統的民法原理還是現行的法律制度,都無法嚴格推理出“陽合同”有效的觀點,更何況將法律針對某一類糾紛案件的處理規則擴展適用到其他領域。
(二)相關制度內涵外延不清,導致法律適用混亂
從上述案例的分析可見,在審理同一類案件時,法官們的裁判標準不一,主要選用以下三種依據來認定“陽合同”的效力:其一,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j《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下列民事行為無效:……(四)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七)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第(四)項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條k《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第(二)項有關“惡意串通”的規定,認為“陽合同”系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行為,合同或價格條款無效。其二,根據《民法通則》 五十八條第(七)項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有關“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規定,認為“陽合同”以合法形式掩蓋了避稅或騙貸的非法目的,合同或價格條款無效;其三,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l《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有關民事法律行為應具備要件的規定,認為“陽合同”不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同或價格條款無效或效力不予評論。
眾所周知,“惡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兩項制度,是我國特有的概念,最早規定在1986年《民法通則》中,至今尚無明確、統一的定性。從民法學理和立法看,惡意串通的概念表述得較為模糊,“在司法實踐中其適用范圍不斷擴張,邊界日趨模糊,以至于被任意運用,侵蝕了其他概念的效力范圍”。m楊代雄:《惡意串通行為的立法取舍——以惡意串、脫法行為與通謀虛偽表示的關系為視角》,載《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4期。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在傳統民法理論體系中也沒有一席之地,理論上因其與通謀虛偽表示等制度產生競合,不僅在立法體系中顯得重復與混亂,在司法實踐中也造成法律適用的矛盾。可見,正因為我國沒有對“陰陽合同”處理作出系統性規定,相關制度又存在內涵不清、外延不明的問題,導致法官們在審判中無法做到嚴格區分、準確定性,而是較為隨意地選擇適用法律依據,從而造成法律適用的混亂,影響了法律的穩定性和嚴肅性。
四、破解之路:《民法總則》通謀虛偽表示之新思路
2017年3月15日新出臺的《民法總則》,作為民法典的開篇之作,在我國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不僅進一步提升了我國民事立法的科學化和系統化,而且對諸多民事法律制度作出了新規定和新突破。其一大亮點是增設了第一百四十六條“通謀虛偽表示”規則:“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通謀虛偽表示的概念由德國民法所創制,雖然各國對其稱謂表達各異(虛偽行為、偽裝行為、虛假行為等),但內涵基本相同,如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認為,通謀虛偽表示,指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的意思表示。應具備的要件有三:①須有意思表示的存在;②須表示與真意不符;③須其非真意的表示與相對人通謀。n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
(一)通謀虛偽表示與類似制度之辨析
在《民法總則》頒布之前,我國立法沒有直接規定通謀虛偽表示制度,學界普遍將“惡意串通”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兩項制度認為是與之最為類似的制度,并對其內涵、外延、優劣進行了諸多分析和比較。
1.與惡意串通行為之區分。
傳統民法上的通謀虛偽表示與我國特有的惡意串通制度存在一定的交叉和相似之處,比如雙方當事人存在意思聯絡,即通謀,但二者的區別也是十分顯著的:第一,通謀虛偽表示須表示與真意不符,屬于雙方故意的意思與表示不一致;惡意串通行為有雙方串通即可,并不必須存在意思與表示不一致。第二,惡意串通行為須以加害第三人的故意為要件;而通謀虛偽表示不一定以加害他人為目的。第三,通謀虛偽表示的無效是基于意思主義的考慮,由于當事人缺乏真實的法效意思,故行為應屬無效;惡意串通行為的無效是因為該行為損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目的具有違法性,因此無效。o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第649—650頁。因此,二者包含的類型不同,如圖3所示:

圖3 通謀虛偽表示與惡意串通行為的關系
2.與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行為之區分。
通謀虛偽表示與我國獨創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行為關系密切,都存在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情形,形成了交叉關系,但二者也存在明顯區別:第一,通謀虛偽表示不一定含有隱藏行為;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行為一定包含有隱藏行為。第二,在都含有隱藏行為的情況下,通謀虛偽表示中的隱藏行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行為中的隱藏行為必然是非法的。第三,通謀虛偽表示行為無效的根源在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其法理基礎為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而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行為無效的根源在于其“目的非法”,因具有違法性而無效。二者的關系如圖4所示:

圖4 通謀虛偽表示與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行為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民法總則》刪除了《民法通則》《合同法》關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規定。可見,“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制度因其自身不足而被擯棄,通謀虛偽表示制度因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被寫入《民法總則》。
(二)“通謀虛偽表示”對“陰陽合同”的有效規制
根據通謀虛偽表示制度,我們可以順利地處理房屋買賣“陰陽合同”糾紛,其規制前提是:第一,賣方與買方通謀,雙方之間就簽訂“陰陽合同”存在意思聯絡;第二,雙方簽訂的“陽合同”為虛偽意思表示,目的是規避稅費或多獲取貸款;第三,雙方簽訂的“陰合同”為真實意思表示,是雙方實際履行的合同內容。可見,房屋買賣“陰陽合同”為含有隱藏行為的通謀虛偽表示,其中“陽合同”是雙方通謀所為的虛偽行為,“陰合同”是該通謀虛偽表示的隱藏行為。陰陽兩份合同相互獨立,其效力應當分別予以認定。
1.“陽合同”的效力認定:“部分無效說”
從上述案例可見,審判實踐中對房屋買賣“陽合同”的效力認定做法不一,主要分為合同無效、價格條款無效、不予認定三種。筆者認為,在分析“陽合同”的效力之前,首先要明確分析的邏輯起點。房屋買賣的備案合同之所以被稱為“陽合同”,是因為其價格條款不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交易價格,而是虛假價格。因此,所謂“陽合同”的效力,確切地說,是指“陽條款”(虛假價格條款)的效力。
關于“陽合同”價格條款的效力問題,我們可以直接適用“通謀虛偽表示”的效力分析。目前,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普遍將“通謀虛偽表示”認定為一種無效的法律行為p詳見:德國民法典第117條、日本民法典第94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87條規定。,其無效的理論根源來自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即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德國學者卡爾·拉倫茨非常精確地指出通謀虛偽表示行為是“表意人和表示的受領人一致同意表示事項不應該發生效力,亦即雙方當事人一致同意僅僅造成訂立某項法律行為的表面假象,而實際上并不想使有關的法律行為的法律效果產生”。q【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邵建東等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頁。因此,認定通謀虛偽表示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是出于對當事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是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使虛偽表示行為無效,體現了民法意思自治的理念。“陽合同”價格條款是買賣雙方為了規避稅費或多獲貸款而虛構的房屋價格,并不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該條款無效。
關于“陽合同”其他條款的效力問題,比如交房時間、違約責任、糾紛解決等條款,由于不是當事人的虛假意思表示,其效力不能依照“通謀虛偽表示”認定為無效。根據《民法通則》第六十條“民事行為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以及《合同法》第五十六條“合同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規定,其他條款不因價格條款無效而無效,其效力應單獨認定,在沒有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其他條款應為有效。綜上,房屋買賣“陽合同”的效力應采取“部分無效說”,即價格條款無效,其他條款有效。
2.“陰合同”的效力認定:“有效說”
房屋買賣的“陰合同”,是買賣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并實際履行,是“陽合同”所掩蓋的隱藏行為。對其效力,各國立法基本達成共識,認為應適用關于該隱藏行為的法律規定,并不因通謀虛偽表示行為無效而無效。德國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通謀虛偽行為隱藏另一法律行為的,認定其效力適用有關該隱藏行為的法律規定。r陳衛佐:《德國民法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頁。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款所設規定與德國民法的規定基本一致。可見,隱藏行為的效力是根據法律對此類行為所規定的生效要件來認定,如隱藏行為符合生效要件則有效,反之為無效。
因此,房屋買賣“陰合同”的效力不受“陽合同”的影響,不因“陽合同”價格條款無效而無效,應根據房屋買賣合同的生效要件進行認定。具體而言,“陰合同”約定的交易價格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有效。“將意思表示真實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乃是貫徹意思自治原則的當然要求。雙方當事人內心真實意思表示的一致(合意)是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的本源根據。”s高治:《通謀虛偽表示下合同的效力及第三人權益保護》,載《人民司法》2011年第3期。同時,承認“陰合同”對當事人的法律約束力,也是維護交易安全所需,避免一些不誠信的當事人以“陰陽合同”為由惡意違約,有利于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交易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綜上,房屋買賣“陰合同”的效力應采取“有效說”。
3.“陰陽合同”其他條款沖突時的效力認定
以上關于“陽合同”“陰合同”的效力認定是建立在除價格條款外,交房時間、違約責任、糾紛解決等其他條款不沖突的情況下。但進一步探討,如果“陽合同”其他條款與“陰合同”發生沖突,二者效力應如何認定?應按照哪份合同履行?筆者認為,還是應當以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為準,只有體現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的條款才是有效條款,才能對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在其他條款沖突的情況下,我們應當結合合同條款的具體內容、合同簽訂時間順序、合同實際履行情況等方面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進而認定其他條款的效力。
實踐中,買賣雙方在簽訂“陰陽合同”時,往往是“陰合同”簽訂在前,“陽合同”簽訂在后,當事人除了價格條款虛低或虛高外,其他條款均是真實意思表示,出現陰陽兩份合同約定不一致的情形,應認定為當事人經協商一致后對原先意思表示進行了更改,即合同變更問題。房屋買賣是一項重大交易,買賣雙方先簽訂“陰合同”約定實際成交價后,有時出于利益考慮會就履行時間、方式、違約責任等內容繼續談判,并協商一致后在“陽合同”中對先前簽訂的“陰合同”其他條款進行變更和修改。這種情況下,可考慮以最后簽署的“陽合同”中其他條款作為體現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內容,雙方按此約定履行權利義務。
綜上所述,房屋買賣“陰陽合同”作為一個整體,其效力應放在整個交易中進行判斷,只有符合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背法律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才能被認定為有效。具體而言,根據“通謀虛偽表示”制度,“陽合同”的價格條款不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為無效;“陰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并實際履行的合同,應為有效;若“陽合同”其他條款與“陰合同”不一致,在認定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基礎上,可考慮以“陽合同”其他條款為準。
結語
“趨利避害”或許是人類的天性,在房屋交易過程中當事人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充分保障自身權益本無可厚非。但追求利益一定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礎之上,切不可為了表面之利而冒險簽訂“陰陽合同”,否則因此引發糾紛或受到法律懲處,所付出的代價將遠大于所得到的利益,實為“得不償失”。每位當事人,在法律面前均應慎思之,慎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