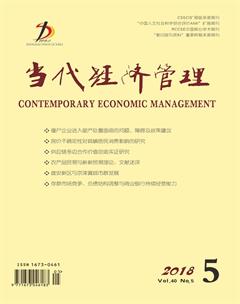雄安新區與京津冀城市群發展
李峰 趙怡虹
摘 要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國三大城市群之一,然而,城市群內部還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層級體系,城鎮體系結構失衡與城市間公共服務水平落差明顯,京津冀城市群的整體效應還未有效顯現。雄安新區的成立為破解京津冀都市圈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提供助力:在空間上,打造現代、智能、立體化的交通體系,降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阻隔與交易成本,化解大城市病及拓展城市群發展新空間;共建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促進京津冀創新擴散的區際過渡、銜接與吸收,推動創新優勢轉化為全球產業優勢與競爭優勢;構筑現代化的智慧、生態新城,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協調發展。建議秉持創新、綠色的理念,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雄安新區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發展,構建京津雄的三角城市群空間形態與布局,逐步轉變城市群“中心地”極化趨勢,突破“以鄰為壑”區域分割格局,打造區域聯動發展的新模式,形成開放性、互動性、共生性的網絡化城市群結構,最終實現以首都為核心的高品質的世界級城市群。
關鍵詞 雄安新區;創新驅動;網絡化空間結構;京津冀城市群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8)05-0045-06
一、引 言
當今全球經濟體系建立在“流”、網絡和節點的空間結構基礎上,城市群正是資金流、人才流、技術流的匯集地,是連接區域經濟和全球經濟網絡體系的節點,是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多層面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1]。國際上,美國紐約城市群、日本東京城市群、英國倫敦城市群、法國巴黎城市群等都已成為國家或大區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是配置全球資源要素和參與全球激烈競爭的核心區域。京津冀城市群作為我國三大城市群之一,科技人才匯集、創新資源豐富,具有雄厚的政治、文化、歷史底蘊,并且是我國自主創新、高端服務、現代制造的核心區域,已成為我國聯接全球經濟網絡的重要樞紐,將是我國參與全球競爭和國際分工中重要的世界級城市群[2]。
然而,當前京津冀城市群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城市與城市之間資源和要素爭奪激烈,功能交叉、同質化競爭比較嚴重。同時,京津雙核極化效應明顯,城市間不平衡與發展差距仍在加劇,還未形成合理城市分工和層級體系,造成京津冀資金、技術與人才資源浪費與低效配置。因此,如何破解京津冀都市圈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完善以首都為核心的城市群形態,解決“產業同構、項目建設重復”粗放城市發展模式,是當前京津冀城市群發展亟待解決的重大命題[3]。雄安這一國家級新區的成立,將在空間上與京津形成新三角空間聯系,疏解北京人口和非首都功能,釋放區域間“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活力,實現區域間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有利于突破“以鄰為壑”形成“共生互動”的城市群。同時,雄安新區的設立將加強基礎設施、人才、資金、服務等向整個京津冀空間拓展,實現技術、產業與人才等向城市群的外圍延伸,緩解中心城市與城市群之間矛盾,理順城市層級間資源配置關系,形成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賦予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4]。
二、雄安新區成立是京津冀城市群發展的歷史性選擇
(一)從國際經驗來看,設立雄安新區有利于形成分散型、網絡化的空間結構,發揮城市群的整體效應,進而化解京津冀大城市病與拓展城市群發展新空間
在全球經濟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化發展已進入到大都市引領的城市群發展階段,城市群已成為城市發展的特殊區域新空間單元。1950年全球人口超過500萬的特大城市僅有7個,2015年增加到73個[5]。美國紐約城市群人口已達6 50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超過90%,金融業及其衍生產業高度發達,已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英國倫敦城市群聚集了英國百強公司50%以上,擁有100多個歐洲500強企業的總部,成為歐洲及全球的金融、保險、證券交易和股票交易中心[6],城市群已成為國家和區域與全球經濟體系聯接的重要門戶,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
然而從世界城市群發展歷史看,這些大城市群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城市發展演進與城市群空間規劃的結果。無論是紐約城市群、巴黎城市群還是倫敦城市群,都經歷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市無序蔓延、區域發展不均衡的“惡性循環初級階段”,表現為住房條件惡化、環境質量下降、城市用地緊張等問題,集中反映了首位城市與其他城市發展之間矛盾以及城市群人口增長、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7]。因此,面向首位城市通過反磁力中心的建設,進行空間規劃與城市職能劃分,建立“分散型網絡結構”的區域空間模式,化解大城市病與拓展城市群發展新空間,在更大地域范圍內解決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非均衡發展,成為重要手段與解決途徑。
當前,京津冀城市群發展不協調、不平衡的矛盾比較突出。一方面,北京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科技、教育、文化等資源要素,城市規模不斷擴張,交通擁堵、人口膨脹、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凸顯,并且非首都功能的聚集超出北京的承載“負荷”,影響北京首都核心功能的發揮。而另一方面,河北省城市發展卻明顯存在不足,2015年河北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1.3%,低于全國城鎮化率4.8個百分點,而且京津兩個發達城市虹吸效應造成周邊地區的燈下黑效應嚴重,2016年河北地均經濟密度為4 010元/平方公里,僅為京津的1/9,與周邊環京津貧困帶形成巨大經濟發展落差和區域內部貧富不平等。
因此,雄安新區的設立將成為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空間支撐,疏解北京人口并集中承載非首都功能,與通州形成以首都為中心的相互支撐、錯位發展兩翼新格局,有效配置資源并實現內涵集約發展,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空間布局與發展形態。同時,借助現代化的交通和信息通達性,促進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向周邊輻射,推動河北省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步伐,提升河北省城市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治理水平,轉變城市群的“中心地”極化趨勢,推進開放性、網絡化城市發展,在分工合作、優勢互補基礎上,共同發揮京津冀城市群整體聚集優勢。
(二)從國內發展看,雄安新區有利于打造區域創新新引擎,推進京津冀城市群創新與協調發展,并為其他城市群發展提供樣本參考
目前,我國城市與區域發展逐步進入新階段,單體城市向城市共同體演變、核心城市向多個城市的集合體演進逐步成為我國區域發展的重要特征。2009~2014年,我國35個一、二線城市共增加3 778萬人口,其中前15大城市增加了3 010萬人,約占80%[5]。2015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GDP總額超過17萬億元,約占全國總量的36%。城市群正逐步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主體形態,也是我國城市化的重要戰略模式,為我國城市與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和活力。
當前,京津冀城市群已是我國北方區位最優、規模最大、創新能力最強的經濟中心區域,伴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深化,京津冀城市群進一步優化城市與區域分工與合作,集聚大量的產業和企業,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同時,由于京津冀集聚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配套體系,通過大城市帶動周邊的中心城市和衛星城鎮連片發展,形成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共享,產業經濟活動密切關聯,有利于京津冀城市群形成錯落有致、優勢互補的城市產業功能結構。
然而,從目前發展來看,京津冀城市群還處于城市群的初級發展階段,從城市人口規模來看,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 170.5萬人,2015年天津市常住人口1 546.95萬人,而河北省城區人口在300萬~500萬的城市只有石家莊與唐山市,河北省整體城市層級偏低,致使區域間深度梯度合作難以形成。另一方面,相比其他成熟的國際城市群,京津冀單體城市產業同質競爭嚴重,其本質遵循了大都市自我發展的發展理念和模式,對外輻射明顯強于對內擴散,京津冀都市圈的整體效應遠沒有發揮,城市群內區域協調和一體化水平明顯存在不足[3]。
雄安新區的設立通過經濟區劃與行政區劃聯動調整,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突破地域和區劃的壁壘,重塑京津冀城市群空間結構,分散北京資源、要素多度集中等問題,促進京津冀城市群更大范圍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梯度轉移。另一方面,雄安新區反磁力中心的建設,有利于化解城市群區域結構失衡、功能失調,改變過去重“外引”而輕“內聯”的問題,加強城市群產業分工耦合和空間一體化,構建都市復合中心和核心區的基礎上, 注重城市群周邊地區制造業、服務業等生產,將有利于形成功能層次完善、結構明晰的城市群空間均衡發展結構。
三、雄安新區推進京津冀城市群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空間上加密交通公共設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空間布局與發展形態,區域空間逐步向開放、流動、多中心的網絡化模式轉變
根據區域經濟理論,由于存在資源競爭、市場競爭與分工合作的區際聯系,多中心城市體系需要滿足六邊形空間結構的原則,次級中心往往位于3個高一層級中心的三角形中央,這將有利于與較高一級中心地錯位競爭、協調發展。雄安新區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距離天津110公里,距離北京120公里,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交匯點,將構成三角形的空間結構,不僅化解次級城市分布松散、關聯程度有限的問題,而且相比其他空間形態,三角形的城市群空間結構更具穩定性,平衡狀態不易被打破,有利于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空間形態,促進城市群空間優化與空間自組織演進。
雄安新區短期規劃面積100平方公里,中期規劃面積200平方公里,遠期規劃面積2 000平方公里,在這一空間尺度上,通過組團式格局對人口規劃、公共服務與公共設施規劃,成為科研轉化與產業合作的通道,成為北京城市功能的疏散區與拓展區,從空間釋放首都創新輻射作用。然而,2016年雄縣、容城與安新三縣的縣域GDP超過200億元,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發展潛力尚未發掘,因此,雄安新區需要加密臨近空間的軌道交通建設,建設高效的基礎設施網絡、發達的國際航運體系以及多層次的軌道交通網絡,保障雄安新區這一級次中心的公共服務質量,吸引全球人才、資金和信息,聚集高質量人口、產業、資本等經濟要素[8]。
而且,交通形式和交通成本不同的公共基礎設施,也會影響城市的空間發展模式。雄安新區不僅需要加快與其他地區高鐵的開通,加速城市的互動,大幅度壓縮與其他地區的時空距離。還需加強與周邊城市物流產業統一規劃,降低城市間阻隔與交易成本,提高城市的布局和交通效率,形成環京津區域環城交叉路網、軌道交通網等多層次立體交通網絡格局。例如,建成雄安至北京、天津、石家莊半小時通勤圈,雄安至京津冀三地機場的“無縫對接”,建設立體式交通樞紐,以先進、高度智能化交通系統,緩解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制約經濟增長潛力發揮的狀況,促進城市群內開展不同層次與不同領域的協作。
同時,需要注意居住與就業均衡、公共設施和生活設施配套需完善,推動人口密度與經濟密度提高,動態調控雄安新區資源、要素和功能,有序承接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科研資源、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以及企業總部資源等, 重構京津冀地區的產業格局。另一方面,作為反磁力中心,基于聯合與競爭的雙向效應,構建雄安新區和保定、石家莊等河北省周邊地區的高效基礎設施網絡,促進京津冀城市群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動和優化,空間利用集約高效,再構京津冀城市群職能分工、資源互補與產業鏈,重塑整個京津冀城市群空間格局。
(二)聚集創新資源要素,發展高端高新產業,共建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國際競爭力
城市群是城市發展的高級階段,為實現城市群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協同創新與區域一體化,是推動區域創新要素轉移、協調、獲取和外溢的主要途徑。美國提出“美國創新共同體”,界定這一具有空間屬性的創新體系概念,并提出系列相關重要舉措;歐盟先后出臺系列政策,從資源、人才和產學研用等推進協同創新。對于京津冀城市群而言,雄安新區將構成協同創新共同體的重要空間載體,促進空間單元之間生產要素的有效流動,減少京津冀區際交易成本,發揮京津冀1+1>2的協同創新效應,從建設中心創新城市向建設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創新城市群轉變,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的國際競爭力[9]。
雄安新區建設應面向全球引進人才、匯聚創新要素,探索新的區域創新發展模式,以重大工程與重大項目作為推進前沿技術研發與創新的重要載體,打造區域科技創新網絡公共服務平臺,發展創新型經濟。制定產業入駐負面清單,防止落后、污染、能耗巨大的企業進駐,發展高端高新產業,建設綠色智慧新城。不僅利用典型科技創新模式,而且利用互聯網、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服務業應用產生的創意為主的發展模式。通過“互聯網+創業”“互聯網+金融”“互聯網+制造”等創新模式,轉換發展方式集聚創新要素,促進資本、人才、科技共同體發展,引領和帶動雄安新區產業科技創新。
另一方面,北京集中了全國1/3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擁有超過2/3的兩院院士。雄安新區依托京津豐富的高校資源、人才資源、創新資源,集聚京津科研院所,建立創新產業園區、產學研聯盟及協同創新重點實驗室等,破除科技創新“孤島效應”,打造京津協同創新共同體,促進京津冀區域創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構建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開發的高效運行機制,建設集技術研發和轉移交易、成果孵化轉化的創新型城區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產業創新中心[10]。同時,承接首都研發轉化和產業研發功能,共建區域成果轉化中心、技術交易中心、知識產權中心,建立京津冀科技創新與轉化的通道和平臺,打造京津冀體制機制高地和協同創新重要平臺,加強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和服務鏈的深度融合,全球資源配置樞紐作用更加凸顯,培育京津冀城市群發展新動能[11]。
(三)以現代化國際化綠色新城,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創新擴散的區際過渡、銜接與吸收,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經濟梯度相連并具有差異化的發展格局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區際發展不僅考慮市場關聯效應,而且要重視知識和技術溢出引致周邊地區發展的外部性,知識溢出會導致邊緣區通過獲得核心區的技術與創新實現經濟增長,進而促進整個區域協調發展[12]。盡管京津冀三地空間上緊鄰,但科技資源和產業發展資源空間布局錯位,創新轉化平臺、利益共享欠缺,北京創新資源未有效輻射周邊,而異地轉化效應明顯。同時,缺乏先行先試政策與國家特殊體制支持,河北省經濟發展的“政策洼地”劣勢明顯。雄安新區定位為國家級新區,這將從高起點、高平臺展開創新改革試驗,通過體制創新和政策支持,促進三地科技與經濟對接、創新成果與產業對接,改造提升鋼鐵、石油化工等河北省傳統產業,延伸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行業產業鏈,通過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河北整個區域產業的升級和創新發展。
同時,雄安新區打造“現代化國際化綠色新城”,轉變傳統的依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的擴張模式,以先進適用技術、循環經濟技術、低碳技術等,綠色化與智慧化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特別針對河北省產業結構粗放,并面臨結構調整陣痛期和環境治理攻堅期,通過發揮生態創新示范功能,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轉型與升級[13]。并且,雄安新區可以探索利用非傳統水源、地熱、風光等可再生能源,推動生態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的建設,通過生態修復、新能源研發應用等示范工程,推進雄安新區海綿城市、城市大腦和智慧平臺的建造,建設京津共建國家綠色生態科技創新區,打造京津冀區域發展新引擎。
雄安新區作為京—保—石發展軸上重要的載體和支點,對接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合作共建跨區域布局協同發展產業帶,將冀中和冀東緊密連接,以點帶面,統籌、整合區域內資源,解決土地、勞動力、資本在區域上的錯配,以實現更大規模的人口承載力,促進人口、資源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同時,補強河北二線城市的缺失,通過知識創造、知識溢出和知識擴散,推進落后地區科技與經濟融合,有序承接首都創新擴散的區際過渡、銜接與吸收,放大河北與京津的協同效應,推進產業集聚、產業鏈重塑,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經濟梯度相連并具有差異化的發展格局[2]。
四、以新的發展理念推進雄安新區發展
國家級新區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戰略意圖的體現。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特區、浦東新區之后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國家新區。深圳特區的使命是讓世界進入中國、讓中國融入世界,是重要的窗口和橋梁,浦東新區最重要作用在于金融發展和國際化,而雄安新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業區和開發區,其定位不僅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決大城市病,而且是在經濟新常態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深化背景下,探索我國區域創新引領、內涵集聚發展路徑的嘗試[14]。尤其雄安新區是地處北方內陸地區,其發展背景正值經濟減速下降的經濟周期,雄安新區的發展必須擺脫我國經濟發展的傳統邏輯,其發展的根本不在于短期政府行為和刺激政策,而在于能夠直面深層次的體制改革與調整,以全新的發展理念主導建設進程,打造開放發展先行區與協同創新示范區,動態體現了國家戰略、創新驅動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良性互動,不僅成為區域經濟發展增長極,而且是制度創新的增長極,以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模式為其他地區發展提供借鑒與參考。
(一)以創新的理念引領雄安新區發展,打造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培育京津冀發展新動能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通過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培育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15]。雄安新區作為國家級新區,需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進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以創新驅動與產城融合推動雄安新區發展。具體舉措來看,一方面,需要密切跟蹤工業物聯網、智能制造、分布式制造等引領的新工業革命,聚集全球創新資源與要素,加強互聯網技術、數字化技術、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研究應用。同時,構建開放式的企業創新模式與區域創新體系,對高端產業鏈關鍵環節和重要結點實施公共研發,促進核心技術與產業共性技術的創新突破,在全球價值鏈與產業分工體系的位置大幅躍升。另一方面,打造具備完善的創新教育、技術研發、技術轉移、創業孵化、科技金融及居住配套等綜合服務功能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促進大量關聯企業及基礎支持機構集聚,培育形成技術領先、配套完備、鏈條完整的產業集群,釋放落地效應或放大輻射功能。同時,構建國家大學科技園、特色產業園區、眾創空間等多邊創新創業載體,打造特色化、差異化、專業化的創新平臺,以智慧、人性化城市功能支持產品分享、空間分享、知識技能分享等,改善新區營商環境、增加投資和人才吸引力,建設全國領先的創新型城區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創新中心。
(二)以智慧綠色的理念推動雄安新區發展,以綠色制造和高端高新產業的融合發展模式,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協調發展
伴隨我國環境污染、生態系統退化日趨嚴重,通過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模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成為當前的緊迫需求。雄安新區定位于創新型國家新區,將與以往新區不同,需要改變傳統城市化的規劃思路,著眼綠色發展和生態優先,改變“先建設、后生態”的發展模式,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另一方面,用改革創新引領產業結構調整,用環保倒逼產業轉型升級,針對制造業“低碳環保”和“智能化”現實需要,加強新一代信息技術、物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在工業制造廣泛應用,深度改變工業生產組織方式,促進制造業產業企業組織結構、管理模式與經濟業態創新,推進新區循環化改造和清潔生產,推廣應用節能環保新技術、新產品,打造京津冀的綠色制造和高端高新產業的融合發展模式,發揮京津冀綠色制造體系的引領作用。
(三)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探索城市間聯動發展新模式,打造開放發展先行區與協同創新示范區,促進京津冀創新擴散的區際過渡、銜接與吸收,推動創新優勢轉化為全球產業優勢與競爭優勢
目前京津冀三地不僅區域差距較大,城市群層級差異大、產業協同與創新擴散比較困難,而河北缺乏先行先試政策與國家特殊體制支持,經濟發展的“政策洼地”劣勢明顯,嚴重阻礙京津冀城市群的協和共生。雄安新區立足于綜合改革試驗區,建立精簡、高效、統一的新區管理機構,先行先試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人權、財權、土地管理以及公共住房的社會管理模式。同時,探索京津冀區域多方主體之間創新合作、互動互利的新機制。建立京津冀協同合作新平臺,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對接與技術轉移,合理重新分配產業轉移關聯區域間利益。并協調區域間企業轉移帶來的GDP、稅收和政績轉移,創新解決利益協調機制建立跨區域的利益共享機制、收入和財稅分成機制,破除城市群內多中心同質化、尺度差異大以及利益博弈嚴重等問題,推進城市群產業結構、空間結構的整合、優化,強化北京思想創新、科技創新、知識創新等策源地功能,打造雄安新區、石家莊、唐山應用研究[16],促進京津冀城市間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發揮城市群的“合作共贏”整體效應,實現城市群內部各城市共生共長、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 陸大道. 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協同發展[J]. 地理科學進展,2015,34(3):265-270.
[2] 周立群. 創新、整合與協調: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前沿報告[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3] 劉士林,劉新靜. 中國城市群發展報告(2016)[M].上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6.
[4] 張軍擴談雄安新區建設:增強京津冀發展協同性的重大部署[N/OL].(2017-04-06).中國證券網,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704-4059814.htm.
[5] 樊綱,郭萬達,中國城市化和特大城市問題再思考[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7.
[6] 文魁,祝爾娟. 首席專家論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重點[M]. 北京: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15.
[7] 賴迪輝. 京津冀都市圈城市蔓延演化模型及其治理路徑研究[J].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48-53.
[8] 王凱,周密. 日本首都圈協同發展及對京津冀都市圈發展的啟示[J]. 現代日本經濟,2015(1):65-74.
[9] 王書華. 京津冀城市群發展趨勢與協同創新格局[J]. 中國科技論壇,2015(11):78-81.
[10] 顏廷標. 努力把雄安新區建成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N]. 河北日報,2017-04-21(7).
[11] 張貴,石海洋,劉帥. 京津冀都市圈產業創新網絡再造與能力提升[J]. 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1):1-9.
[12] 殷廣衛,鄒璇.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對京津冀都市圈發展的幾點啟示[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32(4):124-128.
[13] 陳璐. 深刻認識規劃建設雄安新區重大意義[N]. 河北日報,2017-04-07(7).
[14] 馮奎. 推動雄安新區發展模式的重大創新[J]. 中國發展觀察,2017(8).
[15] 劉世錦. 如何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大邏輯[J]. 人民論壇,2015(9):22-24.
[16] 張莉,唐茂華. 京津冀都市圈發展新格局與合作機制創新研究[J]. 天津社會科學,2012(6):88-91.
Xiong'an New Are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Li Feng1,Zhao Yihong2
(1.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2.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China)
Abstract:Though one of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not formed a reasonable inner functional division and hierarchy system. The infrastructure between cities are not balanced and the differences of public service is obviou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setting up of Xiong'an New Area was for solving the long-term accumulated and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agglomeration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Xiong'an New Area is gonging to build a modern,intelligent,three-dimensional traffic system to reduce and extract the block and transaction cost of the non-capital function,dissolve the disease of big cities and expand new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space. The setting up of Xiong'an New Area is also a good chance to jointly buil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promote the interregional transition,cohesion and absorp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novation diffusion,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novation advantages to global industrial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Xiong'an New Area is gonging to build a modern intelligent and ecological new city. Innovation will be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inally,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innovative and green concept,deepen the reform and promote the high starting,high standard and high level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and build the spatial form and layout of the triangle city group of Beijing,Tianjin and Xiong'an. a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will come into being around our capital after an open,interactive,symbiotic and networked city agglomeration is constructed by designing the appropriate layout of the three areas and gradual depolarization of core cities.
Key words:Xiong'an New Area;innovation-driven;networked spatial structure;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責任編輯: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