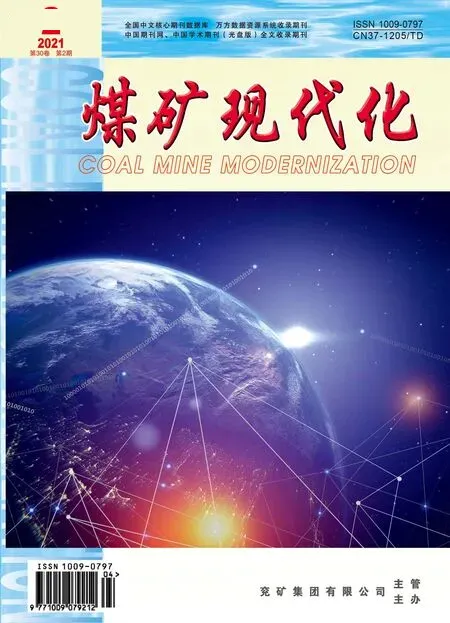復雜條件邊角煤開采沖擊地壓防治技術研究
路亞軍,閆憲磊,曹芳山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興隆莊煤礦,山東 兗州272102)
0 引 言
近年來,各地沖擊地壓事故頻發,造成了較大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也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沖擊地壓形式空前嚴峻。隨著礦井服務年限的延長,礦井采場開采條件條件愈加復雜,孤島、類孤島、不規則、邊角等復雜工作面不斷出現,工作面沖擊危險程度越來越高,沖擊地壓防治工作難度逐步增大。為了應對空前嚴峻的防沖形勢,針對B4328工作面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總結,為今后類似條件的開采提供依據。
1 工作面概況
1.1 工作面位置
B4328 綜放工作面位于四采區東部,北西部為切眼與4326 下順槽相鄰,南西部與4328 停采線相鄰,南東為設計停采線與B4328 運煤巷相鄰,北東側與八采二階軌道下山相鄰。面內有4328 撤除巷及四采下部運煤巷等老巷道。埋藏深度475.5~505.3m。由于采場條件限制,運順與4328 采空區留設25m 煤柱,造成應力集中程度較高,工作面沖擊危險程度較大。工作面位置如圖1。
1.2 煤層賦存特征及頂底板狀況
工作面煤層為下二疊系月門溝統山西組底部之3 煤,以亮煤為主,含鏡煤條帶,半亮型,煤層傾角1°~7°,平均3°。煤層結構復雜,在距頂板2.8~3.0m 發育一厚0.03m 左右之炭質粉砂巖夾矸。煤層厚度一般在7.8~9.95m,平均8.87m,普氏硬度f=2~3。

圖1 工作面位置及危險區域劃分圖
1.3 工作面支護情況
掘進時,B4328 工作面兩順槽采用錨網帶、錨索聯合支護,間排距為1000mm×1000mm,切眼內配合單體支柱聯合支護。
回采期間,軌順選用單元式支架支護,支護長度20m,單元式支架外部選用DW 型液壓單體支柱支護,支護長度不低于100m,合計超前支護長度為120m。運順選用ZT58500/24/45 型順槽支架支護,支護長度12m,順槽支架外部選用單元式支架支護,支護長度不低于108m,合計超前支護長度為120m。
2 工作面防沖評價情況
礦井委托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編制了《B4328 工作面沖擊危險性評價與防沖設計》。工作面沖擊危險性綜合指數為0.73,具有中等沖擊危險。危險區域劃分見表1、圖1。

表3 B4328 工作面回采期間沖擊危險區域劃分表
3 沖擊地壓監測方案
3.1 微震監測
為了確保有效監測,分別在十采四橫八采下山、8300 軌道底車場猴車繞道、B4328 皮聯巷門口、四采下部集軌巷設置一個拾震器,對工作面形成包圍,并對各拾震器位置(三違坐標)進行了校核。回采期間,各拾震器靈敏可靠、微震系統運行正常,監測數據真實、有效。
3.2 鉆屑法
工作面回采期間應采用鉆屑法對沖擊危險區域進行監測,檢測范圍要覆蓋工作面的超前支承壓力影響區,超前工作面煤壁100m 范圍內。鉆孔直徑42mm,孔深14m,孔口距底板1.2~1.5m,工作面煤壁前方第一個鉆孔距煤壁5~10m,幫部鉆孔間距15~20m。鉆孔方向平行于煤層,垂直巷幫,中等沖擊危險區域內每天檢測一次,弱沖擊危險區域每2天檢測一次。
3.3 應力在線
根據B4328 工作面的布置特點,在預測具有沖擊地壓危險區域巷道內安裝應力在線系統進行監測。運順應力傳感器安設范圍自切眼至運煤巷,安設在運順內幫和煤柱幫;軌順內段安設在巷道內幫,軌順外段安設在巷道外幫,始終保持工作面前方200m 左右處于監測范圍內。運煤巷自與運順交叉點向外120m 安設應力傳感器,軌順與運煤巷之間的聯絡巷也需要安設傳感器。
鉆孔應力計每25m 1 組,每組2 個,埋設深度分別為8、14m,每組2 個測點間距1~1.5m。
4 沖擊地壓防治方案
4.1 巷幫煤體預卸壓
在B4328 工作面回采前,在軌順和運順預測出具有沖擊地壓危險地段的巷幫,采用大直徑鉆孔卸壓措施(見圖2)。
工作面運順因為外幫側為煤柱,內幫受本工作面開采影響會產生應力集中,所以在兩幫都取大直徑鉆孔卸壓措施。根據工作面開采煤層厚度,煤柱寬度等因素,考慮運順開采時初次來壓及一次“見方”會提前出現,因此確定運順側初采100m 兩幫采取大直徑鉆孔加密措施,鉆孔間距為1m,鉆孔直徑為150mm,與巷幫垂直施工,鉆孔采用單排布置,距巷道底板距離1.2m 左右,鉆孔深度20m。運順其它地段兩幫施工大直徑卸壓鉆孔,鉆孔間距2m,其它參數同上,一直施工到運煤巷的位置。以上鉆孔在工作面回采前施工完畢。
工作面軌順內段在巷道內幫施工大直徑卸壓鉆孔,由于軌順內段為實體煤巷道,預測具有弱沖擊危險,所以卸壓鉆孔間距為3m。軌順外段預測具有中等沖擊危險,鉆孔間距2m。所有鉆孔在工作面回采前施工完畢。運煤巷在回采期間預測具有中等沖擊危險,鉆孔間距2m,其它參數同上。在工作面回采距運煤巷150m 以前施工完畢。
預卸壓措施施工完畢后,應進行效果檢驗無異常,方可繼續生產。

圖2 防沖措施落實圖
4.2 留底煤巷道預卸壓處理措施
工作面運煤巷、軌順與運煤巷間的聯絡巷、運順與運煤巷交叉處留有底煤,當底煤厚度超過1m時,在工作面回采前對底煤采取以下預卸壓措施。由于以上巷道受工作面采動影響不大,確定巷幫不采取預卸壓措施。
采取大直徑斷底孔配合爆破斷底處理措施處理巷道底煤。首先采取大直徑斷底孔處理措施,具體施工方案如下(見圖3、圖4):
1)在巷道兩底角向巷幫側外傾不大于30°各施工一排斷底鉆孔,斷底孔一般施工至煤層底板。
2)斷底鉆孔直徑不小于110mm,鉆孔間距不大于3m。

圖3 斷底鉆孔施工布置圖圖

4 爆破鉆孔施工斷面圖
爆破方案:
1)先施工大直徑斷底孔,確定底煤厚度以及需進行卸壓爆破區域。
2)對底煤卸壓爆破時,爆破孔位于巷道底板中線對應位置,每組布置一個爆破孔,爆破孔間距不大于6m。
3)采用手持式氣動鉆機施工爆破孔,采用插銷式聯接的麻花鉆桿,每節長1m,φ42mm 的鉆頭,爆破孔垂直底板施工至煤層底板。
4)采用煤礦許用水膠炸藥,炮眼封泥必須使用水炮泥,水炮泥外剩余的炮眼部分應當用黏土炮泥或者用不燃性、可塑性松散材料制成的炮泥封實,現場根據需要卸壓爆破范圍施工相應數量爆破孔。裝藥量根據具體底煤厚度進行選擇。
5 監測措施及數據分析
5.1 鉆屑法

圖5 鉆屑值變化趨勢圖
自2020 年1 月3 日生產至2020 年4 月25 回采結束,此間共施工鉆屑法檢測鉆孔1491 個,合計20 874m。所有檢測數據正常,煤粉量大部分在(2.4~3.6)kg/m 之間,最大煤粉量4.5kg/m。
從上圖可以看出,工作面初采期間,由于基本定未垮落,形成較大面積懸頂,造成工作面前方應力較為集中,鉆屑值較高。基本頂初次垮落之后,隨著工作面回采,頂板垮落比較及時,平均來壓步距僅有11.7m,超前支承應力釋放比較舒緩,鉆屑值逐漸降低。回采期間鉆屑值處于正常范圍內,無預警現象。
5.2 應力在線監測
回采前按設計要求沿線共安裝應力在線44組,監測范圍覆蓋了采動影響區域。回采期間,最大應力值為9.3MPa,出現在2020 年1 月13 日,距面口12m 附近。軌、運順各取一組監測點為例,整理、分析數據如圖6、圖7 所示:

圖6 應力在線變化趨勢圖

圖7 應力在線變化趨勢圖
從圖6、圖7 可以看出,距離工作面60m 處應力值開始有升高趨勢,距離工作面40m 處趨勢逐漸增大,但是均處于正常范圍,未出現預警現象。
5.3 微震監測系統
回采期間,對工作面微震監測數據統計如表2所示。
經對監測到的微震事件分析統計,工作面附近震動主要以小能量震動事件為主,大于104J 震動事件均發生在1 月13 日前,其中4 次發生在1 月7日(回采8.3m)。說明工作面回采初期,頂煤及直接頂未垮落,工作面前方受壓較大,尤其是在頂煤及直接頂垮落前,面前受壓達到最大,1 天內出現了4次大于104 的震動事件。

表2 B4328 工作面1 月3 日至4 月25 日微震事件能量比例統計
通過對各來壓周期微震事件的分布進行分析,微震事件隨著工作面推進逐步前移。軌順分布較多,說明運順側采空區頂板垮落比較充分。工作面前方微震事件主要分布在面前100m 范圍內,說明工作面超前壓力在100m 范圍內比較明顯。尤其是末采期間,由于工作面面長逐漸縮短,工作面承壓逐步增大,受老巷交叉影響,微震事件比較頻繁。
回采期間,微震監測處于正常范圍內,未出現預警現象。
5.4 周期來壓及頂板宏觀顯現分析

表3 B4328 工作面周期來壓統計
為準確分析工作面周期來壓情況,對工作面支架采用2 種方式進行循環末阻力進行實時監測。第1 種方式為依托電液控實時支架工作阻力在線監測,第2 種方式在工作面支架設7 組工作阻力記錄儀監測基點,分別設置在10、20、30、40、50、60、70#液壓支架,實時監測支架前柱及后柱循環工作阻力變化情況。工作面自1 月3 日初采至4 月25 日工作面周期來壓情況如表5 所示。
經統計分析工作面頂煤及直接頂垮落步距為8.64m,基本頂初次來壓步距39.03m,基本頂周期來壓平均步距為11.67m,周期來壓平均支架加權末阻力為7 414.08kN,屬來壓不明顯型。
5.5 上覆巖層破斷與礦壓顯現關系分析
前面分別對工作面回采期間微震、頂板來壓宏觀顯現、支架工作阻力進行了分析,可以得出由于工作面上覆巖層破斷活動造成工作面頂板宏觀,進一步造成支架工作阻力大幅增加,但三者是否存在一定關系及規律,三者與工作面開采強度是否存在一定關系。為此,將上述多源信息進行統計綜合分析,如圖8、圖9 所示。

圖8 工作面周期來壓微震事件、來壓步距、支架阻力變化曲線

圖9 B4328 工作面微震事件、日進尺、支架加權末阻力變化曲線
由圖8、圖9 得出下列結論:
1)工作面直接頂垮落、初次來壓、第1 次期間,微震事件總能量相對后期周期性來壓較高,分別為1.87×105J、3.01×105J、3.01×105J,其中工作面基本頂初次來壓期間微震事件總能量最高,來壓強度最大。
2)微震事件能量存在周期性變化,即低能量事件為高能量事件發生起到“蓄能”作用。
3)工作面微震事件總能量及工作面支架末阻力周期性變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其周期來壓布局基本一致。因此可以通過微震事件變化規律輔助預測預報工作面周期來壓。
4)由圖9 可以明顯看出,微震事件總能量較低時,工作面平均支架末阻力反而較高,即工作面支架阻力與微震事件總能量成負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驗證了上覆巖層運動與工作面來壓之間的關系:隨工作面的推進,上覆巖層開始出現裂隙(未破斷垮落),隨著工作面采空區后方懸頂面積的增加,采場支承應力開始增加,表現為支架工作阻力增加。當懸頂超過上覆巖層抗壓強度時,上覆巖層出現分區域進行斷裂,采場支承應力降低,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降低,如此周期性反復。
5)工作面自1 月3 日初采以來受多方因素影響,生產一直不穩定,開采速度跳躍性較大。由圖9可以看出,微震事件不論總能量還是頻次都與工作面推進速度成正相關,即勻速慢采有利于減少工作面高能量微震事件的發生。
5.6 微震事件演變過程分析
1)工作面頂煤及直接頂垮落期間,微震事件在平面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工作面前方,且超前工作面距離較遠,這是由于直接頂垮落后基本頂未出現破斷,仍處于懸臂狀態。
2)基本頂初次來壓期間,微震事件總能量達到最大。微震事件在平面分布上仍主要集中在工作面前方及軌順側巷道交叉區域,但超前工作面距離較直接頂垮落期間有所減小,且微震事件開始在工作面采空區后方出現。
3)自工作面第2 次周期來壓開始,工作面微震事件總能量開始降低,平均每次周期來壓期間累計微震事件總能量約為8.18×104J,平均工作面每推進1m 微震事件總能量約為7.47×103J,說明B4328工作面整體周期性來壓強度不高,工作面頂板垮落比較及時,不易形成大面積懸頂。
4)第7 次、第8 次周期來壓期間,受工作面見方影響,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顯著增大;在此期間,微震的頻度與總能量并無較大變化,說明工作面前期卸壓效果較為顯著,應力得到較大程度的釋放,有利于安全生產。
6 結 論
本工作面已于2020 年5 月30 日安全回采、撤除完畢。各項防沖監測、治理措施落實到位,生產期間各項監測數據傳輸、采集正常,各項指標無預警。說明本工作面的防沖設計可行、防治措施有效,此工作面沖擊地壓防治方案可作為類似工作面沖擊地壓防治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