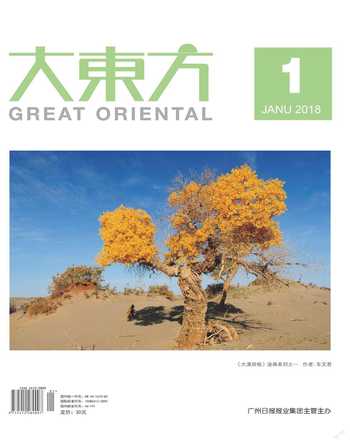非藝術何以成為藝術
摘要:1917年,在巴黎的獨立藝術家沙龍展上,馬賽爾.杜尚買到一件小便池,簽名后命名為《泉》,把它作為藝術品送去參展,被拒絕。到1960年,《泉》的重要價值開始被藝術界追認。以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泉》在藝術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關鍵詞:杜尚;《泉》;安格爾;達達主義
杜尚是在現代主義美術史上爭議較大的人。他早年醉心于純粹繪畫,但資質平庸終無所成。1912年杜尚開始放棄繪畫材料轉而使用拼貼和現成品。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泉》。在1917年那次展覽上,作為評委之一的杜尚化成“R.Mutt”,送去了一個在公共廁所中隨處可見的男用小便器,并在其上署名:“R.Mutt”,這就是《泉》。這件作品立刻遭到了獨立藝術家協會的拒絕,當然,他們不知道作者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杜尚。看到同行們的反應,杜尚終于驗證了自己的預測,他明白自己的藝術觀念太超前,時人無法接受,于是他立即退出了獨立藝術家協會。杜尚把小便器搬到博物館,用這個現成品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到底什么事藝術品,什么是藝術?藝術和生活的距離有多遠?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是什么?
對于審美文化和藝術史來說,杜尚的出現不啻是一場災難,從杜尚開始粗糙的現成品的組合也被納入了藝術語言的范疇,杜尚式的藝術排斥審美,傾向于智力游戲式的淺薄觀念。杜尚的行為本身并沒有多少意義,它似乎只是傳達杜尚的一種個人見解,作為自由社會來說,杜尚有其通過自己的手段傾訴觀念和藝術認識的自由權利,但杜尚的行為引起的震動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行為本身,使杜尚功成名就的不是杜尚的藝術而是對杜尚的爭論。從傳統觀念的角度,杜尚打破了藝術和非藝術、藝術家和普通人的界限,因而受到廣泛的譴責。傳統認識中的視覺藝術一般是約定俗成的藝術品,按照傳統大眾認識的慣例,特定的視覺藝術形式和特定材料樣式的藝術品是對立的,有獨特的可辨認的物理存在方式。傳統的大眾心理認識其實是對藝術的狹義見解,正是這種狹義見解給了杜尚可乘之機,尤其在20世紀,對藝術意義的認識有很大的分歧,這也成為杜尚依靠機巧而把握的間隙。杜尚巧妙地周旋在藝術本質論和非本質論之間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對于藝術這樣一個概念是無法精確定義的,古今哲學家對藝術的認識也是見仁見智。
杜尚的《泉》讓我想起了古典時期的一位大師安格爾,他的代表作《泉》堪稱新古典主義的巔峰之作。安格爾一生追求和表現理想美,十分迷戀于描繪女性人體,在他的筆下,每個人體都畫得圓潤細膩,健康柔美。少女的造型在整體上是遵循古希臘雕刻的原則,但更為細膩微妙。把古典美和女性人體的美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出色的表現了少女的天真的青春活力。安格爾把他心中長期積淀的古典美與寫實的現實美完美的結合了起來。這幅畫得奧秘在于畫家表現了人體姿態從不平衡到平衡的變化,抓住了人體內部力的微妙關系,即左傾斜的雙肩和向右傾斜的胯部,想上的用力和向下傾斜的水罐,前趨的右膝和后繃的左腿都體現了力而打破了平衡。這幅《泉》早在安格爾在佛羅倫薩期間就開始醞釀,事隔三十多年以后才最終完成。杜尚的《泉》意在質疑人們關于何為藝術品的觀念:很少會有什么東西去讓人們思考藝術實際上是什么,或它是如何被表達的問題;他們只是假定了藝術要么是繪畫,要么是雕塑。很以才會很少有人會將《泉》視為藝術品。杜尚認為,應該由藝術家來決定什么是藝術品,什么不是。這在傳統的觀念中是一次挑戰,一直以來藝術家都是被支配的地位,而杜尚認為:只要對其背景和含義加以改變,就可以成為藝術品。而且藝術家也可以不再被媒介所左右,油畫布、大理石、木頭為什么一直支配者藝術家?他要打破媒介第一位的傳統認識,“媒介永遠是第二位的,最首要也最重要的是理念。”本質上,藝術可以是任何東西,只要藝術家這么認為就可以。僅僅是跨越100多年的時間,藝術界竟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革,安格爾的少女純潔、美麗、傳統,他在秉承拉斐爾的古典道路精益求精,也固守陳規,他不會想到百年之后這個法國人用了最低賤、普通、丑陋的男性小便器也創作了一個叫《泉》的作品,并且在世界藝術史的影響力毫不遜色于他,甚至是開創性的先河。
杜尚的《泉》的特殊之處于杜尚根本沒有認為那座小便池具有“價值”,那種和經典藝術藏品比肩同列的所謂“價值”根本不是達達主義追求所在。達達主義者也根本沒打算獲得傳統的承認。“無論好的趣味還是壞的趣味都根本沒有意義”,在一份發表于1961年的訪談中,馬賽爾.杜尚這樣追述自己在二十世紀初所提交的那些“現成品”,“我只是偶然把標簽貼在那些現成物品之上”。這是一種最赤裸而鮮明的“反藝術”態度。它否定以往的一切藝術準則,要在自己的藝術行為和以往的藝術行為之間劃上一條決裂的邊界,達達主義否定一切傳統的藝術,甚至也否定它身邊的其它先鋒藝術取向。《泉》的出現,絕不僅僅是某種樣式或技法上的增減;而是想徹底推翻以往一切與藝術相關的概念,不論是“趣味”,“構思”,還是“技巧”,亦不論是藝術的創作方式,還是藝術的展示方式和藝術的認識方式,都在達達的徹底批判之列。
在現代藝術進程的一個世紀中,由于藝術進化論和觀念化、個人化的泛濫,使審美文化的價值觀承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傳統所積淀和傳承的藝術成就和經驗幾欲絕跡。很多歐美國家的藝術院校已經淪為空泛地討論觀念的場所,“審美”、“技術”和“傳統”成為人皆躲避的詞匯。原本應該通過視覺語言來傳遞的模糊情感,在很多現代主義者那里都變成了簡陋而又清晰的淺薄觀念。個性化一方面鼓勵了個人發展以及注重個人的地位和價值,因而有些某種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個人主義的發展則導致利已主義,使人易于滋生以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的惡劣品質,在藝術上則體現為牽強的偏激。本來藝術是可以按照自然升華的規律延展的,但現代社會的綜合機智扭曲了藝術升華的自然規律。尤其是現代形形色色的理論和觀念,對藝術實踐越位地進行假設、干預和荒唐的引領,大多數理論家和哲學家不是從具體的藝術經驗出發而是從純粹的思辨的角度來預測藝術的方向和未來,對藝術實踐起了很大的干擾和誤導運用,使審美的精神越來越空乏淪落,與審美無關的其他信息則日益以藝術的名義占據。
作者簡介
周亭(1995-),女,河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17級研究生,專業為美術,研究方向為中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