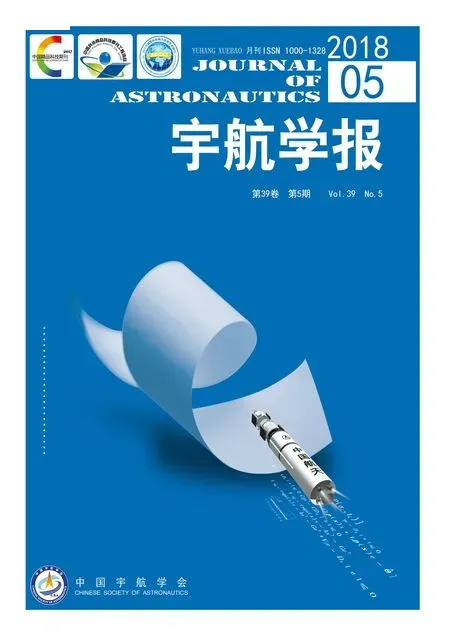固體火箭尾艙熱環境研究
楊學軍,沈 清,付繼偉,任一鵬,姚 瑤
(1.北京宇航系統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076; 2.中國航天空氣動力技術研究院 北京 100074)
0 引 言
固體運載火箭具有發射準備時間短,發射流程簡單的優點,近年來發展迅速,我國多型固體運載火箭已經成功發射。固體運載火箭的動力來源于大型固體火箭發動機,發動機噴流溫度高,是一個能量極大的熱源。固體火箭尾艙空間狹小,布局復雜,儀器電纜眾多,一般有伺服系統,控制系統,彈體結構,管路系統等,熱環境參數決定了防熱設計,關系到火箭飛行的成敗。對底部熱環境估計不足會嚴重威脅底部設備的安全性,但估計過度又會使防熱設計過于保守而增加結構消極質量,影響火箭的運載能力。
國外采用了多種方法研究飛行器噴流熱環境問題。早在1972年,針對火箭底部過熱的狀況,Kramer[1]對大力神III固體火箭底部噴流熱環境進行了研究,提出有效的解決措施;Bannink等[2]、Henckels等[3]開展了噴流試驗研究;Jin等[4]采用有限體積法求解RANS方程對Henckels的實驗算例進行了數值模擬,湍流模型采用大渦模擬,進一步驗證了高壓噴流的欠膨脹特性。
國內學者也開展了噴流方面試驗和仿真的研究,山其驤等[5]通過實驗測試了渦噴發動機的熱噴流的紅外輻射特性;胡海峰等[6]對大膨脹比噴管氣流分離狀態的流動、傳熱、結構耦合狀態進行數值分析與試驗,獲得了噴管的局部載荷;文獻[7-13]通過數值仿真,對發動機尾噴流的流場進行了模擬,獲得了尾噴流流場的影響范圍和壓力分布。
綜上,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發動機噴流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但鑒于火箭尾艙底部流動復雜特性及飛行試驗熱環境測量數據較少的現狀,對于固體火箭真實飛行過程中發動機噴流與外流相互作用下的尾艙底部熱環境,較少有相關研究。本文利用理論預測方法和數值計算方法,對固體火箭尾艙的熱環境進行了研究,給出了輻射熱流與對流熱流的預示結果,并與某型固體火箭的地面發動機試車試驗和真實飛行試驗熱環境測量數據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表明固體火箭尾艙熱環境存在天地差異,在固體火箭設計時需考慮真實飛行狀態下存在的量值更大的對流熱流。
1 固體火箭尾艙熱環境特點
與液體火箭相比,固體火箭尾艙的顯著特點是結構緊湊,固體發動機噴管深入尾艙內部,見圖1。固體火箭的結構形式使得火箭底部的熱環境具有以下典型特征:尾艙內的儀器設備與噴流的距離更近,受熱將更嚴重;固體火箭發動機工作時尾艙是一個受來流和噴流同時干擾的背風空腔,發動機噴流將與外流形成復雜干擾,形成極為惡劣的熱環境,對尾艙內各種儀器設備及電纜的熱防護是嚴峻的考驗。
固體火箭的噴流溫度極高,圖2給出了在發動機地面試車試驗狀態下的紅外溫度云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固體火箭發動機噴管出口溫度高于2000 ℃,是一個能量極大的熱源。
準確預測固體火箭尾艙的熱環境對于新型火箭尤為重要,雖然發動機連帶尾艙會進行地面試車,可以布置熱流與溫度測點進行熱環境測量。但火箭發射過程與地面試車情況截然不同,存在天地差異。從理論上分析,地面試車狀態由于試驗場大氣壓力較高,發動機噴流為不滿流狀態,且固定在發射臺上,發動機噴流對周圍空氣有抽吸作用,因此尾艙內僅存在輻射熱環境。而真實發射過程與地面試車試驗不同,火箭從地面到高空,周圍環境壓力不斷減小,噴流不斷膨脹;火箭從靜止加速到高超聲速,火箭周圍的高速空氣流動與發動機噴流相互作用,形成復雜的相互作用,除了輻射熱流,還存在對流熱環境。準確預示尾艙的熱環境對于固體火箭的總體設計尤為重要,僅依據地面發動機試車試驗的測量結果作為熱環境條件進行熱防護,會帶來風險。
2 固體火箭尾艙輻射熱環境研究
固體火箭尾艙的輻射熱環境可以通過理論計算與地面試驗相結合的方法獲得。
將噴流簡化成半無限長圓柱,并假設溫度和組成是均勻的,對尾段內的空間點的輻射角進行計算,通過積分獲取噴流對空間點的輻射熱。
計算公式如下:
Qf=εΨc0(T/100)4
(1)
從上式可以看出,輻射熱流條件主要受噴流燃氣的輻射系數與燃氣溫度影響,其中,燃氣溫度的影響較大,為4次方的關系。
在固體運載火箭研制過程中,會進行若干次發動機試車,測量發動機的性能,典型的試車狀態示意圖見圖3。在試驗中,搭載熱流與溫度傳感器,對火箭尾艙內的熱環境進行測量。
典型的地面試驗結果見圖4與圖5。圖4給出了尾艙內熱流測量結果與計算結果對比,可以看出,應用輻射熱流簡化計算公式得到的輻射熱流結果與地面試驗符合較好。圖5給出了尾艙內空氣溫度測量結果,可以看出地面試車溫度除了在點火時刻溫度短時間升高外,其余時刻溫度與環境溫度基本一致,空氣溫度沒有明顯升高,說明尾艙內基本不存在對流熱環境。
3 固體火箭尾艙對流熱環境研究
固體運載火箭尾艙的對流熱環境在首次發射前無法通過試驗獲得,準確預示尾艙熱環境極為復雜。固體火箭噴流的介質為高溫燃氣,并含有大量鋁粒子,數值模擬難度較大,同時,在發射過程中,火箭在大氣中高速飛行,來流為不同高度下的大氣,如采用多介質模擬,計算量極大且不成熟。本文探索了一種單介質簡化方法,通過非定常數值模擬,對整個發射過程固體火箭底部的對流熱環境進行了計算,計算結果與飛行試驗數據進行了對比,表明該方法可以有效預測固體火箭底部的對流熱環境,為固體火箭尾艙熱環境設計提供了重要參考。
3.1 流場控制方程
控制方程為柱坐標系下基于Favre質量加權平均的守恒型無量綱化軸對稱Navier-Stokes方程:
(2)
式中:
其中,ρ,u,v,P,e,h分別為流體的密度、速度笛卡兒坐標分量、壓力、單位質量總能和總焓。τxx,τrr,τxr,τθθ為應力張量的分量,qx,qr為熱流通量。
湍流模型采用三方程k-kl-ω模型,三方程的湍流模型對于模擬層流、湍流邊界層的混合問題精度更高。
(3)
(4)
(5)
3.2 線性化熱力學參數單介質簡化
數值模擬中采用可壓縮的理想氣體為介質,但由于固體火箭發動機燃氣參數與空氣熱力學參數差距極大,因此采用線性化方法對理想氣體的定壓比熱、導熱系數,黏性進行簡化處理,線性方法見式(6),在數值模擬中,只需給出兩點的熱力學參數,在本文的計算中,一點基于理想氣體,另一點基于固體火箭發動機燃燒室的燃氣。
(6)
3.3 網格
由于固體火箭發動機為圓柱體,在網格建模時簡化為軸對稱,劃分結構化網格,并設置監測點。主要包括以下邊界類型:箭體和發動機噴管為固壁邊界,箭軸為對稱軸,發動機燃燒室設置為壓力入口,來流設置為壓力遠場。計算域徑向取11米,火箭軸向37米。因為計算對流熱環境,與計算壓力分布相比,網格數要求更多,本文計算劃分48萬結構化網格,最小網格面積為1.37×10-4m2,圖6給出了局部網格,在尾艙附近進行了加密。
3.4 非定常計算
隨時間變化的邊界條件主要有發射軌道的環境壓力、環境溫度、Ma數,通過編寫函數賦值到邊界條件,一條真實發射軌道的主要邊界條件見圖7~圖9(Pref= 101 325 Pa,Tref=273 K)。首先對發射場點火后的流場進行穩態計算,得到初始流場,作為非定常計算的起始狀態。以0.01s為時間步長進行非定常數值模擬,記錄監測點的對流熱流與溫度。
3.5 仿真計算結果
3.5.1仿真校驗
固體火箭初始流場工況為火箭剛剛起飛,與發動機地面試車試驗物理邊界基本一致。初始流場的各物理參數見圖10~圖12,固體發動機喉道處、噴管出口的壓力、Ma數和溫度與發動機系統提供的預示參數一致。以發動機系統提供的喉道處壓力為截斷數值,給出模擬的發動機內部壓力分布見圖13,可以看出截斷數值在喉道處,說明模擬方法有效。
3.5.2模擬結果與飛行試驗結果對比
在火箭底部布置了熱流與溫度傳感器,獲取了真實發射工況下的熱環境參數。在數值仿真中,在傳感器相同位置處布置了監測點,通過非定常全發射過程的數值模擬,得到了監測點的對流熱流與空氣溫度,固體運載火箭的熱流傳感器測量的熱流包括輻射熱流與對流熱流,在對比分析時,扣除了輻射熱流。在火箭剛起飛時,由于火箭底部是低壓區,引射作用明顯,此時的熱流成分為輻射熱流,在文獻[1]中已有相同的研究結論。
以輻射熱流為參考熱流,對流熱流隨時間變化規律見圖14,可以看出數值仿真結果與飛行試驗數據整體符合較好,熱流量值與規律與真實飛行數據基本一致。固體火箭發射在t/tmax≈ 0.4進入超聲速,對流熱流明顯開始增加,在t/tmax≈ 0.75達到對流熱流的最大值,飛行試驗的Q/Qref峰值為3.78,計算的峰值為3.63,偏差小于5%。對流熱流整體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
底部空氣溫度與發射測量數據比較見圖15,數值仿真結果略小于實際飛行測量數據,在數值仿真中未計算輻射,造成仿真數據略小于實際飛行測量數據。在t/tmax= 0.8時,數值仿真的溫度下降幅度大于飛行試驗測量結果。整體仿真結果與實際飛行數據規律一致性較好,溫度整體為單調上升的趨勢。
3.5.3流場特征
選取三個典型時刻,分別是代表起飛段的t/tmax= 0.1,對流熱流最大時刻t/tmax= 0.75,飛行高度最高t/tmax= 1,流場的Ma數分布見圖16~圖18。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飛行高度的不斷增高,發動機噴流逐漸膨脹,膨脹的發動機噴流與來流相互作用,形成剪切層。剪切層與火箭尾艙相通,將噴流燃氣帶入尾艙,形成對流熱流。外場激波與尾噴流激波在發射后期逐漸接近,剪切層區域減小,與尾艙相通的區域在后期也逐漸減小,是火箭底部對流熱流密度在發射后期減小的原因。
4 結 論
本文對固體運載火箭尾艙的熱環境進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結論:
1)固體運載火箭尾艙內存在惡劣的熱環境,熱環境由輻射加熱與對流加熱組成。
2)固體運載火箭地面試車試驗可以獲得輻射熱流,并與輻射理論預示方法符合較好;但無法獲得對流加熱環境參數。
3)CFD數值模擬可以獲得發射工況下的對流熱環境,固體運載火箭尾艙內的對流熱環境量值可以達輻射熱流的幾倍。
4)在固體運載火箭熱環境設計時均需要考慮輻射與對流熱環境,尤其是在首次發射前需重點考慮對流熱流的預示。本文提出的一種線性化熱學參數的單介質模擬方法可用于預示固體火箭尾艙對流熱環境。
參 考 文 獻
[1] Kramer O G. Titan III convective base heating from solid rocket motor exhaust plumes [R]. 1972, AIAA Paper 72-1169.
[2] Bannink W J, Houtman E M, Bakkker P G. Base flow/ underexpanded exhaust plume interaction in a supersonic external flow [R]. 1998, AIAA paper 98-1598.
[3] Henckels A, Gulhan A.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base flow [J]. Notes on Numerical Fluid Mechanics and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2008, 98: 20-39.
[4] Jin Y, Friedrich R.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nozzle jet-external flow interaction [J]. Notes on Numerical Fluid Mechanics and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2008, 98: 57-81.
[5] 山其驤, 卜滿, 鄭禮寶.熱噴流紅外輻射特性的測試實驗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 1995, 27 (6): 791-796. [Shan Qi-xiang, Bu Man, Zheng Li-bao.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hot jet [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1995, 27(6):791-796.]
[6] 胡海峰, 鮑福廷, 王藝杰, 等.噴管分離流流動_熱_結構順序耦合數值模擬及試驗研究[J]. 宇航學報,2011,32(7): 1534-1541.[Hu Hai-feng, Bao Fu-ting, Wang Yi-jie, et al. Nozzle flow separation fluid-thermal-structure load transfer coupled analysis and test research[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 2011,32(7):1534-1541.]
[7] 鄭忠華, 陳偉芳, 吳其芬. 尾噴流底部流場與外流場干擾的拓撲結構數值模擬[J]. 國防科技大學學報, 1998, 20(3):18-22. [Zheng Zhong-hua, Chen Wei-fang, Wu Qi-fe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opological structure in the based flow of jet wake with disturbance of a main flow field [J]. Journa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1998, 20(3):18-22.]
[8] 徐春光, 劉君.某型導彈尾噴流形狀的數值模擬[J]. 推進技術, 2003,24(2):141-143. [Xu Chun-guang, Liu Jun.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plume flow structures for a missile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3, 24(2):141-143.]
[9] 林敬周, 李樺, 范曉檣, 等.超聲速底部噴流干擾流場數值模擬[J]. 空氣動力學學報, 2005, 23(4):516-520.[Lin Jing-zhou, Li Hua, Fan Xiao-qiang, et al.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base jet interaction in a supersonic external flow [J]. Acta Areodynamica Sinica, 2005, 23(4):516-520.]
[10] 田耀四, 蔡國飆, 朱定強, 等. 固體火箭發動機噴流流場數值仿真[J]. 宇航學報,2006,27(5):876-879.[Tian Yao-si, Cai Guo-biao, Zhu Ding-qiang, et al. Exhaust plume simulation of solid rocket [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 2006,27(5):876-879.]
[11] Tang Z G, Liu G, Mou B, et al. Effects of turbulence models 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nozzle jets [J]. Acta Areodynamica Sinica 2010 28(2):188-196.
[12] 蔡國飆, 王慧玉, 祖國君, 等.真空小噴管羽流場的Monte Carlo直接模擬[J]. 推進技術, 1997, 18(2): 44-49. [Cai Guo-biao, Wang Hui-yu, Zu Guo-jun, et al. Mont carlo direct simulation of small nozzle plume in vacuum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1997, 18(2): 44-49.]
[13] 姜毅,傅德彬.固體火箭發動機尾噴焰復燃流場計算[J]. 宇航學報,2008,29(2): 615-620. [Jiang Yi, Fu De-bin.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non equilibrium chemically reacting fluid field of the solid rocket motor exhaust plume [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 2008,29(2):876-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