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石(外一篇)
2018-06-04 16:43:38東君
野草
2018年3期
東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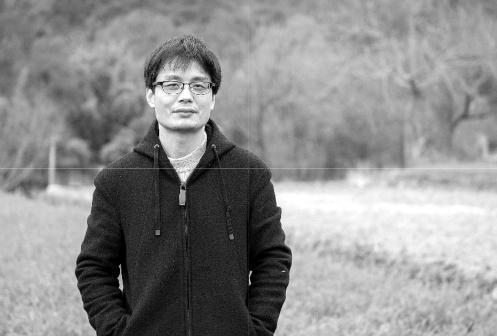
剛念初中時,父親有一回見我用毛筆在寫字本上涂抹,就問,這是什么?我說,是一塊石頭,兩棵樹。父親沉著臉說,你在寫字本上亂畫什么?!過了半晌,父親又問我,你想學畫?我點了點頭,父親說,明天我帶你去見一位畫畫的先生。父親習慣于把那些受人敬重的老師稱為“先生”。大一點的,稱先生伯;再大一點的,稱先生公。次日,父親帶我去拜訪那位“畫畫的先生”時,我才知道“先生”原來就是我的美術老師胡鐵錚。父親把我的涂鴉之作遞給胡老師,不知道說了幾句什么。胡老師瞥了一眼說,山水畫。然后就在構圖上指點二三。后來,我想,父親那天帶我去拜訪胡老師好歹也該帶點伴手禮的。父親舍不得花這個錢,我自然也不好意思登門學畫。學畫的念頭,就此擱下了。現在想來真是有些慚愧,當年有這么好的老師在眼前,居然沒有把握機會追隨他學畫。
胡老師有大雅的一面,也有大俗的一面。他的酒量是驚人的,好啖豬蹄也是出了名的。有一回,有位書法家朋友做東請客,其中一個盤子里滿當當盛著從樂清西門一家老字號店帶回的豬蹄。座中有人動箸,書法家突然伸手說,先別動這一盤。那人問,為什么?書法家說,這一盤豬蹄是特意為胡老師準備的。胡老師未動筷子之前,大家照例不動。胡老師來了,也不客氣,豪飲之間,把一盤豬蹄吃了個精光,連連稱善。
一個熱衷于喝酒吃肉的人應該是熱愛生活的。蘇東坡雖說不善飲酒,卻愛吃肉。他的《禪戲頌》有這樣一段話:“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