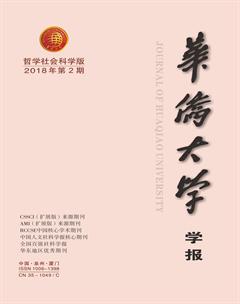圖像·音樂·儀式:意識形態具象化的三種典型
龍柏林 劉偉兵
摘 要:意識形態作為抽象的觀念集合,只有通過具象化的方式才容易被人們所把握。意識形態在敘事方式、感性認同和時空場域這三個環節中,實現了抽象性向現實性轉化的具象化。圖像形式,是對意識形態敘事方式具象化的典型,最終實現的是對歷史記憶的當代詢喚和對虛假意識形態的正名。音樂形式,則是意識形態感性認同環節具象化的典型,是對意識形態的感性化處理,最終實現的是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具象化契合。儀式形式這一典型,則是通過時空場域的建構和對他者在場的確立,最終生動地實現意識形態時空場域的具象化。
關鍵詞:意識形態;具象化;圖像;音樂;儀式
作者簡介:龍柏林,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意識形態與文化、社會理論與現代性。劉偉兵,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廣東 廣州 51027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當代中國社會分化的文化整合研究”(16BKS068)
中圖分類號:G02;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18)02-0012-09
意識形態作為觀念的集合,從特拉西提出開始,就一直作為一種抽象性的存在橫亙在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們面前。但是,作為一種觀念實在,意識形態早在這一概念提出之前就一直存在。正如馬克思所言,“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于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頁。隨著階級社會的發展,意識形態自身的階級性特征日益明朗起來。后來,不同學科話語和學術范式對意識形態進行了泛化解讀,以致于意識形態成為一種不可捉摸之物。在這里,我們采用的意識形態是指作為反映社會存在的抽象理論觀念的集合體系。由此值得追問的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何以能對抽象的意識形態予以感知?許多學者從不同學科對意識形態的具體形象化問題進行了探索,歸納起來就是意識形態的具象化理論。從馬克思對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批判到將意識形態看作是經濟基礎的派生物的分析,體現了馬克思對抽象意識形態的現實性的具象把握。之后,葛蘭西的社會水泥隱喻和阿爾都塞的國家機器理解,則深化了對抽象的意識形態進行具象化的把握。因此,正如杰姆遜所言,“不是到人們的觀點或謬誤、世界觀或者思想體系中去找出意識形態的東西,而在另一過程中去尋找。這一過程就是指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等完全是準規范性的程序所有層次上(人體和感官,精神狀態,時間,空間,工作過程和閑暇時間)對日常生活重新進行全面有系統的組織。”[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73頁。這里,我們可從敘事方式、感性認同和時空場域三個部分中,分別選擇圖像、音樂、儀式作為意識形態從抽象走向具象的富有典型性的形式進行聚焦尋找。必須說明的是,圖像、音樂、儀式并不是現代的產物,而是人類開始進行社會化活動之時就存在并延續發展至今的實踐活動。選擇這三種形式既能生動地反映意識形態具象化的機理,也能體現這一理論發展的歷史延續性。同時,圖像并不僅僅只是意識形態敘事方式的體現,也是意識形態在感性認同和時空場域的生動體現。同樣,音樂和儀式也并不是機械的單方面對應意識形態一部分內容的具象化。作為一個綜合載體,圖像既是意識形態的敘事方式,也發揮著意識形態感性認同和承載時空的功能。然而,為了更加直觀針對性地探討意識形態在敘事方式、感性認同和時空場域等三方面的具象化體現,則分別針對性的選取這三方面的代表形式,并將其置于意識形態整體性中進行探討。因此,梳理意識形態具象化的這三種典型,將有益于拓展意識形態研究深化的創新空間,同時更是把握意識形態落地生效的重要抓手。
一 圖像:意識形態敘事方式具象化的典型
意識形態從存在現象到理論自覺的過程,也是意識形態從抽象的觀念走向抽象的理論過程,并廣泛表現在道德、法律、文學、藝術、宗教等社會生活領域中。在此,人們通過具象化的抓手,實現意識形態的理論表達與傳播。這一方式就是意識形態的敘事方式。敘事方式最常見的就是話語和圖像。相比較于圖像,話語的敘事方式更加理性更加抽象,通過共同語境的思維共識來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抽象把握。圖像敘事方式則是意識形態感性化、具象化的敘事體現。通過圖片、表情、影視作品等生動形象的圖像實現視覺的感性沖擊,以一種視覺文化的方式構筑起意識形態的具象化。因此,在探究意識形態敘事方式具象化時,圖像成為了最典型的代表形式。
(一)歷史的敘事:歷史記憶的圖像詢喚
意識形態作為觀念的集合體,是通過歷史記憶的方式,實現意識形態的歷史傳承。通過歷史敘事的方式,實現對歷史記憶的當代詢喚(interpellation),從而實現意識形態在時間上的傳承。“歷史敘事是指敘事作為語言人工品,用來構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試驗和觀察所控制的結構模式和工序。”轉引自朱立元、包亞明《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四卷,后現代景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73頁。將存在過往時空的他者意識形態,以歷史記憶的方式傳承至今。“在一社會的‘集體記憶中,有一部分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形態呈現與流傳。人們藉此追溯社會群體的共同起源(起源記憶)及其歷史流變,以詮釋當前該社會人群各層次的認同與區分。”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8頁。但是,記憶依舊是一個抽象的范疇,是難以捕捉到的。因此,圖像的時空雙重內涵的特性,使其成為歷史敘事的優先載體。圖像對過往時空的他者復原,使得歷史記憶突破了時間的限制。感性直觀的圖像敘事,通過圖像對歷史記憶進行當代的詢喚,從而真正實現意識形態的具象化。將抽象的意識形態在敘事方式的環節中,通過圖像敘事的方式成為人們可以控制和接觸的具象化存在。正如海登·懷特所言:“必須把歷史看作是符號系統,歷史敘事同時指向兩個方向:敘事所形容的事件和歷史學家作為事件結構的圖標所選擇的故事類型或神話。敘事本身不是圖標;歷史敘事形容歷史紀錄中的事件,告訴讀者怎樣才能找到關于事件的圖標,使得事件變得‘熟悉起來。”轉引自朱立元、包亞明《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四卷,后現代景觀》,第580頁。歷史敘事的雙重向度,使得歷史記憶成為一個可操控的存在。歷史學家對歷史記憶的個體化解讀,使得歷史記憶被不斷地重構。作為集體記憶的歷史之維,歷史記憶發揮著集體認同的歷史在場。通過歷史的他者在場,為集體的意識形態賦予和集體的意識形態認同提供了合法性來源。意識形態作為抽象的觀念集合,通過記憶的范疇實現抽象的理論向現實觀念的轉化。通過歷史記憶的形式,實現意識形態歷史維度的自明。因此,意識形態在歷史層面體現為記憶的范疇。這種抽象的記憶一旦通過圖像這一歷史敘事的方式便能實現歷史記憶的傳承和感知。人們可以通過對歷史敘事的方式把握歷史記憶來把握意識形態的歷史之維。圖像的敘事方式,是對過往記憶的當代詢喚,也是對歷史記憶的當代重構,既是歷史記憶的時間延續,也是意識形態的現當代轉化。當然,歷史記憶并不完全等于歷史真實,意識形態也不完全等于現實。然而,通過圖像敘事將記憶從歷史中進行當代的詢喚,意識形態歷史敘事的抽象記憶便變成了人們直觀感知到的圖像。在這個意義上,圖像既是歷史記憶的延續,也是意識形態的具象化。
(二) 虛幻的正名:敘事方式的圖像具象
敘事方式是意識形態具象化的方式之一。作為敘事方式的一種,圖像成為意識形態具象化的一種形式。作為歷史記憶的載體,圖像通過自身的符號系統構筑起一個時空場域,通過象征的路徑實現對抽象的意識形態具象化。在這一時空場域中,能指與所指的統一實現了符號對真相的遮蔽,意識形態的虛幻性得到了正名。“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和本我、真實欲望相對立的,它作用在于通過提供意識形態幻象( 想象界) 來填補本我和自我的裂痕,表面看來它與本我精神契合,它反映了人們內心的欲望,但實質上,意識形態只是人們潛在需要的本我的替代物,它通過替代本我來消除了真正的本我,從而實現了對個人的全部控制。”陳文育:《關于圖像時代的意識形態問題》,《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69—70頁。因此,圖像對意識形態的具象只是使意識形態具有了外在的形式和現實的載體,并不是將抽象、虛幻的意識形態現實化。換句話說,圖像的具象恰好是對虛幻的意識形態的正名。在視覺文化支配的圖像時代下,圖像通過象征的方式實現了對真相的遮蔽和對抽象的具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類像代替了物像,虛幻代替了現實,仿真代替了真實。意識形態通過圖像這一話語結構和符號系統的象征作用重塑了其自身的虛幻性。“幻象不僅無法根除,而且還是自我的根基,與實在界漸行漸遠是人類在襁褓之中即已開始上演的認知悲劇。”王健:《意識形態的隱喻》《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年第3期,第52頁。在圖像的這一象征界中,符號系統的象征作用實現了能指與所指的統一,即自我、他者、對象三元的統一。意識形態的他者在圖像的時空場域中生產了“自我”的主體和可感知的對象。正如湯普森而言“象征形式是屬于一個主體和為了一個主體(或一些主體)的表述。”[英]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高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138頁。因此,一個可感知可觸摸的圖像,具體化了意識形態的抽象性,從而使得意識形態成為人們可接受可感知的存在。在這一過程中,人們觀看圖像觀看的并不是圖像的形象,而是感知到圖像所承載的抽象的意識形態。可以說,圖像既是作為當下空間的存在,同時也具有歷史記憶的時間維度。在雙重向度的話語結構中,對圖像的每一次空間上的直觀感知都是對時間上的意識形態他者的記憶傳承。虛幻的意識形態和抽象的歷史記憶在具體的物質載體圖像上,實現了意識形態的具象化也就是對意識形態虛幻的正名。
(三)歷史與現實:圖像意識形態的變革
圖像作為敘事方式的一種,是人們最初就擁有的話語方式。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就會在洞穴的石壁上進行繪畫,記錄當時的生產生活情景。在文字發明以前,圖像承擔著記錄歷史的功能。“即在我國語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們曾經有過一個以圖記事、以圖說事和以圖表情達意的漫長歷史時期,故圖像文化應是早于文字而獨立存在的中華早期文明之一。”李榮有:《圖像學的歷史傳統及其與現代的接軌》,《藝術百家》2012年第6期,第166頁。進入階級社會后,繪畫技術的發展和社會意識的不斷賦予,圖像作為文本話語的補充方式開始逐漸具有了意識形態承載的功能。但是在這一時期,圖像敘事方式依舊只是對文字、語言的話語補充,并沒有成為一個時代的交流主要方式。圖像更多的是能動地發揮了藝術的特征,作為藝術文化的一種被歷史不斷揚棄和發展。然而,用圖像交流的敘事方式依舊只是從屬于文字和語言的敘事方式。但是,資本主義的確立,帶來的生產力快速的發展,極大地解構了以往的社會傳統。“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403頁。在追求最大化和增值的資本邏輯推動下,視覺文化開始支配著這個時代。“但是需要說明的是,視覺文化的轉向并不意味著語言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消失了,而是說,較之于傳統的話語文化形態,視覺文化彰顯了圖像的生產、傳播和接受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使得視覺因素在文化中更具優勢地位。”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第4頁。視覺文化就是“以圖像為主因(dominant)的文化通過各種奇觀影像和宏大場面,主宰人們的休閑時間,塑造政治觀念和社會行為,不僅為創造認同性提供了種種的材料,促進一種新的日常生活結構的形成,而且也通過提供象征、神話和資源等,參與形成某種今天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多數人所共享的全球性文化。”肖勝偉:《視覺文化與圖像意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頁。這種圖像的轉向使得時代進入了圖像時代。“世界圖像并非意指一幅關于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德]馬丁·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86頁。人的表象活動把世界把握為圖像,意味著時代的發展中客體越是客觀而主體更顯主觀。在祛魅的理性時代,理性代表著正義和科學,象征著真相和正確。然而資本的高效率和快速增值的內在要求,使得直觀感性又成為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必然選擇。因此視覺作為理性與感性的合流,成為資本主義文化的直接選擇。“在超驗的層面上,與依附于感官體驗的視覺相區分,它指示一種理性和情感參與其中的判斷。”高燕:《視覺隱喻與空間轉向:思想史視野中的當代視覺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6頁。視覺因素在資本邏輯的裹挾中,成為了資本主義文化的重要因素,由此支配所產生的視覺文化轉向造成了如今的娛樂至死和景觀社會。圖像作為一種符號化的存在,從最初遮蔽真相體現意識形態的虛幻性,轉變為在消費社會和景觀社會中作為一種消費主義和物化了的意識形態存在。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就直接地揭露了這一現象,“它想方設法地讓人把那僅僅屬于魔術幻燈的東西當成幻象,它通過虛假的象征,使個體陷入到所謂個體無意識的神話中,以促使他們對其做出投資而完成消費功能。”[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2頁。德波則在《景觀社會》中將圖像意識形態的典型體現——景觀披露了出來。“景觀——由一種經濟生產的自動化體系的具體成功所導致的意識形態物質化——事實上,它將社會現實認同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鑄全部現實的意識形態。”[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9頁。總之,圖像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敘事方式的具象化,在資本邏輯的裹挾中實現著自我的變革與時代的宰制。
二 音樂:意識形態感性認同具象化的典型
抽象的意識形態是通過認同機制實現對人們的意識形態控制。無論是什么形式的意識形態最終都是通過同質化個體的思維來體現的。個體意識的異質性是個體自身特殊矛盾決定的。但是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的人們往往出現具有集體性的意識。這就是抽象的意識形態對個體的同質化作用。人們對意識形態的認同,是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機制,也是人們與意識形態產生聯系的機制。音樂作為人們表達情感的基本方式,是人們感性直觀的實踐方式。人們通過音樂抒發感情,也通過聽音樂來感受情感。這樣,音樂感性認同就成為意識形態在認同機制上的具象化形式的典型代表。
(一)音樂的認同:雙重世界的具象化象征
人們對意識形態的認同體現為意識形態的要求與日常生活實踐的契合。一方面是精神世界接受抽象的意識形態的要求和理論,另一方面在抽象的意識形態要求下實現對日常生活世界的實踐指導。通過這一認同機理,抽象的意識形態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具象化了。這一雙重世界的屬性與音樂自身的內在雙重向度構成了天然的吻合。音樂通過自己的樂器、節奏、聲音模仿構筑起一個現實的世界,但是音樂自身帶來的情感共鳴通過人們的想象構筑起一個精神世界。意識形態通過雙重世界的象征實現了在音樂形式中的具象化。在現實生活世界里,音樂通過音和律的形式模仿了現實世界。人們利用現實中可以發出聲音的材料制作成樂器,通過發出類似大自然鳥叫、馬鳴、流水等聲音來模仿現實世界。然而,單個樂符的象征并不能實現抽象意識形態的旨歸。因此,人們通過將不同聲音組合成不同的旋律和歌曲,將單個樂符的個體象征整合成一個系統的象征,實現音樂的現實世界建構。在音樂的現實世界向度中,人們感受到的是樂曲的變化,音調的時高時低,不同樂器的交叉使用,旋律的變化,等等。但是,音樂是人們內心情感的外在表達。附著在音樂形式上的是樂者自身的情感宣泄,也是聽者情感接受和精神世界構建的意識來源。古人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戴德、戴圣:《禮記》,楊靖、李昆侖編,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157頁。音樂在構筑起自身的現實世界向度的同時,樂者和聽者在現實世界的向度上構筑起自身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說,現實世界為精神世界的交流提供了物質載體。樂者在制樂、譜曲的過程中,通過不同的樂曲和音律表達出自己的不同情感。在音樂的實踐過程中,意識形態的賦予通過樂者的主觀性創造具象化了。例如,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救亡圖存的革命歌曲蘊含著當時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即抗日救亡。樂者們在接受這一主流意識形態后,通過情感賦予譜寫了一曲曲以情感為外衣的主流意識形態歌曲。當聽者在聽這一歌曲并接觸到音樂的現實世界向度時,聽者的精神世界也就與樂者在音樂中構筑起的精神世界產生情感的共鳴,也就是意識形態的認同。因此,“音樂作為人的一種存在和表達方式,從文化、宗教、藝術等精神創造性活動中,以紛繁復雜和系統體系化的符號形式,標志著人與動物的區別,昭示著人的存在。”黃靈智、周顯寶:《 “音樂認同”:一種哲學人類學解讀》,《學術界》2016年第4期,第190頁。在音樂認同的這一過程中,意識形態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具象化為音樂曲調、音律等,在精神世界中具象化為情感。音樂通過雙重世界的內在向度,實現了抽象意識形態在認同機制中的具象化,成為意識形態具象化的又一典型形式。
(二)情感的交流:意識形態的感性化處理
意識形態在認同環節的具象化表現為樂曲、曲調作為物質載體,情感共鳴則作為意識形態認同的路徑。抽象的意識形態認同就表現為音樂的欣賞和情感的交流。虛幻的、抽象的意識形態通過自身的感性化處理,具象化為人的情感,最終通過人們的感性接受的方式實現意識形態的認同。“人對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系,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頁。由此,意識形態通過在音樂雙重世界中的他者在場的方式,完成了聽者與樂者二人的意識形態詢喚。這種感性直觀的情感交流方式不僅適合于早期蒙昧時代的意識形態教育,也適合當代的情形。在早期,人們的思想并沒有祛魅,理性主義尚未宰制,統治階級通過直接的簡單的感性方式進行意識形態教育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于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1頁。但是,在現代信息時代,快速發展的社會造就人的專業化和信息的爆炸,使得人們在非專業領域中也熱衷于通過感性直觀的方式獲得信息,從而提高效率。“從生活實踐出發去觀察和理解意識形態現象,認真去認識意識形態豐富多樣的真實表現形式,就一定能發現,真實的意識形態形式雖然包含著理性思維,但主要以生動的感性形象表現出來的。并且支配廣大社會成員行為的主要意識形態也往往不是那些體系化、抽象化的價值或道德理論,而是通過文化傳承、心理積淀和風俗習慣的繼承等‘原生態的感性方式形成的生活信念和價值規范。”宋辰婷:《網絡時代的感性意識形態傳播和社會認同建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153頁。一首經典的歌曲,不僅承載著歷史記憶,更是人們共同情感的最大公約數。無論是中外哪個時期,不同年代的人們都有著自己最愛的歌手或者歌曲。這種音樂的審美是建立在集體記憶和共同情感之上的。因此,音樂審美其本身就是聽者與樂者的情感交流,本質是意識形態的感性交流。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感性化處理,使得抽象的意識形態理論變成了人們直接可以感知到的情感,再通過音樂的形式實現情感的共鳴達到意識形態的認同。這種以情感為外衣,內涵價值觀滲透的感性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音樂形式具象化的內在機理。
(三)歷史與現實:音樂意識形態的變革
音樂意識形態并不是現代的產物,也不是靜態不變的。在原始社會時期,音樂作為社會意識在認同環節的具象表征就存在了。“音樂教育意識的萌發,取決于人類對生活與美的追求及情感的發泄,其中包括:生產、生活、精神、情感、宗教及異性之間的關系與需求等。而這種需求正是音樂教育賴以發生、發展的美學、生理學和心理學基礎。”馬東風:《中國原始音樂教育的意識與形態》,《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第50頁。在人的情感的內在需求推動下,人們對美的追尋,使得音樂異化為意識形態對人的感性滲透,音樂不再是與語言并存的敘事方式,而是能動地發展為藝術形式。在早期中國,音樂的感性認同功能被統治階級關注并納入了早期的宣傳教育體系中。“原始儒家關注音樂的目的,意在發揮其道德教化的作用。”張節末、楊輝:《 “移風易俗”:中國古代的審美意識形態命題》2004年第5期,第36頁。禮樂文化的確立,使得樂成為了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環節。在這一時期,音樂的政治屬性被不斷突出。樂的意識形態功能被擺到了官方層面。“樂者,同倫理者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西漢]戴德、戴圣:《禮記》,楊靖、李昆侖編,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157頁。用音樂通達倫理與政治,是意識形態認同環節具象化的第一次明確。美的感性內涵、宗教的神性和統治的政治性共同構成了意識形態的他者在場。統治階級通過移風易俗和對意識形態音樂化的雙重實踐,實現了意識形態的具象化。一方面是強調音樂的審美意識形態作用,明確音樂意識形態的統治功能。“強調音樂具有移風易俗作用,認為音樂能以其和諧的情感深入人之身心,因而易于感化民風,有助于社會意識形態的長久統一與傳承。”楊輝:《審美意識形態視野下的漢代“移風易俗”音樂政策》,《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5期,第187頁。另一方面則是將意識形態以音樂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抽象的教化應隨著傳播形式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高建旺:《意識形態的戲化樂化——《伍倫全備記》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第156頁。意識形態不再是通過法律、道德、文本的形式赤裸裸地體現在人們的面前,而是通過編排成戲劇的形式或者是將民間戲劇音樂賦予政治意識形態的功能,從而形成意識形態音樂化的效果。譬如,“曹魏時,仍在民間繼續傳唱同時也作為宮廷饗宴音樂的二十二曲短簫鐃歌中的十二曲樂曲仍在行用,它們的歌詞內容則被改變為謳歌王朝的創立及其權力的正統性。”渡邊信一郎:《曹魏俗樂的政治意識形態化——從鼓吹樂所見》,牟發松譯,《襄樊學院學報》2010年第10期,第22頁。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音樂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認同的工具呈現出隱蔽性。資本邏輯下的大生產、同質化、多消費的現代性特點,使得音樂呈現為產業化的形式。如果說在古代社會音樂還能區分為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的等級差異,那么在現代社會中,錄音技術的發展和資本邏輯的大眾化滲透,使得音樂成為了商業產品,進入了批量生產模式。無論是什么著名的歌手、大型的演唱會都可以制作成音樂唱片或者是在網絡上進行付費下載,等等。這種大眾化的音樂表面上體現的是大眾的生活敘事,其實質是資本邏輯導致的意識形態隱蔽化滲透。作為交換商品的音樂,成為了一個用金錢量化的交換產品。人們通過對音樂的付費來感受音樂,其實質是對人的主體性的拒斥。因此,音樂意識形態的變革呈現為從自發的音樂教育向自覺的意識形態教育轉變,生活性向政治性的轉變以及資本邏輯宰制的邏輯進路。
三 儀式:意識形態時空場域具象化的典型
抽象意識形態在敘事方式上的典型具象化形式是圖像,在感性認同機制上的具象化代表是音樂。但是,意識形態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是要構筑起自身的現實時空場域,以便進行意識形態的敘事和認同。儀式自身固有的場域性質,使其成為了意識形態具象化的典型場域載體。
(一)他者在場:意識形態的他者確立
他者是相對自我而言的。意識形態的他者確立,即意識形態與自我的異質關系的確立。意識形態在具象化的儀式中表現出來的他者在場是通過信仰、記憶、情感三大范疇來體現的。第一,信仰的在場,意識形態在儀式中的確立。儀式從早期的宗教儀式開始,到現當代的政治儀式的確立,儀式的他者確立就是信仰意識形態。從最初對宗教的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是意識形態的神性和政治性的轉化。“信仰是人類特有的心理現象,是人們對一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的信奉和遵循,是統攝其他一切意識形態的最高意識形態。”李曉榮:《.略論意識形態與信仰的關系》,《理論導刊》2014年第5期,第47頁。人們在宗教儀式中實現了與他者的意識形態詢喚,在政治儀式中實現了對政治性意識形態的他者確立。第二,記憶的在場,意識形態在儀式中的確立。在宗教儀式和政治儀式的面前,信仰的確立是意識形態的他者在場。但是在社會層面、民族層面的儀式場域里,記憶成為了意識形態的他者在場。無論是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社會記憶都是集體記憶的不同向度。例如,汶川地震的周年祭是全國人民對2008年大地震的集體記憶。在所有的紀念儀式上,人們與儀式的記憶他者對話,回憶地震時期全國人民的抗震救災和自我扮演的角色。對記憶的詢喚其實質就是意識形態的他者在場。正是有著共同的抗震救災的集體記憶,人們才能在紀念儀式中接受和認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精神等主流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第三,情感的在場,意識形態在儀式中的確立。在日常生活層面,儀式的他者確立是情感。這種情感的感性化處理,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著儀式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自發的儀式。這些儀式并沒有固定的形式,也沒有固定的人群參與,甚至日常生活儀式也出現了個體化的現象。例如,舊城文物改造過程中,許多城市的原住居民出現了對城市歷史集體記憶的懷念。他們保持并重復著原有的生活習慣,既是對過往生活的懷念也是對過去文化的堅持。儀式感的他者確立,使得人們在儀式的場域中詢喚了這種儀式感,從而感知到圓滿、完整的節慶情感,也就是主體的自我確立,而這種儀式感就是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儀式中的他者在場。
(二)時空場域:意識形態的現實載體
意識形態在現實中的具象化,就是要構筑起自己的時空場域。正是因為時空場域的構建,才能區分他者與自我的異質時空。儀式的時空確立,是意識形態在現實世界的現實載體。第一,空間的確立。儀式通過對空間的選擇和改造從而為意識形態的具象化提供現實載體。一方面,通過對空間的選擇來體現意識形態。例如中國早期通過對禮廟的數量控制來體現政治上層人物的政治等級差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此以少為貴也。”[西漢]戴德、戴圣:《禮記》,楊靖、李昆侖編,第95—96頁。此外,通過空間的大小、高低、方向、顏色等的選擇都能體現意識形態。有的方位是高貴的人才能走才能坐,不同高低的座位象征著不同等級的人,不同大小的儀式器物也代表儀式中不同的權力資源分布,甚至通過顏色的差異體現儀式中人員的等級差異。這些都是意識形態通過空間選擇自覺建構起來的現實載體。另一方面,通過空間的限制進行意識形態的具象化。儀式中,對每一個儀式人員的站位、步數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不同的人處于不同的空間,這本身就是用空間限制的方式體現人們對意識形態的認同。例如,早期中國對為人子女孝敬父母都進行了空間上的限制規定。“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享不為概,祭祀不為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登高,不臨深……”[西漢]戴德、戴圣:《禮記》,楊靖、李昆侖編,第25頁。通過這種空間的選擇和限制為意識形態在空間上的具象化提供了現實載體。第二,時間的確立。相比較于空間的現實性,時間和意識形態一樣都以抽象的方式體現出來。但是,儀式自身的連接性,連接著過往、現在與未來的時間延續。通過儀式承接著過往的歷史記憶,實現對意識形態的他者詢喚。并且,儀式將記憶作為現實的記錄者,將當下的時間通過儀式進行具象化。例如事件周年和逢五逢十的紀念節日等,將抽象的時間具體化為特殊的時間節點,抽象的意識形態在抽象的時間維度中被具體化為特殊的節日和紀念日。儀式時空場域的確立,為抽象的意識形態在現實世界中確立了有形的載體。
(三)歷史與現實:儀式意識形態的變革
儀式作為意識形態的現實載體伴隨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變革。在不同時代,儀式意識形態體現為不同的特點。在早期,儀式作為重要的意識形態教育手段,成為統治階級統治的自覺選擇。中國早期對禮的重視和推廣就是儀式意識形態的重要體現。“廣義的禮是國家典章制度(官制、刑法、律歷等)、倫理規范(如三綱五常等)與行為儀式(朝聘燕享、婚喪嫁娶等)的總稱……狹義的禮則指人類日常生活中所奉行踐履的行為儀式與規范,是一個倫理學的概念。”謝謙:《中國古代宗教與禮樂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頁。通過儀式將抽象的意識形態(倫理道德規范)具體化為人們的日常行為規范。禮的確立包括了國家、社會、個人等多個層面,以一種明文確定的規范體現出來。人們通過學習禮的方式掌握了社會生存的規范。從這一角度看,早期的儀式意識形態體現為統治階級的自覺建構和對社會的強制性規范要求。儀式意識形態不僅在中國早期已有系統的使用,在西方社會里宗教儀式也從教堂走進整個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見,儀式意識形態在早期體現為強制性、全方位、自覺性的特點。在現代,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崛起,對宗教和封建迷信的祛魅,使得儀式被大量解構了。“迷信的衰落被置于多重語境之中:這是科學的天然對立物,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其自身合法性的場所,也是各式各樣的被論述對象周旋于改造者、群體利益以及各自生存境遇與內心體驗的社會空間。”沈潔:《儀式的凝聚力:現代城市中的行業神信仰》,《史林》2009年第2期,第35頁。中國早期的禮和西方的宗教儀式都被當做科學理性的對立物被剝奪了。這種對過往的消解,是在生活敘事對宏大敘事的解構語境中發生的。人們不再關注上帝,不再關注人類整體命運,不再關注國家與民族等宏大的命題。人們開始將視野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到個人生活世界本身。因此,儀式意識形態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出現了政治性向生活性的轉變,意識形態也由顯性傳導向隱性滲透轉化。日常生活的儀式不再是自覺建構的,也不再是外在強制性要求的。相反的是,儀式呈現為個體化現象。每個人追求的不再是固定的儀式和宏大的儀式解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對自我的確證需求下追尋著儀式感的他者在場,從而實現自我對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賦予。因此,每個人都具有著自我的儀式感追尋,這與多元化社會是吻合的。但是這種自覺走向自發,外在強制走向內在認同,形式優先走向儀式感追尋的當代儀式,依舊是意識形態在個人生活時空場域的具象化表征。
總之,作為一種觀念存在的意識形態,人們雖然能夠通過邏輯推演和學術論證實現對意識形態理論上的確證。但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意識形態仍然需要通過具象化的方式才能被人們所把握,從而實現意識形態的落地生根和廣泛認同。
Images,Music,Ceremony:Three Typical Examples
of Ideological Embodiment
LONG Bo-lin,LIU Wei-bing
Abstract:
As an abstract set of ideas,ideology can be easily grasped by people only through concrete methods and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bstraction to reality in the three stages of narrative style,perceptual identification and space-time field.The image form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way of ideological narration and ultimately realizes the contemporary call for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rectification of false ideology.The form of music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ideological perceptual identification,a sensible treatment of ideology,and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th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The ceremonial form realized the embodiment of ideology in space-time fiel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ace-time fiel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sence of the other.
Key words:ideology;embodiment;images;music;ceremony
【責任編輯 龔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