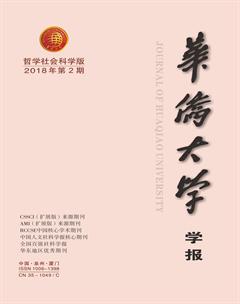明清小說敘事與江南園林空間經營互文性研究
張恒 李俐



摘 要:明清時期文人造園興盛,與此同時,文人章回小說創作與評點走向成熟。通過互文性理論視角,將江南園林與章回小說并置,共時性地考察明清小說的敘事結構、敘事轉換技巧與江南園林的空間結構、空間轉換方式,闡述兩者之間內在的互文關系,尋求在當代西方風景園林觀念盛行背景下,從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中挖掘中國本土造園觀念,為中國風景園林走出自己的道路提供一種可能。
關鍵詞:明清小說;江南園林;敘事;空間經營;互文性
作者簡介:張恒,華僑大學建筑學院講師,藝術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風景園林學;李俐,華僑大學建筑學院景觀設計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風景園林學(福建 廈門 361021)。
基金項目:華僑大學科研啟動經費項目(17bs20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51578251)
中圖分類號:I206.2;TU9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18)02-0143-08
現當代對于古典園林與文學的關系研究,多從園林意境、楹聯匾額、詩詞點景等語義的解釋層面進行討論,而互文性的思想理論,與中國文人“山水即文章”的觀念相契合,給出了從文本結構形式角度解讀園林與文學關聯性的途徑。通過對《紅樓夢》《金瓶梅》這兩個虛構的園林小說與同時期江南的文人園林之間的互文性解讀,可以理清明清章回小說敘事觀念與江南園林空間經營在結構形式上的異質同構特征,亦為文學與園林這兩種“文本”的互文性闡釋提供了理想范本。
一 中國傳統的“互文”特質
(一)何為“互文”
20世紀60年代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從巴赫金關于語言的“對話性”和“復聲部”理論中受到啟發,提出了“互文性”的重要文學理論。克里斯蒂娃認為文本空間的“語詞”是一個點而非一個面,其意義是由水平維度(作者——接受者)與垂直維度(文本與前后的社會文化關系總和)相互交錯的網絡系統所決定的。此概念成為后結構主義的批評術語:文本所包含的文字符號、知識話語、表意實踐等,與其他文本及廣泛的知識話語具有或顯性或隱性的聯系,即文本的“互涉”。羅蘭·巴特所述“文本即織物,一切文本都是過去引文的新織品”即是文本互涉性的另一種表述話語。“互文性”這一概念,對于中國人而言不難接受,古人對于“文”的觀念具有高度開放性與多元性,《易·系辭》曰:“物相雜故曰文”,先秦儒家認為任何事物相互交錯都可稱為“文”;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三十一情采》提出了“形文”“聲文”“情文”的概念,在劉勰看來色彩、聲音、情感的交錯都可成“文”。可見,中國古人早已擅長用廣義的“互文”性觀念看待異質文本的同構關聯性。
(二)明清文人的“互文”觀念
明清之際,商業經濟興起,而文人們面對政治的混濁,黨伐門爭,以及個人仕途的坎坷,經世治國的機會日漸渺茫,不甘心追求卓越之心被埋沒以及社會的動蕩將他們引入到其他文化領域,使得這一時期許多乖離正統的文人文化活動特別活躍:一方面,出現了具有濃厚文人色彩的章回小說,同時文人受到小說作品的感染,參與對小說的評點,如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金圣嘆評點《水滸傳》與《西廂記》、脂硯齋評點《紅樓夢》等;另一方面,文人造園興起,園林成為在現實社會狀態下理想與心靈的歸宿,隱含著明清時期文人的價值取向。“園林”文本與周圍的現實社會,與其誕生時代的文化氛圍,如繪畫、小說等“邊緣文本”,實際上共同構成當時明清社會的“大文本”。
文人造園立意構思多與詩文相通,清·張潮在《幽夢影》中有言:“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清)張潮撰,王峰評注:《幽夢影》,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53頁。,從“互文性”這個角度考量,明清小說與江南園林雖是不同的異質“文本”,但明清小說敘事結構、敘事轉換技法與江南園林空間結構、空間轉換機制之間復雜微妙的“異中之同”的結構關系,使得文人園林如同文學敘事的變體,兩者被文本的“互涉”牢牢吸附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正如陳從周先生在《中國詩文與中國園林藝術》一文中指出:“中國園林與中國文學,盤根錯節,難分難離,我認為研究中國園林,似應先從中國詩文入手,則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許多問題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園論園,則所解不深”陳從周:《中國詩文與中國園林藝術》,《揚州師院學報》1985年6期,第41—42頁。。
二 明清小說敘事與江南園林經營
(一)明清小說敘事結構與江南園林空間結構
“結構”本是建筑術語,晉·葛洪《抱樸子·勖學》講到:“文梓干云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明清文人常常將建屋造園與作詩文相類比,清·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論“結構第一”里說:“至于結構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清)李漁著,沈勇評注:《閑情偶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第234—235頁。。李漁將填曲詞比作建宅立架,他認為結構是掌控填詞全局的要點。而陳衍在《石遺室詩話·卷十七》也講到:“詩要處處有意,處處有結構,……譬如造一大園亭然”(清)陳衍:《石遺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264頁。。“結構”及其含義成為明清文人評議詩文與園林兩種異質文本時可互為解釋的常用術語。
1.明清章回小說“單元”敘事結構
明清時期的章回小說是將獨立的故事片段一回回的串聯成百回著作。美國漢學家浦安迪認為,從結構外形上來看,明清章回小說具有主、次雙層結構,且主次兩層結構關系相似:小說每五回或十回左右構成一個單元,每個單元內部講究語篇結構的起、承、轉、合,每“十回”次結構單元有相對獨立的人物與情節,內部亦有高潮起伏,構建出同型完整的敘事結構,統一性的結構布局將不同片段的敘事情節串聯經營在一起。而就全書而言,若干個敘事單元組構成更高層級的大敘事結構,全書的高潮處于大敘事結構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處,峰巒迭起,曲折連綿,全書大結構有著與敘事單元相同的起、承、轉、合的結構關系。浦安迪以《金瓶梅》為例,將其敘事結構劃分為10個“十回”次結構,全書以西門慶家的盛衰為主線,共有“百回”,而每“十回”敘述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縱觀《金瓶梅》全書,前二十回寫西門慶納妾可視為故事“起”,中間40回寫西門慶的通奸與買官賣官是故事的“承”,直到第七與第八個十回寫西門慶之子官哥之死到西門慶淫亂至死,成為全書的高潮與轉折。后20回成為故事的“合”,即以西門慶家族的家破人亡為結尾。(如圖1)這種大小回敘事方式“建構起了循環的、空間化的時間框架,表現出一層套一層的嵌套結構”陳展、趙炎秋:《中國古代小說的分形敘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51頁。。
圖1 《金瓶梅》敘事結構圖
2.江南園林“園中園”子空間結構
明清文人在園林的整體空間格局中,通過廊,墻、建筑將園林劃分為主次有別的園庭空間,每個園庭空間具備山石、植物、水池等景觀要素,并通過匾額楹聯的點景構成主題多變、自成一體的小庭院或小園林,形成子空間式的“園中園”結構。明·鐘伯敬在《梅花墅記》中談游園感受時,就點出了園林中“園中園”的空間結構特點:“身處園中,不知其為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后知其為園。此人情也。予游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趙厚均、楊鑒生編注,劉偉配圖:《中國歷代園林圖文精選·第三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2頁。童寯先生在《江南園林志》中提到:“園之布局,雖變幻無盡,而其最簡單需要,實全含于‘園字之內。今將‘園字圖解之:‘囗者圍墻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為池,‘衣在前似石似樹。……園之大者,積多數庭院而成,其一庭一園,又各為一園字也。”童寯:《江南園林志》,北京:中國建工出版社,1983年,第7頁。童寯先生以‘園的字形結構形象地道出了“園中園”的園林空間本質特點。如創建于明代的留園,歷經清代重修與擴建,分為西、北、東三區。西區以自然山景為主,中區以園林山水見長,東部則以庭院景觀為盛,留園整體的空間序列是從入口處時明時暗、時松時緊的三折曲廊小院引導至中部主景區,此處以水景為主,四周環以假山、亭臺、樓閣、廊道,形成游園的高潮,隨后穿行過五峰館院、石林小院、林泉耆碩等庭院景觀至冠云樓前,從山石之趣轉入曲院回廊之巧,再至孤峰之秀,形成游園的次高潮,最后經過留園北部盆景園的過渡,轉入山林野趣的西部園區,游園接近尾聲,呈現出開始段(起)——引導段(承)——高潮段(轉)——結尾段(合)的空間序列。而園中各個園區的“子序列”同樣呈現出起、承、轉、合的空間關系,園庭空間及其景觀要素在不同層級、尺度上派生,形成自相似性:中部園區隨曲廊行至濠濮亭等視線開敞的主景區而后進入空間相對閉合的西樓;西樓也可視為東部游園的開始,游園者隨五峰館院等庭院再進入冠云峰庭院,此處以冠云峰為主景,瑞云、岫云雙峰倚立兩側,庭院由亭臺廊館形成圍合,構成東部園區的高潮,隨后由北部園區穿行至西部的盆景園后,引入游園者視線的是一座土石假山,穿過土石山上的漫山楓林,到達位于山頂的至樂亭、舒嘯亭,此處視線開闊,可遠眺,亦是西部游園的高潮處,隨后下山,到達位于山腳的活潑潑地,游園結束。(如圖2,圖3,圖4)
圖2
圖3 留園空間結構圖
圖4 留園“子空間”敘事結構圖
3.園林空間結構與小說敘事結構的互文性
明清江南文人園林空間結構與同時期章回小說的敘事結構的相似性在于:明清章回小說以十回為“敘事單元”,類似于大園中的小園,看起來“方方勝景,區區殊致”。而小說主要人物事件的線索貫穿著整體的謀篇布局,形成小說整體情節的跌宕起伏,如同園林中的小園看似獨立,但各單元之間息息相關,曲折有致,一氣貫通,組成園林整體的空間序列關系。如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所述:“拆開則逐物有致,合攏則通體聯絡。”(清)沈宗騫著,李安源、劉秋蘭注:《芥舟學畫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年,第13頁。江南文人園林的空間結構與明清章回小說的敘事結構存在雙向的互文關系:明清文人參照與引用傳統建筑結構邏輯的關系來構建文本的空間結構,對建筑建構形式進行借用與擬仿,是一種顯性互文關系;而文人在構建園林時,將文本敘事空間的組織邏輯隱含在實體園林空間中,則形成一種隱性的互文關系:江南園林“園中園”的空間形式與章回小說的“百回”文本結構形式類似,這種互文關系需要游園者細心的參與解讀,即依賴于游園者的互文能力。
(二)明清小說敘事聯結策略與江南園林空間轉換機制
敘事聯結作用是將文本的次結構單元聯結為一個整體,明清小說評點中稱之為 “過文”“過脈”“前后伏應”等。對明清小說評點中所論述的敘事轉換技巧與園林空間轉換機制進行雙向性的認知與考察發現,兩者內在的“互文性”不僅在于前述的敘事結構層面,還存在于敘事聯結轉換層面的關聯性。
1.明清小說敘事評點的“間三帶四”與江南園林營造的“步移景異”
(1)“間三帶四”法
“間三帶四”指情節的轉換技巧,是通過小說人物在不同文本空間中的游走,表現出不同場景的人與事,使敘事情節自然轉換,不漏痕跡。《胭脂齋評點紅樓夢》第七回回前評:“到他(曹雪芹)小說中一筆作兩三筆者,一事啟兩事者均曾見之。豈有似‘送花一回間三帶四贊花簇錦之文哉?”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9頁。第七回描寫周瑞家領得送宮花的差事,通過周瑞送花的行走路線展示了榮國府里各個人物的生活狀態,暗示小說中的人物線索:周婦嘆香菱(王夫人家門前)——迎春、探春下棋(王夫人正房三間抱廈);惜春與小尼姑智能兒聊天——李紈歪在炕上睡覺(穿過夾道子,從李紈后窗下越過西花墻)——賈璉和熙鳳風月嬉戲(到鳳姐處)——周女求母(去賈母家的路上)——寶玉與黛玉游戲(到賈母家),遣茜雪探寶釵。作者是借周瑞的視角游走于各個單元空間之間,使觀眾的視線亦隨著周瑞的游走路徑對各個場景進行觀照。從敘事層面講,“間三帶四”法是將不同空間串聯,起到了彌合不同場景之間界線的作用。
圖5 網師園主景區游線圖
(2)江南園林的“步移景異”
“步移景異”是游園者隨著“步移”——視點的變化,在動態地步行中觀賞空間各異的景致,在不經意的游走間來感受空間的變化。以網師園的主景區為例:其空間布局是將入口設置在東南角,以較為封閉的門廳、轎廳等室內空間壓縮視野,隨后經由曲廊引導入“小山叢桂軒”,“小山叢桂軒”深藏于黃石堆山中,視野較為封閉,但透過疊石隱約可見園中水景;沿著長廊再前往“濯纓水閣”,此處視野開闊;隨后再經沿水曲廊,到“月到風來亭”,這兩處亭、榭空間開闊且軒楹高爽,可一覽水景全貌,游園達到高潮;而后游園者隨曲橋進入看松讀畫軒前的庭院,庭院堆有黃石并種植白皮松、柏、羅漢松、牡丹等植物,略成疏朗山林畫面。最后游園者行至竹外一枝軒與射鴨榭這兩處臨水廊亭,這種灰空間的景觀建筑形式大大消弱了大建筑體量對水面的影響,而與對面的月到風來亭形成對景。在主園區的游線中建筑灰空間與外部空間交替,游園者視線亦隨著黃石假山的高低起伏而變化。(如圖5、圖6)
圖6 網師園步移景異示意圖
(3)江南園林“步移景異”與明清小說“間三帶四”的互文性
江南園林“步移景異”的空間鏈接方式與“間三帶四”的敘事方式相似:文人園林的“步移景異”是以游園者的行進為線索,將空間的起承轉合、抑揚頓挫按照一定序列編排,隨著時間的流變逐步展現多變的空間形態,園林意境在忽明忽暗的曲折空間轉換中得到拓展與延伸,是基于時間維度的園林空間經營方式,文人們將園林空間體驗狀態時態化,實現了賞園的變換、連接與意境的生成發展;明清小說“間三帶四”的敘事方式則具有基于空間維度的敘事空間建構形式,是將小說歷時性的時間敘事形態空間化,實現了敘事的轉換、延續與情節的跌宕發展,前者將空間時間化,后者將時間空間化,構成了互補性的互文關系,隱含了文人對兩種文本審美向度充分的比較與把握。
2.明清小說敘事評點的“橫云斷嶺”法與江南園林營造的“障景”法
(1)明清小說敘事評點的“橫云斷嶺”法
“橫云斷嶺”是明清小說評點敘事的術語之一。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提出:“宜連則連、宜斷則斷”,并認為“《三國》一書,有橫云斷嶺,橫橋鎖溪之妙。”周汝昌在評《紅樓夢》寫到:“‘橫云斷嶺,則又是正說到‘熱鬧中間,讀者急待下文時,卻橫空‘插入(也是插入)一個人、一句話、一聲響……突然將上文截住了,——然而又不同于‘異峰突起,人來了不一定壓眾,話來的不一定驚人,它起過‘斷嶺作用后,‘收拾過去,大有‘重作輕抹的意味。”周汝昌:《紅樓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第77頁。“橫云斷嶺法”一方面使小說情節不累贅,還是后文生發它事之伏筆。如《紅樓夢》第十七回寫賈政與眾人游大觀園“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來回話。”庚辰雙行夾批: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漸寫雨村親切,正為后文地步。伏脈千里,橫云斷嶺法。這里作者并沒有因為賈雨村給賈政回話而打斷游園,而是到第三十二回再繼敘賈雨村造訪賈政一事。此處“橫云斷嶺”貌似以賈雨村給賈政回話為“斷”,實則以賈雨村與賈政之“親切”為“伏”,使得小說“留下有馀不盡之音韻,也更為后來的文章設下千里的伏脈”,“橫云斷嶺”是讓小說“敘而有斷、斷而須續”,在文本空間引導敘事視角的轉換。
(2)江南園林營造的“障景”
“障景”是文人造園常用的藏露有趣的園林意境生成手法,先用假山、植物等“阻斷”游人視線,而游人透過假山洞口、婆娑樹影隱約可見里面的庭院深深,為園內景觀起到鋪墊的“伏筆”作用,而后又“接續”引導空間,營造曲折含蓄、小中見大的園林意境。明·唐志契在《繪事微言》論述了“藏”與“露”的關系:“丘壑藏露:更能藏處多于露處,而趣味無盡;蓋一層之上,更有一層,層層之中,復藏一層。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若主露而不藏,便淺而薄。……景愈藏,景界愈大,景愈露,景界愈小。”(明)唐志契著,張曼華校注:《繪事微言》,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年。《紅樓夢》中對大觀園的描寫:“開門進去,只見一道翠嶂擋在面前,眾清客都道:好山,好山……”這種開門見山的障景方式常見江南園林中,如拙政園原入口處的黃石堆山“阻斷”空間視線,避免園內之景一覽無余,而不遠處的遠香堂在山后露一角,使得園內景觀欲露先藏,欲顯先隱,以達山重水復, 曲徑通幽的意境。(如圖7)
圖7 拙政園原入口腰門處
(3)“障景”法與“橫云斷嶺”法的互文性
“橫云斷山”法是通過顯隱得當的敘事方式,讓讀者產生山窮水復、柳暗花明的審美愉悅。而在江南園林中與“橫云斷山”法相對應的空間處理手法是“障景”:明清小說敘事的“斷”對應江南園林構景的“藏”,明清小說敘事的“續”對應江南園林構景的“露”。園林空間中的“障景”是在歷時性的游園過程中,插入一景,形成游園時間上的縱向停頓與空間上的橫向拓展,然后又讓游園者歸復到歷時性的游園路徑上來,這使得游園者在曲折往復的園林空間中,體會園林意境的趣旨。而“橫云斷山”的敘事技巧亦是在敘事進程中攔腰隔斷的插入另一情節,然后再次復歸到敘事主干情節中。明清文人將“間三帶四”“橫云斷山”等敘事技巧“延異”到園林中,呈現出積極的互文性特征,使得小說的“元文本”含義得到了擴展——小說文本空間的敘事轉換技巧轉化為造園空間的處理手法,使得園林空間抑揚頓挫、顯隱有致,產生了悠遠的意境。
三 結語
詮釋明清小說敘事與江南園林空間經營的“互文性”結構意趣,使得江南園林與章回小說這兩個看似互異的“文本”,實際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明清文人將造園與作文類似,所建造的園林其實就是空間化的文學。漢寶德認為:“(明清)這群文人的建筑觀,與他們生活中最基本的成分——文學——的關系最為密切。他們對建筑的看法,則直接與他們的金石和繪畫的感覺相通。”明清園林與小說——這兩種“異質”文本所遵循的共同的敘事邏輯既內在地統攝著章回小說的文本結構關系,又指向江南園林的空間組織關系。兩種“敘事性”文本深處隱匿著共同的文化思維模式,瓦解了兩者結構內在的封閉性,拓展了“文本”間的開放性,構成了兩者的“互文性”關聯,亦成為文學與園林共通的“敘事之道”。
在當代西方思想體系的造園觀念盛行下,符合中國本土語境的造園法則式微,通過借助“互文性”這一新興的文藝理論,積極從中國文學等文化關聯域中找尋中國古典園林的造園思想與法則,期望為中國風景園林走出自己的道路提供一種可能。
(注:圖1改編自孫志剛《<金瓶梅>敘事形態研究》,哈爾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圖3、圖4自繪,圖2、圖5、圖6改編自劉敦楨《蘇州古典園林》,中國建筑出版社,2008年。)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betwee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Jiangnan Gardens
ZHANG Heng,LI Li
Abstract:
The gardening were flourish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t the same time,the literati novels creation and criticism became ma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the synchronic research on the narrative skill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the spacial transformation ways of the Jiangnan gardens,is to arg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space structure of the Jiangnan garde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it is possible to excavate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ocal gardening,and provide a way for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go out of its own way.
Key words: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iangnan gardens;narrative;space management;intertextuality
【責任編輯 陳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