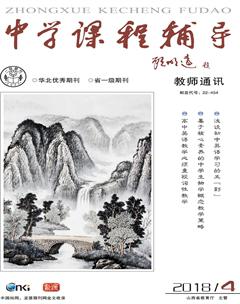例談“借古諷今”手法在高中語文“必修、選修”教材中的運用
楊小燕
借古諷今是一種經久彌新的寫作手法,它產生的很早,興盛于西晉,阮籍、嵇康、傅玄、陸基、潘岳、左思等人,把這種寫作手法錘煉得非常成熟。
余秋雨先生也曾說過,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大的抒情主題,不是愛,不是死,而是懷古之情,興亡之嘆。詠史詩就是以吟詠或評論歷史故事或人物為題材,借此抒發情懷,諷刺時事的詩歌。懷古詩是由作者身臨其舊地憑吊古跡而產生的聯想、想象,引起感慨而抒發情感抱負。
一、同是天涯淪落人
杜甫的《詠懷古跡》(其三)“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中,王昭君因漢元帝昏庸、不辨美丑而遠嫁異鄉,流離而不得歸,身死而遺長恨;而作者杜甫的一生,雖濟世之志甚高,但終其一生,也未得施展抱負。肅宗朝雖任職京師,也只不過是一左拾遺。就這,還因憂國惜才,上疏救房琯而觸怒肅宗,差點獲刑。雖獲救,卻終被疏遠,郁郁辭官,漂泊西南。 晚年的杜甫陷入了“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的境地,甚至于湘江的船上去世。享有絕世才貌的王昭君,擁有沉魚落雁之容,卻只能“獨留青冢向黃昏”;享有詩圣美名的杜甫,擁有“達”的本錢,卻只能“憑軒涕泗流”,命運所給予他們的只是無休止的思念和悲苦。
作者借王昭君當年想念故土、夜月魂歸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作者在詠嘆王昭君不幸的同時也在感嘆自己的不幸,在對王昭君的千載之怨寄予深厚同情的同時也暗含了對自己懷才不遇、抱負不得施展的惆悵。二人可謂是同病相憐。
二、雄姿英發VS早生華發
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中,周瑜文武兼備,其卓越的軍事謀略,對三國的鼎立和孫吳政權的鞏固影響很大。他指揮若定,善揚長避短,出奇制勝,作戰不畏艱險;而作者蘇軾因烏臺詩案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職位低,無實權。蘇軾在他的《自題金山畫像》中也說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瑜可謂是少年得志;而此時的蘇軾卻是“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所以在這首詞中,蘇軾借對周瑜的仰慕,抒發自己功業無成、壯志難酬的感慨。
三、舊瓶裝新酒
其實,借古諷今的手法不僅在必修三和必修四中的這兩首詩詞運用的很成功,其在必修三的《過秦論》以及選修的《阿房宮賦》、《六國論》、《伶官傳序》這些文當中也運用的很成功。
賈誼的《過秦論》被魯迅譽為“西漢鴻文”,名為過秦,實則過漢。通過敘述史實:秦崛起時之雄心勃勃;秦擴張時之所向披靡;秦統一時之勢如破竹;秦因施暴政使民怨聲載道導致秦之覆滅。秦興時所向披靡,亡時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攻時勢如破竹,守時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殺豪杰。分析秦滅亡的原因:當年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如今始皇余威震于殊俗,而陳涉只是氓隸之人,遷徙之徒也,卻亡秦族矣;況山東之國與陳涉不可同年而語矣。幾相對比,“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結論 自然就出來了。而賈誼生活的年代,表面上看似太平,實際上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如諸侯王的封建割據和中央集權之間的矛盾,匈奴屢次入侵和西漢人民希望安居樂業之間的矛盾,勞動者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等。作者看出了這些矛盾的存在,并且從秦王朝覆滅的歷史史實中意識到人民的力量的偉大。他希望通過對秦朝興亡的分析借古諷今,使漢王朝接受歷史的教訓,從而改革政治,調整矛盾,避免社會危機。
杜牧的《阿房宮賦》同樣是想通過秦統治者的窮奢極欲、殘酷剝削、橫征暴斂導致滅亡之事來諷諫當時的唐朝統治者無視歷史教訓,沉湎于聲色,又大起宮室,身居積薪之上,仍以為安。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呢?以此來警告當世:要戒奢愛民。
蘇洵的《六國論》圍繞中心論點“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展開論述的。通過論述六國滅亡的原因:弊在賄賂秦國,來勸勉宋王朝“無從六國破亡之故事”。蘇洵親歷北宋三朝,當時,遼崛起于北,西夏崛起于西北,他們時時侵宋給北宋朝廷造成很大的威脅。而北宋的統治者對他們妥協退讓,每年向他們交納幾十萬銀兩和大量的絹,得到的卻只是一夕安寢。古之六國與秦皆諸侯,六國雖弱卻猶有不賂而勝之之勢;今之北宋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則在六國下。結論:勿從六國破亡之故事。
歐陽修的《伶官傳序》,借后唐莊宗興衰之事,發出感慨,指出封建王朝的興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15年得天下之可謂壯哉;3年失天下之何其衰也!說古論今,目的在于告誡當時宋王朝的執政者,以莊宗寵幸伶人、身死國滅的歷史事實為教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
通過比較這四篇文章,我們發現,歷史是驚人的相似。《過秦論》和《阿房宮賦》同是以秦的滅亡為歷史教訓,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過秦論》側重講的是秦施行暴政而導致覆滅,《阿房宮賦》側重講的是秦貪欲而導致其覆滅。但歸根究底都是導致秦滅亡的原因。《六國論》和《伶官傳序》雖作者不同,但兩個作者卻生活在同一時代,他們只是借不同時代的歷史故事來勸宋王朝的統治者奮起反抗,要居安思危。
最后,引用《貞觀政要》中的一句話:“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杜甫和蘇軾以古人為鏡,明白自己的得失在何處。賈誼、杜牧、蘇洵、歐陽修則站在國家的高度,以歷史為鏡,看清了歷史的興亡,明白自己所處的時代的興替,創作出千古傳誦的名篇。賈誼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杜牧的“戒奢愛民”;蘇洵的“六國破滅,弊在賂秦”以及歐陽修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等不僅警戒當朝人,亦警戒于后人。
(作者單位:安徽省寧國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