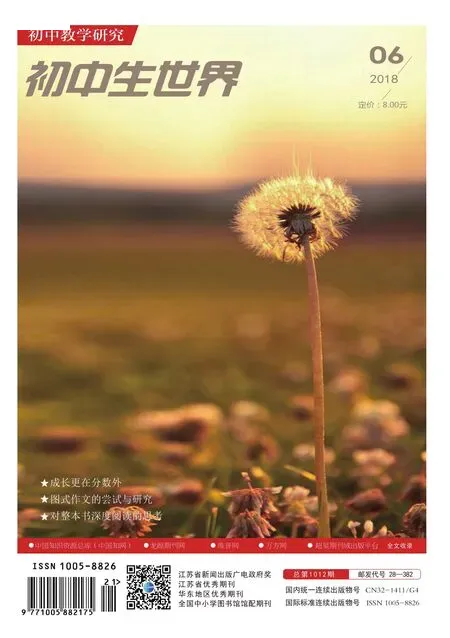對整本書深度閱讀的思考
■王躍平
深度閱讀是一種有品質的閱讀,對學生的情感發育、能力培養、知識拓寬、文化認同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但是,整本書閱讀因內容體量大、持續時間長,閱讀的困難也更大。因而,教師在進行閱讀指導時要考慮三個問題:一是如何規劃閱讀指導方案,提供閱讀策略,讓學生深讀;二是如何評價閱讀的“深淺”,歸納同類書籍的閱讀策略;三是如何將整本書閱讀與單篇、群文閱讀結合,讓學生在文化、文學素養的積淀上有所長進。那么,對整本書進行深度閱讀,我們要深入思考哪些問題呢?
一、評價閱讀深淺的一般標準
如何評價整本書閱讀的效果?如何判斷學生讀得深還是淺?我們首先要了解閱讀的一般層次,然后根據相關情況來評價。目前學界對閱讀層次的劃分標準,主要有以下幾種:
1.閱讀收獲。閱讀的任務,一是理解語言文字,二是運用語言文字。這本身就是閱讀的兩個層次,“運用語言”比“理解語言”的層次要高。《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把語文核心素養凝練、整合為四個方面,即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這四個方面也可以看作是閱讀中拾級而上的層次。
2.閱讀難度。美國的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將閱讀分為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和主題閱讀四個層次,四個層次是漸進的,由易而難。
3.能力發展。香港理工大學祝新華教授將閱讀能力分為復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鑒、創意六個層次。南京大學王彬彬教授認為,敘事類作品的閱讀有三個層次——情節人物、思想感情和語言寫法,這可以作為敘事類作品閱讀深淺劃分的一個標準。
4.閱讀目的。培根說:“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怡情即愉悅性情,是一個層次;傅彩即為自己增色,比怡情層次高;長才,即增長才干,將讀書所得轉化成能力,這是高標。
其實,以上幾種標準的共同點就是我們在閱讀中常說的感知、理解、分析、欣賞和運用等幾個層次。如果讀完一本書,只是達到感知的層面,那是淺的;如果能夠達到理解分析甚至是欣賞運用的層面,無疑是深的。如讀完《西游記》,只了解到本書主要寫唐僧師徒西天取經的故事,這是淺層的;如果進一步思考“為什么把唐僧的故事作為附錄”“這本書的情節鏈是怎樣的”“這本書的敘事線索是什么”等問題,那就達到“分析”的層面了。
二、評價閱讀深淺的基本策略
閱讀是很私人的事情,根據什么來判斷讀的“深淺”呢?在面對不同的學生時,我們又該怎么評判?我們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以下幾點:
1.基于年齡。同一本書,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乃至指導閱讀的語文教師,需要達到的閱讀層次是不同的。我們以《西游記》為例,小學生主要在情節人物上下功夫,須掌握以下內容:每一回寫了怎樣的故事?前一回和后一回之間是怎樣銜接的?前一個人和后一個人之間有何關系?人物有怎樣的特點……初中生則可能需要讀出情節的起伏與波瀾、作用與特色。當然,初中生如果僅僅讀到情節和人物層面是遠遠不夠的,根據基礎情況,還應該讀到思想、語言和寫法的層面。高中階段,學生如果重讀《西游記》,就應該做一些專題的研究,如分析《西游記》的結構藝術,進行語言欣賞、情節欣賞等。
語文教師的閱讀,不僅為了豐富自己,還要擔負指導學生的重任,應該是偏向專業化的閱讀,與社會化的閱讀不同。社會化閱讀是一種個性化、主動式閱讀,它關注人物的命運和情節的曲折,收獲的是情感或價值的浸潤。專業化閱讀則是帶著專業的眼光、根據專業的需要來閱讀。如“語文視角”的閱讀,它強調情節的合理性、邏輯性,強調人物形象的個性和塑造的意義,關注作品是怎么寫出來的,用了怎樣的表達方式、表現技巧、敘述視角及什么樣的語言等。
作為專職教學整本書閱讀的語文教師,更應該在尋找“悅讀”和“深讀”的教學點上多下功夫,為學生選定路標、引導方法、提供策略,促使學生喜歡閱讀、深入閱讀,獲得更多的營養。如教學《西游記》時,可以選擇“取經團隊的妖怪”這個“路標”,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引導學生分析他們成妖的過程:孫悟空因為個性鮮明、桀驁不馴被壓在五行山下;豬八戒因為酒后調戲嫦娥被貶為妖怪,流落云棧洞;沙僧因為打破琉璃盞被貶為河妖,在流沙河每七日要受萬箭穿心之痛;小白龍因為縱火燒了“殿上明珠”,要被天庭斬首,觀音救下他,將他選為取經人,在鷹愁澗等候師父的到來。另外,唐僧原是如來的二弟子,只因為有一次如來講經時沒有“認真聽講”,就被貶下凡界,經受九九八十一難。以上種種,都可能是影射明朝“輕罪重罰”的現象。這些分析會讓學生明白作者的寫作是有深意的,涉及閱讀的思想層面。
2.基于讀情。如果班級中大多數學生只達到了閱讀的感知層面,而教師能引導他讀到理解層面,那就是進步。如果學生已經感知了情節,教師能引導其用特定的語言形式將情節概括出來,或者畫出情節鏈,梳理出作品的情節脈絡,這就是又深入了一步。如學生講述“蓮花洞高懸”(“九九八十一難”中的第25難)這一難時,畫出了這一難的情節結構圖并且用七言句子概括如下:
銀角智擒三師徒——行者被壓力不足——銀角差使收悟空——行者變身騙寶物——銀角派兵請干娘——行者計奪幌金繩——銀角念咒縛大圣——行者耍計巧脫身——銀角使寶裝心猿——行者再逃換葫蘆——銀角不敵進葫蘆——行者智破蓮花洞
學生在原來感知第25難的基礎上,用特定的語言形式畫出情節鏈,在原來的閱讀基礎上有所提升。因此,教師在制定深度閱讀的標準時,首先應該考慮學生的閱讀情況。如果教師的教學能讓學生在現有的基礎上有所提升,那就是“深讀”了。
3.基于作品。有人把適合學生閱讀的書分為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兩類。非虛構類的作品主要指實用類文體,閱讀時著眼于提取信息、整合信息和推斷結論三個層次;虛構類作品主要指文學類作品,閱讀時側重于寫了什么、為什么要寫這些、是怎樣寫的和這樣寫有何妙處四個層次。
不同讀者對同一部作品,由于理解力的不同,或者理解視角的差異,有的讀得比較膚淺,有的比較深入。如同樣是讀《西游記》這本書,有的人只讀到了故事,有的人卻讀出了思想,這是閱讀的深淺之分。如郭沫若讀了《西游記》的“三打白骨精”后,寫了這樣一首詩:“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毛澤東也寫了一首詩和郭沫若:“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很多人讀“三打白骨精”,讀到的只是故事,這是“照著講”,而這兩位大家則是“接著講”。因為所處的位置不同,擔任的社會角色不同,他們對同一個故事產生了不同的感悟:郭沫若批判唐三藏,毛澤東贊美孫大圣。再深一步分析,郭沫若希望自己能夠遇到智慧清明的領導;毛澤東作為領導人,希望手下個個都是孫悟空。
日本的山本玄絳禪師說:“一切諸經,皆不過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其實,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讀者的角色與經典一樣重要。閱讀《西游記》,學生讀到的可能是故事,是成長,老師讀到的可能是人生,是思考;小孩子讀到的可能只是好玩有趣,大人讀到的則可能是嚴謹有序;研究佛教的人讀到的可能是佛法,信奉道教的人讀到的可能是道教秘學。在與經典對話的過程中,讀者不斷地生發出新意義來。經典之所以經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閱讀經典一方面要“照著講”,另一方面也要“接著講”。但不管是“照著講”還是“接著講”,最終目的都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4.基于標準。依據上述評價整本書閱讀深淺的一般標準,可以設計一些問卷,通過問卷來了解學生閱讀的層次。如就敘事類作品而言,可設計以下問題。

寫法用什么方法寫?結構如何安排?寫法和結構是如何呈現的?語言語言有何特色?語言特色是怎樣顯現的?感知 理解 分析 欣賞 運用情節人物寫了什么人(事)?這個人(事)在作品中處于什么地位?他(它)與別的人(事)是什么關系?分析人物(情節)之間的關系:人物鏈及人物關系圖是怎樣的?情節鏈是怎樣的?欣賞情節的波瀾;欣賞人物的獨特。思想感悟為什么要寫這些?思想感悟源于什么?表達這樣的思想感悟有何目的?語詞特點、修辭特色、句式特點、話語體系各是怎樣的?欣賞語言的獨特與精妙之處。運用這樣的方法和結構有何妙處?修辭手法、寫作方法、思路結構各是怎樣的?如果重新調整情節或設置人物,會如何?這樣的思想感悟給我們怎樣的啟示或幫助?怎樣在自己的文章中表達感悟或思考?我能學到什么樣的表達?我能學到什么樣的方法或結構?
表中的問題,橫向與縱向都有由淺入深的變化,非敘事類的作品也可以參照執行。這本書“寫了什么”屬于“感知”,“為什么要寫這些”屬于“理解”,“它是怎么寫的”屬于“分析”,“為什么要這樣寫”屬于“欣賞”,“這本書帶給我怎樣的新思考、新思路”屬于“運用”。
三、需要注意的問題
深度閱讀是在“深度學習”的基礎上提出的,為了更好地引導學生進行深度閱讀,教師還須注意以下問題。
1.深而有“界”。深度閱讀要考慮讀者的年齡特點,要關注學生的閱讀起點,要注意閱讀的學科特色,還要了解學生的閱讀興趣,不能舍本逐末、殺雞取卵,要讓學生愛上閱讀,成為“好讀者”,養成終身閱讀、終身學習的好習慣。我們必須思考:深度閱讀的落腳點在哪里?是為考試而讀,還是為提升自身素養而讀,抑或是為傳承文化而讀?
2.深而有“展”。“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深度閱讀的研究并不排斥“多閱讀”,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廣收博覽可以促進深度閱讀,深度閱讀又能帶動閱讀視野的拓展,由讀好一本書到讀好一類書,再到跨學科閱讀甚至全科閱讀。
3.深而有“序”。俗話說“一口吃不成胖子”,深度閱讀也是這樣,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深度閱讀的指導需要循序漸進:首先要進行讀情調研,然后根據閱讀情況設計推進路徑,提供相應的策略支持或工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