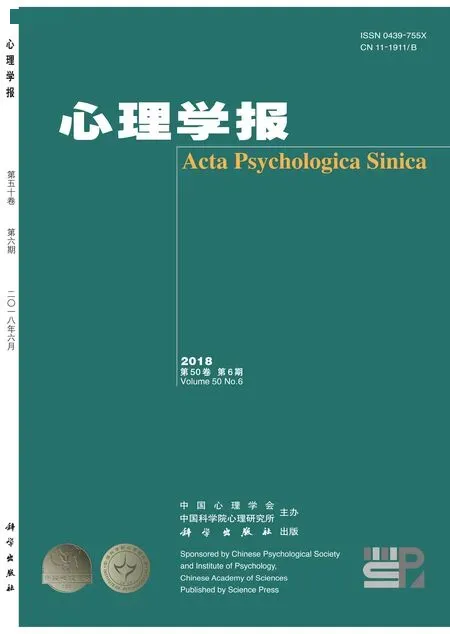領導創造力期望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劉偉國 房儼然 施俊琦 莫申江
(1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 廣州 510275) (2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杭州 310058)
1 問題提出
團隊領導是推動團隊實現創造性結果的一大關鍵推力(Drazin, Glynn, & Kazanjian, 1999; 羅瑾璉, 門成昊, 鐘競, 2014)。領導創造力期望能顯著提升成員們的創造動機(Tierney & Farmer, 2011)。然而, 這不足以闡明領導如何促使團隊形成集體性創造力(collective creativity)。一方面, 領導創造力期望會改變團隊內每個個體對集體性創造知識如何被創生的認知(Drazin et al., 1999; Ford, 1996); 另一方面, 創造努力轉化為創造力, 取決于領導是否能有效激發集體性知識分享和深度加工(蔡亞華, 賈良定, 尤樹洋, 張祎, 陳艷露, 2013; Marrone, Tesluk& Carson, 2007)。因此, 要想真正理解領導創造力期望如何影響團隊創造力, 在關注創造動機變化的同時, 必須理解團隊知識創造的認知機制。
回應上述問題, 我們融合Kelley (1952)的規范參照群體理論(normative reference group theory)與Grand, Braun, Kuljanin, Kozlowski和Chao (2016)的團隊知識創造的過程導向理論(process-oriented theory of knowledge emergence in teams), 提出團隊領導影響團隊創造力的認知過程模型。規范參照群體理論指出, 設定行為規范的關鍵參照對象(significant others)的期望是人們評估自己下一步應該采取什么行動的重要指引(Kelley, 1952; Merton, 1957)。在創造性工作團隊中, 團隊領導掌握創造資源, 擔當關鍵風險, 把握創造目標(Jung, Chow, & Wu, 2003)。因此, 領導的創新倡導行動直接影響團隊內部現有知識交換和外部新鮮知識獲取等(Bresman & Zellmer-Bruhn, 2013; Chung & Jackson, 2013; Grand et al.,2016)。同時, 集體性創造力不是成員們分別獲得新鮮知識, 就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Grand et al., 2016)。新知識轉化為創造性結果的過程中, 成員們必須投入更多認知資源, 面對大量創造風險(蔡亞華等,2013; Marrone et al., 2007)。這一集體性加工過程必須匹配團隊領導的高度承諾和示范參與。
因此, 本研究預期有助于人們理解團隊創造力形成的認知機制, 拓展規范參照群體理論在團隊創造力領域的解釋效力, 并通過刻畫團隊領導在集體性知識創造的學習和分享過程中的影響效果, 強化團隊知識創造理論。
1.1 領導創造力期望和團隊新知識獲取行為
團隊領導能夠直接影響團隊目標設定, 設定內部合作流程, 并決定獎懲規則等(Mumford, Scott,Gaddis, & Strange, 2002; 蔡亞華等, 2013)。成員們通常將團隊領導的期望和行為作為群體規范的關鍵線索, 并依此來調整自身工作行為(Kelley, 1952)。領導創造力期望是指團隊領導基于工作職位, 對成員們付出創造性努力、實現創造性結果的工作要求和規范設定。當成員們清晰地感知到團隊領導對集體創造性結果提出較高期望時, 會對團隊創造性目標形成一致看法, 積極采取創造學習行動, 尋求有助于產生創新想法的新知識和信息(Drazin et al.,1999; Ford, 1996)。
團隊知識創造的過程導向理論指出, 團隊要想實現集體性創造結果, 必須首先促使成員們通過團隊內交流和團隊外探索等兩種方式, 獲得新鮮知識,拓展各成員加總的知識池(knowledge pool), 以支撐團隊整體下一步開展集體性知識加工(Grand et al., 2016)。一方面, 成員們會形成較為一致的集體目標和創造性規范認知(Collins & Smith, 2006), 并感受到創造性工作壓力, 意識到無法僅依賴現有知識和方法來獲取創造性結果。因此, 他們會更積極地貢獻各自擁有的知識, 內部開展高頻率知識交換,以期成員們能夠發現新鮮點子或解決思路(Gong,Kim, Lee, & Zhu, 2013; Paulus & Yang, 2000; Teigland& Wasko, 2003)。基于以上理論推導, 我們提出假設1。本研究包含的所有研究假設見圖1所示。
假設1:領導創造力期望有助于促進團隊知識交換行為。
另一方面, 當領導提出對創造性成果的明確期望, 成員們會積極開拓思路, 嘗試從團隊外部找出解決問題的新辦法(例如, Grand et al., 2016)。具體來說, 成員們會共同意識到現有知識和方法存在局限性, 無法創造新點子和解決方案; 必須打破團隊已有知識體系, 從外界補充新鮮知識。因此, 成員們跨越團隊邊界, 從外部尋求有助于實現團隊創造性工作結果的新鮮知識(Marrone et al., 2007;Teigland & Wasko, 2003)。因此, 假設2如下所示:
假設2:領導創造力期望有助于促進團隊邊界跨越行為。
1.2 領導創造力期望影響團隊創造力:知識交換行為和邊界跨越行為

圖1 研究假設模型
充分的知識交換能夠促使團隊成員們在自身知識積累基礎上, 更加準確地理解團隊內其他成員所具備的知識和專長, 以促使成員們開展知識重構,產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案(Janis & Mann, 1977), 最終提升團隊整體創造力(Gong et al., 2013)。這一結論在不同類型的團隊場景中, 例如, 研發團隊(Gong et al., 2013; Shin & Zhou, 2007)、銷售團隊(Sung &Choi, 2012)、生產制造團隊(Zhang, Tsui, & Wang,2011), 均獲得了有效驗證。綜合假設1中有關領導創造力期望影響團隊知識交換行為的理論推導, 我們提出如下假設3。
假設3: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對領導創造力期望與團隊創造力間關系具有顯著的間接作用。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是指團隊成員們跳出團隊邊界, 積極與團隊外部人員建立聯系, 汲取新鮮知識和想法, 并引入到團隊工作中來(Faraj & Yan,2009)。研究表明,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能夠顯著拓展團隊的知識范圍(Ancona & Caldwell, 1992; Cross &Cummings, 2004; Tushman, 1977), 為團隊帶來與其原本擅長的領域截然不同的新思路和新方法(Malhotra & Majchrzak, 2004), 提升團隊構思新方案的能力(Weisz, Vassolo, & Cooper, 2004)。因此,綜合假設2有關領導創造力期望與團隊邊界跨越行為的關系推導, 我們得到如下假設4。
假設4: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領導創造力期望與團隊創造力間關系具有顯著的間接作用。
1.3 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的調節效應
團隊知識創造可劃分為新知識學習(learning)和新知識分享(sharing)兩個階段; 集體性創造力不是成員們分別獲得新知識, 就自然后續形成的結果(Grand et al., 2016)。與獲取新知識相比較, 成員們為了將新知識轉化為創造性結果, 必須投入更多認知資源, 面對大量創造風險, 并就如何將新知識應用到創造工作中去達成共識(蔡亞華等, 2013; Grand et al., 2016; Marrone et al., 2007)。這一過程中, 成員們將更加依賴“團隊是否真正將創造力作為核心價值”等規范信息(Farmer, Tierney, & Kung-McIntyre, 2003)。因此, 非常有必要引入創造力角色認同(Callero, 1985; Callero, Howard, & Piliavin,1987; Grube & Piliavin, 2000), 即團隊領導“多大程度上認同創造力價值, 并視自己為創造力踐行者”(Farmar et al., 2003; 楊晶照, 陳勇星, 馬洪旗,2012)。
團隊內部知識交換促進成員們準確理解其他成員的知識專長, 實現知識重構; 但同時耗費大量認知資源, 打破心理安全(Edmondson, Dillon, &Roloff, 2007)。高創造力角色認同的團隊領導會充分利用自身地位, 促進成員們形成關于創造力價值的統一看法, 并促進深度溝通和協作(Collins &Smith, 2006), 樹立創造力榜樣, 設置清晰的團隊創新規范(Jaussi & Dionne, 2003)。這一情境下, 成員們更愿意采納互動獲得的新思路來設計創新方案(Basadur, 2004; Paulus & Yang, 2000)。相反地, 低創造力角色認同領導無法給予直接指引, 甚至不明確創造性努力究竟是否真正被團隊尊重和認可, 將導致成員們難以全心投入創造性試錯轉化過程。同時, 團隊領導的創造力期望是推動團隊成員們開展內部知識交換的關鍵動力。綜合起來,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5: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對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和團隊創造力間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具體而言, 當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較高時,團隊知識交換行為更有利于提升團隊創造力。
假設6: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對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而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具體而言, 當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較高時, 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知識交換行為提升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作用更為顯著。
以往研究指出, 盡管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能夠增加團隊內知識總量, 但其存在潛在負面影響(例如,Ramarajan, Bezrukova, Jehn, & Euwema, 2011)。團隊整體必須承擔較大風險(Glover & Sautter, 1977)。成員們分享彼此擁有的新知識, 比單純的知識學習過程要耗費更多資源(Grand et al., 2016), 容易導致負面情緒、角色過載(Marrone et al., 2007; Ramarajan et al., 2011)。這些都可能導致內部協作能力顯著降低, 最終削弱集體性創造效能。
因此, 團隊領導展現出對創造力工作的承諾度和榜樣作用, 對邊界跨越成功至關重要。一方面, 高創造力角色認同的團隊領導會不斷向成員們傳遞有關創造力重要性的價值觀點, 并通過自身參與, 幫助成員們減輕外部學習導致的角色過載壓力(Cheung& Wong, 2011; Marrone et al., 2007)。另一方面, 高創造力角色認同的團隊領導提供良好表率, 降低邊界跨越不確定性。因為領導擔當創新風險, 成員們更敢于面對潛在失敗風險, 開展集體性試錯。進一步結合領導創造性期望促進團隊邊界跨越行為的理論推導, 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7: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對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和團隊創造力間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具體而言, 當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較高時,團隊邊界跨越行為更有利于提升團隊創造力。
假設8: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對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而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具體而言, 當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較高時, 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邊界跨越行為提升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作用更為顯著。
2 研究方法
2.1 樣本和調查過程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位于中國北京和深圳的4家科技型公司。它們主要提供IT軟件開發服務。項目研發團隊是這些公司的基本工作單元,并承擔著實現產品和技術創新的主要功能。所有參與問卷調查的員工均是自愿參與本項研究, 并在其工作時間內完成了問卷填寫。
我們分別在三個時間點收集研究數據, 中間分別間隔兩個月時間。第一階段時, 我們收集了樣本人員們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包括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在現有職位上工作期限), 并統計了參與調研團隊的規模; 同時, 團隊成員們評價團隊領導對他們創造力的期望水平。第二階段時, 團隊成員們主要對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和邊界跨越行為進行評估。第三階段時, 團隊領導除了評價自身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之外, 還對其所負責的團隊的創造力水平進行評價。
我們總共向4家公司中的132個項目團隊發放了650份紙質問卷, 第一輪回收了來自130個團隊的 638份問卷; 第二輪回收了來自 116個團隊的568份問卷; 第三輪時, 我們成功得到了所有樣本團隊領導的問卷回應。因此, 我們最終得到了來自116個項目團隊的 568份有效問卷, 有效回收率為87.4%。團隊規模均值為4.86(標準差為2.28), 所有樣本團隊接受問卷調查的成員覆蓋率均達到了90%以上。樣本人員的平均年齡為27.89歲(標準差為2.27), 其中490位為男性, 在現有工作崗位上的平均任期為1.67年(標準差為0.93)。
2.2 測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Brislin (1970)推薦的回譯的方式將英文量表翻譯為中文。若非特別說明, 本研究的各個量表均選用了Likert 7點量表進行測量, 其中, 1表示“完全不準確”, 7表示“完全準確”。
領導創造力期望 本研究采用由 Tierney和Farmer (2004)開發的量表來測量團隊成員感知的團隊領導對其創造力的期望。該量表共包含3個題項, 分別為“我的上司期望我做有創造性的工作”,“我的上司視創新為我日常工作要求的一部分”, 以及“我的上司期望我創造性地解決問題”。我們選用了 Likert 7點量表, 其中,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7表示“完全同意”。這一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7。
團隊知識交換行為 本研究選用 Collins和Smith (2006)的量表來測量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該量表共包含 8個題項, 例如“通過互相交流和整合思想, 能比單打獨斗更快地推進新項目”和“經常感到通過交流和整合思想, 從彼此學到了東西”等。團隊成員依據自身團隊互動感受, 對團隊內知識交換情況做出評價。這一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92。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 本研究采用 Faraj和 Yan(2009)開發的量表測量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該量表共包含 4個題項, 例如“與團隊外的重要人物接觸,為團隊獲得信息和資源”和“重視團隊成員利用自己在團隊以外的關系獲得的信息和資源”等。這一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2。
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 本研究采用Farmer (2003)等學者開發的量表來測量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該量表共包含 3個題項,由團隊領導自我評價在多大程度上“經常想著要有創意”, “時常抱有我是一個‘創造性個體’的自我概念”, 以及認為“成為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個體是我個人身份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一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8。
團隊創造力 本研究采用了 Shin和 Zhou(2007)開發的團隊創造力量表, 由團隊領導對其所負責的團隊進行評價。該量表包含4個題項, 例如,你所領導的團隊 “在提出創意上做的有多好?”和“創意有多好的實際效果?”等。Likert 7點量表中, 1表示“非常差”, 7表示“非常好”。這一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90。
控制變量 以往研究文獻指出, 團隊規模、成員年齡構成、在現有職位上的工作期限長短, 教育水平差異, 以及團隊成員的創造力自我效能水平等都可能對團隊成員們開展交流和互動的模式以及團隊創造力水平產生影響(例如, Brooke, Rasdi, &Samah, 2017; Hirst, van Knippenberg, & Zhou, 2009;Koriat & Gelbard, 2014; Marrone, Quigley, Prussia,& Dienhart, 2016; Somech & Drach-Zahavy, 2013;Tierney & Farmer, 2002)。因此, 本研究控制了團隊規模、團隊成員的平均年齡、團隊成員在現職位上的平均工作期限, 團隊成員的平均教育水平, 以及團隊成員創造力自我效能感對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團隊邊界跨越行為以及團隊創造力的影響作用。我們選用Tierney和Farmer (2002)開發的創造力自我效能感量表來測量團隊成員的創造力自我效能感。該量表包含3個題項, 由團隊成員評價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擅于想出新點子”, “對運用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信心”, 以及“擅長從別人的點子中, 發展出另一套自己的想法”。這一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6。另外,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樣本來自 4家公司, 因此我們在數據分析中也加入了3個虛擬變量, 以控制樣本來源對模型估計產生的影響。
2.3 多水平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了確信本研究采用的各個測量量表能夠有效捕捉相應變量, 我們針對研究主要變量(領導創造力期望、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團隊邊界跨越行為,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 領導評價的團隊創造力)開展多水平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見, 五因子模型能夠較好地擬合數據, χ=629.71,
df
= 286, RMSEA = 0.05, CFI = 0.92, TLI =0.90, 組內SRMR = 0.04, 組間SRMR = 0.07。另外,考慮到團隊知識交換和邊界跨越行為都是新知識獲取行為, 而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和團隊創造力都由團隊領導在第三次問卷調研中進行評價, 我們也檢驗了四因子模型A (將團隊知識交換和邊界跨越行為合并為一個因子, 而領導創造力期望、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團隊創造力作為三個單獨因子), 四因子模型B (將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團隊創造力合并為一個因子, 而領導創造力期望、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團隊邊界跨越行為作為三個單獨因子), 三因子模型(將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合并為一個因子, 將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團隊創造力合并為一個因子, 而領導創造力期望作為一個單獨因子), 雙因子模型(將團隊成員評價的領導創造力期望、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合并為一個因子, 將團隊領導評價的自我創造力角色認同和團隊創造力合并為一個因子)和單因子模型(將所有主要變量合并為一個因子)的模型擬合結果。從表1可讀, 相較五因子模型而言,四因子模型A、四因子模型B、三因子模型、雙因子模型和單因子模型的擬合度均顯著下降(Δχ=541.48, Δdf
= 6; Δχ= 107.73, Δdf
= 4; Δχ= 647.12,Δdf
= 9; Δχ= 1486.45, Δdf
= 12; Δχ= 1604.37,Δdf
= 13)。因此, 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 研究假設的五要素模型的擬合效果最佳, 為量表的內容效度和區分效度提供了有力支持。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3 研究結果
3.1 數據聚合
本研究采用了團隊水平的研究設計, 但領導創造力期望、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和邊界跨越行為的測量都是在團隊成員個體水平上進行的。因此, 我們首先需要確認個體水平上測量獲得的數據可以被聚合到團隊水平上進行統計分析。我們通過計算各個變量的ICC (1), ICC (2)以及
r
中位數來驗證數據聚合的合理性。具體而言, 團隊成員創造力自我效能的ICC (1) = 0.12, ICC (2) = 0.38,r
中位數為0.90; 領導創造力期望的ICC (1) = 0.09, ICC (2) =0.33,r
中位數為0.90; 團隊知識交換行為的ICC(1) = 0.11, ICC (2) = 0.37,r
中位數為0.97;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的ICC (1) = 0.08, ICC (2) = 0.30,r
中位數為0.93。這些結果表明, 團隊的組間差異能夠解釋團隊成員創造力自我效能12%的方差、領導創造力期望9%的方差、團隊知識交換行為11%的方差、以及團隊邊界跨越行為 8%的方差, 且不同團隊成員的評分具有足夠的組內一致性, 能夠聚合為團隊水平的變量開展后續分析。由于本研究選用的樣本團隊規模相對較小(n
= 4.86), 因此導致ICC(2)結果相對偏低。我們在問卷發放和回收中, 均保證了90%的團隊成員覆蓋率(參見Koopmann, Lanaj,Wang, Zhou, & Shi, 2016)。我們認為, 該數據能夠保證團隊均值的準確性。因此, 本研究后續分析采用聚合到團隊層面的創造力自我效能感、領導創造力期望、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和團隊邊界跨越行為。3.2 數據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 Mplus 7.2軟件, 通過估計兩個獨立的模型來分別檢驗中介假設和調節假設。具體而言, 在模型一中, 我們在控制了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的影響基礎上, 同時估計了領導創造力期望對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以及團隊知識交換和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進而, 根據模型一結果, 通過計算 bootstrap置信區間的方式來估計領導創造力期望對團隊創造力的間接影響。在模型一的基礎之上, 我們在模型二中加入中心化之后的中介變量(團隊知識交換和邊界跨越行為)與調節變量(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的交互項作為團隊創造力的預測項, 并通過計算bootstrap置信區間的方式估計了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對模型一中所估計的間接效應的邊界調節作用。在檢驗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的調節效應中, 我們也依據Cohen, Cohen,West和Aiken (2013)的推薦, 依據不同程度的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1/?1
SD
)作圖進行分析。3.3 描述性統計分析
各個變量的平均值、相關系數、標準差與信度系數等均已總結在表2中。從表2可見, 團隊領導創造力期望與團隊知識交換行為(
r
= 0.20,p
< 0.05)以及團隊邊界跨越行為(r
= 0.28,p
< 0.01)顯著正相關。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與團隊創造力顯著正相關(r
= 0.24,p
< 0.05), 但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與團隊創造力間關系并不顯著(r
= 0.13,p
> 0.05)。假設1、假設2和假設3得到了初步結果支持。3.4 假設檢驗
我們用 Mplus7.2估計模型中各變量間的非標準化路徑系數, 并將結果總結于表3和圖2中。首先, 由表 3中模型一的系數估計結果可見, 團隊領導創造力期望顯著促進團隊知識交換行為(
γ
= 0.15,p
< 0.05)和團隊邊界跨越行為(γ =
0.22,p
< 0.01)。因此, 本研究的假設1和假設2得到了數據支持。其次, 團隊知識交換行為顯著提升了團隊創造力水平(γ =
0.50,p
< 0.05), 而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與團隊創造力間的關系并不顯著(γ
= ?0.14,p
> 0.05)。本研究通過計算5000次bootstrap來估計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知識交換行為或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間接作用的置信區間。結果表明領導期望通過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間接效應為0.073, 95%的bootstrap置信區間為[0.013, 0.188]; 領導期望通過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間接效應為?0.030, 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171, 0.028]。因此, 領導創造力期望能夠通過顯著增強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而間接提升團隊創造力, 但不能夠通過顯著增強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而間接提升團隊創造力。因此, 本研究提出的假設3得到了有力支持, 而假設4沒有得到支持。
表2 研究變量的平均值, 標準差, 信度和相關性

表3 回歸分析結果

圖2 研究模型中各路徑系數結果圖
由表3中模型二以及圖2所示, 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沒有呈現對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與團隊創造力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γ
= ?0.30,p
> 0.05),但對團隊邊界跨越行為與團隊創造力間關系具有顯著調節作用(γ
= 0.42,p
< 0.05)。參照 Cohen 等(2013)的建議, 我們將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的調節作用在圖3中加以展示。可見, 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較低時,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不利于團隊創造力水平提升(γ
= ?0.64,p
< 0.05); 而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較高時,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的消極作用不再顯著, 并呈現出正向促進團隊創造力的趨勢(γ
= 0.20,p
>0.05)。因此, 本研究提出的假設 5沒有被支持, 而假設7得到有力支持。
圖3 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的調節效應
本研究也通過計算bootstrap置信區間, 檢驗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對領導創造力期望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的調節作用。一方面, 團隊領導的創造性角色認同水平并不能顯著調節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間接效應(
γ
= ?0.044, 95% CI = [?0.164, 0.002])。假設6沒有獲得支持。另一方面, 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顯著調節了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間接效應(γ
=0.093, 95% CI = [0.014, 0.252])。具體而言, 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較低時, 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間接影響為?0.142 (95% CI = [?0.376, ?0.020]); 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較高時, 該間接效應為0.044 (95% CI = [?0.057, 0.202]), 二者之間的差異為0.185 (95% CI = [0.029, 0.504])。因此, 假設8得到有力支持。4 討論
4.1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發現, 團隊領導創造力期望能夠有效地促進團隊知識交換行為以及邊界跨越行為。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能夠直接提升團隊創造力, 不受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的調節影響; 而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則取決于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這一邊界條件。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較低時,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而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水平較高時,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呈現出正向影響團隊創造力的趨勢。
我們認為, 之所以團隊知識交換行為和邊界跨越行為影響團隊創造力的機制存在顯著差異, 是因為團隊成員們在通過內部知識交換和外部跨界學習提升集體創造力的過程中, 面臨著不同程度和類型的創新壓力和不確定性。因而, 成員們在開展集體性知識加工的過程中, 對團隊領導提供創新規范的依賴度也明顯不同。具體而言, 雖然團隊知識交換和邊界跨越行為都是團隊獲取新興知識和信息的重要方式, 但團隊成員們在處理由內部知識交換獲得的新知識時, 主要基于彼此現有的信息及資源,進行集體互動而產生知識增量(Gong et al., 2013;Paulus & Yang, 2000; Teigland & Wasko, 2003)。同時, 團隊內既有的一定程度的成員們相互協作的創造工作模式, 也有利于成員們將各種創造努力轉化為最終創造性結果。而團隊成員們在處理由邊界跨越行為獲取的新知識時, 則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和資源, 面臨更高風險性和不確定性, 設法建立起外部新知識與團隊創造性目標間的緊密關聯(Teigland& Wasko, 2003)。因此, 相較于團隊知識交換行為,開展邊界跨越行為的團隊成員們會承擔更高的創新壓力和風險(Marrone et al., 2007; Zhao & Anand,2013)。只有當團隊領導向成員們充分展示其對創造性工作的真實承諾和充分支持時, 團隊整體才可能打破原有知識體系, 讓從團隊外部引入的新知識真正發揮創造性價值。反之, 在缺少團隊領導對創造性過程和結果的真實鼓勵和認同的情況下, 引入大量新知識, 反而會導致團隊創新停滯。
4.2 理論意義
本研究在現有團隊創造力研究文獻的基礎上,主要考察領導創造力期望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和邊界條件, 并獲得了以下幾方面主要的理論貢獻。
首先, 本研究通過展現領導創造力期望感知影響團隊創造力的認知機制, 顯著促進了人們對于團隊領導在團隊創造力產出過程中扮演角色的深入理解。具體而言, 以往團隊創造力研究著重強調了團隊領導能夠提升團隊成員們的創造動機(例如,自我創造力效能感), 而較少關注其對團隊成員們創造性認知過程的影響。整合規范參照群體理論(Kelley, 1952)和團隊知識創造的過程導向理論(Grand et al., 2016), 本研究闡明了團隊領導創造力期望通過規范成員們在團隊內部和團隊外部開展創造性知識學習, 并最終實現集體性創造結果的過程機制。
其次, 本研究通過刻畫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對于團隊創新知識學習影響團隊創造力關系的調節作用, 拓展了規范參照群體理論在團隊創造力領域的解釋效力。近年來, 在創造力研究領域中,學者們持續號召應當深入探討領導角色之于創造力提升過程的價值(Amabile, Schatzel, Moneta, &Kramer, 2004; Mumford et al., 2002)。依據規范參照群體理論思路, 本研究發現, 只有當團隊領導表達出高水平創造力期望的同時, 認同并重視將創造學習努力真正轉為集體性創造結果, 身體力行加以推動, 才能夠幫助團隊成員們克服邊界跨越行為的潛在負面效果, 真正促進團隊創造力提升。
第三, 本研究將團隊領導因素納入團隊知識創造的過程導向理論框架, 闡明了團隊領導的創造力期望和自身創造力角色認同在集體性知識創造學習和分享過程中的影響作用。這一方面強化了團隊知識創造過程理論在創造力領域的解釋效力, 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對于新知識創造過程理論的團隊情境邊界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 提升該理論的應用價值。
4.3 實踐啟示
本研究聚焦探討團隊領導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機制, 對企業優化創造力管理實踐具有重要借鑒意義。首先, 企業組織或工作團隊的領導者應當采取適當措施, 幫助成員們準確地把握群體對于創造力及創新結果的重視和期望, 進而引導成員們積極開展不同形式的知識獲取行動, 為實現集體創造力提升打下堅實基礎。其次, 企業管理者和員工們都應當意識到,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帶來豐富、多元的新鮮知識的同時, 也會產生不確定性。因此, 我們建議企業組織應當更加有針對性地倡導成員們開展跨界學習, 并與內部知識交換形成有效協同。第三, 團隊領導要想成為一名高效的創造力推動者,就必須在強調提升團隊創造力管理能力的同時, 向成員們清晰說明創造性工作的預期目標, 充分認可創造性結果的真實價值, 并親自參與到團隊創新工作中去。單一地要求團隊成員們變得更加具有創意,而不為他們做出真實榜樣, 將無法真正激活團隊創造力。
4.4 研究局限性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首先, 在研究測量方面, 在綜合考慮問卷調研的可行性之后, 本研究將團隊領導的創造性角色認同安排在第三階段,而非第二階段進行測量。以往研究表明, 個體的角色認同屬于相對穩定的個人特質(Farmer et al.,2003), 不會在短期內發生重大變化。因此, 我們認為, 本研究運用在第三階段測量的團隊領導創造力角色認同進行分析是可行的。但與此同時, 我們建議未來研究應當采用更加嚴謹的研究設計。其次,本研究采用了團隊成員個體評價并聚合到團隊層面的方式, 測量成員們感知到的團隊領導創造力期望 。雖然較高的組內一致性確保了本研究測量的有效性, 但我們建議未來研究應當提出更加細膩的領導創造力期望測量思路, 例如社會網絡或時序研究設計, 捕捉不同成員對領導創造力期望感知差異的原因及其對團隊互動的影響效果。第三, 以往文獻顯示, 變革型領導、領導開放性等領導特質或行為變量會對團隊創造力產生顯著影響(例如, 蔡亞華等, 2013)。因此, 我們建議未來研究考慮更加細膩地控制其他領導特征或行為前因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5 結論
團隊領導的創造力期望顯著地促進團隊知識交換和邊界跨越行為。其中, 團隊知識交換行為能夠直接提升團隊創造力;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的直接影響效果并不顯著, 受到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的顯著調節。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較低時, 團隊邊界跨越行為對團隊創造力具有顯著的負面作用。而當團隊領導的創造力角色認同較高時, 該負面作用不顯著。
Amabile, T. M., Schatzel, E. A., Moneta, G. B., & Kramer, S. J.(2004). Leader behaviors and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 Perceived leader support.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5
(1), 5–32.Ancona, D. G., & Caldwell, D. F. (1992). Bridging the boundary:External activity and performance in organizational tea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 634–665.Basadur, M. (2004). Leading others to think innovatively together: Creative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5
(1), 103–121.Bresman, H., & Zellmer-Bruhn, M. (2013). The structural context of team learn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d team structure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4
(4), 1120–1139.Brislin, R. W. (1970). Back-translation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
(3), 185–216.Brooke, J., Rasdi, R. M., & Samah, B. A. (2017). Modelling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ur using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or.
European Journal of Training & Development,41
(2), 144–159.Cai, Y. H., Jia, L. D., You, S. Y., Zhang, Y., & Chen, Y. L.(2013).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knowledge sharing and team creativity: A social network explan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45
(5), 585–598.[蔡亞華, 賈良定, 尤樹洋, 張祎, 陳艷露. (2013). 差異化變革型領導對知識分享與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社會網絡機制的解釋.
心理學報, 45
(5), 585–598.]Callero, P. L. (1985). Role-identity salien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8
(3), 203–215.Callero, P. L., Howard, J. A., & Piliavin, J. A. (1987). Helping behavior as role behavior: Disclos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nalysis of prosocial 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0
(3), 247–256.Cheung, M. F. Y., & Wong, C. S. (2011).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der suppor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32
(7), 656–672.Chung, Y., & Jackson, S. E. (2013).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tworks of knowledge-intensive teams: The role of task routinen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9
(2), 442–468.Cohen, J., Cohen, P., West, S. G., & Aiken, L. S. (201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 UK: Routledge.Collins, C. J., & Smith, K. G. (2006). Knowledge exchange and combination: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nology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3), 544–560.Cross, R., & Cummings, J. N. (2004). Tie and network correlates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intensive 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6),928–937.Drazin, R., Glynn, M. A., & Kazanjian, R. K. (1999).Multilevel theorizing about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4
(2), 286–307.Edmondson, A. C., Dillon, J. R., & Roloff, K. S. (2007). Three perspectives on team lear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
(1), 269–314.Faraj, S., & Yan, A. M. (2009). Boundary work in knowledge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
(3), 604–617.Farmer, S. M., Tierney, P., & Kung-McIntyre, K. (2003).Employee creativity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role identity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6
(5),618–630.Ford, C. M. (1996). A theory of individual creative action in multiple social domai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1
(4), 1112–1142.Glover, J. A., & Sautter, F. (1977). Relation of four components of creativity to risk-taking preferenc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1
(1), 227–230.Gong, Y. P., Kim, T. Y., Lee, D. R., & Zhu, J. (2013). A multilevel model of team goal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6
(3), 827–851.Grand, J. A., Braun, M. T., Kuljanin, G., Kozlowski, S. W. J.,& Chao, G. T. (2016). The dynamics of team cognition: A process-oriented theory of knowledge emergence in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
(10), 1353–1385.Grube, J. A., & Piliavin, J. A. (2000). Role identity,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s, and volunteer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
(9), 1108–1119.Hirst, G., van Knippenberg, D., & Zhou, J. (2009). A crosslevel perspective on employee creativity: Goal orientation,team learning behavior,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2), 280–293.Janis, I. L., & Mann, L. (1977).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Jaussi, K. S., & Dionne, S. D. (2003). Leading for creativity:The role of unconventional leader behavior.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4
(4–5), 475–498.Jung, D. I., Chow, C., & Wu, A. (2003). The rol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ypotheses and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4
(4–5), 525–544.Kelley, H. H. (1952). Two functions of reference groups. In G.Swanson, T. Newcomb, & E. Hartley (Eds.),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pp. 410–414). New York: Holt.Koopmann, J., Lanaj, K., Wang, M., Zhou, L., & Shi, J. Q.(2016). Nonlinear effects of team tenure on team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and climate strength: Implications for average team membe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
(7), 940–957.Koriat, N., & Gelbard, R. (2014).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among it personnel: Integrated model and implications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4
(5), 577–591.Luo, J. L., Men, C. H., & Zhong, J. (2014). The effect of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eam creativity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35
(5), 172–180.[羅瑾璉, 門成昊, 鐘競. (2014). 動態環境下領導行為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研究.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35
(5),172–180.]Malhotra, A., & Majchrzak, A. (2004). Enabling knowledge creation in far-flung teams: Best practices for IT support and knowledge sharing.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8
(4), 75–88.Marrone, J. A., Quigley, N., Prussia, G. E., & Dienhart, J. W.(2016). Can I and do I want to?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rivers of employee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16
, 17851.
Marrone, J. A., Tesluk, P. E., & Carson, J. B. (2007).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eam member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6), 1423–1439.Merton, R. K. (1957).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 K. Merton (Ed.),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281–386). Glencoe, IL:Free Press.Mumford, M. D., Scott, G. M., Gaddis, B., & Strange, J. M.(2002). Leading creative people: Orchestrating expertise and relationship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3
(6), 705–750.Paulus, P. B., & Yang, H. C. (2000). Idea generation in groups:A basis for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2
(1), 76–87.Ramarajan, L., Bezrukova, K., Jehn, K. A., & Euwema, M.(2011). From the outside in: Th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boundary spanners' relations with member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2
(6),886–905.Shin, S. J., & Zhou, J. (2007). When is educational specialization heterogeneity related to creativit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s a moderat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6), 1709–1721.Somech, A., & Drach-Zahavy, A. (2013). Translating team creativity to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The role of team composition and climate for innov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39
(3), 684–708.Sung, S. Y., & Choi, J. N. (2012). Effects of team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the creativ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al tea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8
(1), 4–13.Teigland, R., & Wasko, M. M. (2003). Integrating knowledge through information trading: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ndary spanning communication and individual performance.
Decision Sciences, 34
(2), 261–286.Tierney, P., & Farmer, S. M. (2002). Creative self-efficacy: Its 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relationship to creative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6), 1137–1148.Tierney, P., & Farmer, S. M. (2004). The Pygmalion proces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30
(3),413–432.Tierney, P., & Farmer, S. M. (2011). Creative self-efficacy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over tim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
(2), 277–293.Tushman, M. L. (1977). Special boundary role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2
(4), 587–605.Weisz, N., Vassolo, R. S., & Cooper, A. C. (2004).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social capital of nascent entrepreneurial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04
, K1–K6.Yang, J. Z., Chen, Y. X., & Ma, H. Q. (2012).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A role 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9
(9), 129–134.[楊晶照, 陳勇星, 馬洪旗. (2012). 組織結構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 基于角色認同理論的視角.
科技進步與對策,29
(9), 129–134.]Zhang, A. Y., Tsui, A. S., & Wang, D. X. (2011).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group creativity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The role of group processe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2
(5), 851–862.Zhao, Z. J., & Anand, J. (2013). Beyond boundary spanners:The ‘collective bridge’ as an efficient interunit structure for transferring collective knowledg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4
(13), 1513–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