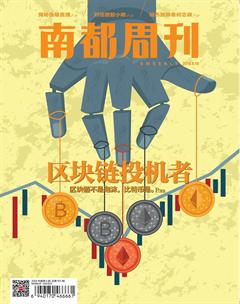戛納電影節(jié)的“亞洲時刻”
Lorenzo
第七十一屆戛納電影節(jié)落下帷幕,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獲得金棕櫚大獎。本屆戛納電影節(jié)被《銀幕》等雜志稱之為異彩紛呈的“大年”,意指佳作頻頻,閃光點繁多。本屆電影節(jié)除了公認的質量高,還有非常多高光的“亞洲時刻”。
七部亞洲電影齊聚主競賽
在本屆戛納電影節(jié)前夕,戛納電影節(jié)總監(jiān)福茂就許諾本屆電影節(jié)的選片將顛覆過去,有著改革的意義。最終我們看到今年的戛納電影節(jié)的21部主競賽作品里,有7部來自于亞洲。如果算上合拍片《小家伙》(制片國家俄羅斯/德國/波蘭/哈薩克斯坦/中國,導演謝爾蓋·德瓦茨沃伊出生于蘇聯,現哈薩克斯坦)則有8部,亞洲陣容空前強大,這是戛納電影節(jié)新千年以來最多亞洲電影入選主競賽的紀錄。反觀2017年,僅有3部亞洲電影入選,2016年則只有2部,2018可謂亞洲電影的“超級大年”。
今年入選主競賽的7部亞洲電影分別是:
中國:賈樟柯《江湖兒女》
日本: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日本:濱口龍介《夜以繼日》
伊朗:阿斯哈·法哈蒂《人盡皆知》
伊朗:賈法·帕納西《三張面孔》
韓國:李滄東《燃燒》
黎巴嫩:娜丁·拉巴基《迦百農》
7部來自7名亞洲導演的作品,其中東亞電影占到4部,中日韓皆有,而中東作品3部。作品地域分布均勻,且大師云集,可以說匯聚了亞洲電影的最高水平。其中中國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和日本家庭片大師是枝裕和都是第五次入圍戛納主競賽 ;韓國導演李滄東的上一部作品《詩》斬獲了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編劇獎;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憑借《一次別離》和《推銷員》已兩次摘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賈法·帕納西僅缺一枚金棕櫚就能完成三大電影節(jié)大滿貫;黎巴嫩女導演娜丁·拉巴基曾憑借作品《吾等何處去》獲得第64屆戛納電影節(jié)一種關注大獎提名。
最終《小偷家族》斬獲本屆戛納的金棕櫚大獎,而《迦百農》則斬獲了評審團獎,宣傳過《北京遇上西雅圖2》和《鯊灘》的路畫影視(Road Pictures)已經買下了這兩部電影的中國版權,國內觀眾不日可在影院欣賞到這部電影。
《小偷家族》的獲獎不僅改寫了日本電影21年無緣金棕櫚的歷史,更是打破了新千年來僅一部亞洲電影獲得金棕櫚的局面。在這部作品中,是枝裕和不僅探討了他擅長的家庭題材,而且引入了社會的干預與評價,讓作品顯得更有社會意義和深度。
不得不提的還有韓國導演李滄東的作品《燃燒》,雖說電影最終只拿到了費比西影評人獎這個小獎,但卻獲得場刊史上最高分3.8(滿分為4)。國外權威媒體紛紛獻上四星以上的高分,甚至有媒體直接說,“如果這部電影不拿大獎,那么評委們都瞎了”。
《燃燒》根據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和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燒馬棚》改編而來。電影講述的是送貨員鐘秀(劉亞仁 飾)偶然與童年好友惠美相遇(全鐘淑 飾),在前往非洲旅行之前,她請求鐘秀照顧她的貓咪。旅行回來后,惠美向他介紹了本(史蒂文·元飾),一個她在旅途上認識的神秘富二代,一場三角戀由此開始。
李滄東作為一名作家導演,作品一直擁有極強的文學性,前作《密陽》和《詩》都是如此,特別是《詩》,一舉拿下第63屆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編劇獎,這充分肯定了李滄東的創(chuàng)作才能。在《燃燒》里,李滄東改編了村上春樹和福克納的作品,并且融入了自己的解讀,《燃燒》從根本意義上來說變成了一部擁有希區(qū)柯克風格的懸疑電影。《燃燒》有望引入內地,在影院與影迷見面。
華語電影表現可圈可點
據美國電影協會統計,中國2017年票房總額高達79億美元,北美地區(qū)則為111億美元,統計專家預計,中國很快將超越美國票房成為世界第一大票房貢獻國。戛納電影節(jié)作為歐洲最大的電影市場自然要應對這個大潮流,今年的戛納電影節(jié)上,華語電影表現不俗,在各個單元都有展映:
主競賽單元:賈樟柯《江湖兒女》
一種關注單元:畢贛《地球最后的夜晚》
特別展映單元:王兵《死靈魂》
導演雙周單元:章明《冥王星時刻》
短片競賽單元:魏書鈞《延邊少年》
雖然最終華語電影并未斬獲任何戛納重要獎項,唯一的收獲是魏書鈞執(zhí)導的中國短片《延邊少年》獲得短片單元“二等獎”——特別提及榮譽獎,但是華語電影在本屆戛納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
賈樟柯的《江湖兒女》獲得了媒體場刊2.9分的高分(3分以上即是杰作),電影女主角趙濤一直是呼聲極高的影后競爭者。在這部《江湖兒女》里,賈樟柯串聯起自己過往的作品,完成了自己宇宙觀的塑造,且把“江湖”二字普及給國外媒體。電影拍攝從山西到三峽再到新疆,從21世紀初到2018,鋪陳了一個縱橫經緯的中國發(fā)展史,或許是賈樟柯最具野心和觀賞性的一部作品。
而在一種關注單元、導演畢贛的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獲得記者們的一致好評。電影講述的是黃覺飾演的男主角羅纮武回到貴州,偶然發(fā)現湯唯飾演的“神秘女子”蹤跡,繼而回想起十二年前與她度過的那個秘密夏天。畢贛將故事設定在了他的家鄉(xiāng)貴州凱里,攝影色彩飽和,構圖和場景好似王家衛(wèi),街巷里燈紅酒綠的廣告牌匾,綠野中云霧繚繞的重巒疊翠,一幅幅畫面如同海報,每一張都色彩斑斕美不勝收。
首映當日進場前記者們被人手發(fā)放了一副3D眼鏡,開場字幕則告知“本片非3D電影,請觀眾在觀影時自尋正確時機佩戴”。而當電影中男主角開始做夢戴上了3D眼鏡,記者們也才意識到手里3D眼鏡的作用,一個小時的長鏡頭炫技到了極致,也使畢贛成了當日戛納電影節(jié)的熱搜關鍵詞。《地球最后的夜晚》雖沒有拿到任何獎,卻為畢贛鋪好了一條再戰(zhàn)戛納的大道。
除了場刊銀幕的打分表,《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戛納官方觀眾打分表排名所有影片第9,在“一種關注”單元排名第1,而王兵導演的長達8小時15分的紀錄片《死靈魂》則技壓群雄,冠絕觀眾打分總榜,這也是華語電影的高光時刻。但由于《死靈魂》在特別展映單元不參與競賽,最終也無法收獲獎項,然而這部作品卻意義非凡,記錄了中國勞改營幸存者的苦難記憶,被譽為“時代的挽歌”。
第71屆戛納電影節(jié)頻出的“亞洲時刻”肯定了亞洲電影的卓越貢獻,也印證了福茂所說戛納電影節(jié)正處于一個大興變革的時期。越來越多年輕導演,以及亞洲導演獲得戛納電影節(jié)的肯定。這意味著亞洲電影勢必迎來更加輝煌的時代,在接下來的影節(jié)中引領風潮,也將攪動市場的一江春水,最終惠及熱愛電影的普羅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