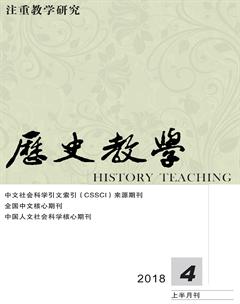用唯物史觀解讀先秦時期國家的發(fā)展變化
關鍵詞 唯物史觀,歷史合力,早期國家形態(tài)
中圖分類號 G6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0457-6241(2018)07-0033-0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指出:“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于新形成的社會各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取而代之,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jīng)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qū)團體了。”①也就是說,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但它不是對氏族組織的簡單繼承,而與氏族組織有著根本的區(qū)別。關于國家組織的特征,恩格斯進行了三個層次的區(qū)分與定位:一是國家按地域劃分它的國民,按居住地來組織國民,氏族組織則是以血緣關系組成居民組織;二是公共權力是國家產(chǎn)生的另一個標志,國家以公共權力強制被統(tǒng)治階級服從,即以武裝的人及其物質的附屬物,如監(jiān)獄和各種設施為后盾,這是氏族社會所沒有的;三是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甚至發(fā)行公債。恩格斯的這些論斷,是我們理解從夏商王朝到周王朝、從周王朝到秦帝國,這一早期國家形態(tài)演進的理論原點。但是,按照這一認知,筆者解釋中國早期的國家形態(tài),尤其是西周“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這一特性時,難免會有一種困惑:怎么解釋夏商西周的國家形態(tài)呢?如何理解東周列國到秦統(tǒng)一的國家組織結構的變化呢?
結合恩格斯關于國家起源的論述,判定夏朝建立進入國家形態(tài)的突出標志是“家天下”。夏本來也是部落組織,禹傳位給兒子是以“家天下”的方式壟斷了公共權力。但是,夏朝的生產(chǎn)力還處于石器時代,商朝雖然進入青銅時代,生產(chǎn)工具仍然以石器、木器為主,考古很少發(fā)現(xiàn)青銅工具。考古資料顯示,在春秋早期鐵器還較少使用,中晚期逐漸增多,進入戰(zhàn)國后,尤其是戰(zhàn)國中期,鐵農(nóng)具的使用已經(jīng)較為普遍了。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chǎn)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chǎn)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chǎn)關系。這些生產(chǎn)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①恩格斯后來又進一步地闡發(fā)了馬克思的這段經(jīng)典論斷:“根據(jù)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②“我們視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jīng)濟關系……也決定著階級的劃分,決定著統(tǒng)治和從屬的關系,決定著國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經(jīng)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fā)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的殘余,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huán)境。”③
結合馬恩的上述觀點及恩格斯關于國家起源的論述,夏、商、西周雖然產(chǎn)生了公共權力,但是三代的生產(chǎn)力水平還不足以徹底瓦解血緣部族組織。商和西周國家形態(tài)的發(fā)展表現(xiàn)為以“家天下”為特征的中央權力不斷強化,這是社會存在強化了社會意識,一個強大部族統(tǒng)治了周邊弱小的部族,部族中的貴族沿襲先前的傳統(tǒng),世代居統(tǒng)治地位,決定了階級的劃分。中國早期國家即使到西周仍然沒有按照地域建立地方組織,血緣家族仍舊是國家的基礎。西周分封制規(guī)定,各地諸侯要按時向周天子進貢,這可以視為早期國家收取的“捐稅”。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突飛猛進,在生產(chǎn)關系層面沖擊和突破了原來的社會組織和經(jīng)濟制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大幅提升,私田、荒地不斷開墾,導致井田制度發(fā)生危機。井田制下的公田荒蕪,統(tǒng)治者想出賦稅征收的新辦法,新辦法的推行,又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也促使社會組織、尤其是農(nóng)村里的基層組織“村社”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了大批的自耕小農(nóng)與地主。同時,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也帶來了手工業(yè)、商業(yè)的活躍。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一種追逐利益、實力競爭的局面。原先以部族組織為基礎的國家軍隊,還不是以募兵制建立的常備軍。在爭霸戰(zhàn)爭與兼并戰(zhàn)爭中,不僅加速了舊貴族階級的淘汰和新職官階層的崛起,而且瓦解了部族組織。各國出于富國強兵的動機,發(fā)展職官制度;實行征兵制,推行軍功獎勵制度,這是推動新舊制度更替最重要的兩個輪子。國家制度的更新通過一系列變法逐步成為現(xiàn)實。比如商鞅變法中最值得注意的三項:其一,新的職官實行任命制和俸祿制,既擺脫了血緣宗法制的直接干預,也掐斷了與地方政治經(jīng)濟的直接相關性,成為中央權力系統(tǒng)的工具。與此同時,對世卿世祿制也實行以“軍功”論取舍,作為一種過渡,直到最后自行消亡。其二,實行郡縣制,國家以地域組織取代原來的血緣部族組織,完善了國家形態(tài)。其三,固定國家征稅標準,向全民征糧、征稅、征發(fā)徭役。恩格斯所論的國家三個特征到戰(zhàn)國時期完全對應成為事實,即中國早期國家向成熟國家的過度,在戰(zhàn)國時期才完全實現(xiàn)。
用唯物史觀解釋三代到春秋戰(zhàn)國的變化,生產(chǎn)力水平是根本因素。在相對落后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水平上,夏、商兩代都沒能打破血緣部族組織。西周分封的諸侯國改變了部族的上層。但是血緣組織的特征仍然存留下來。直到鐵制農(nóng)具與犁耕技術的出現(xiàn),才打亂了原先的國際格局、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以宗法血緣關系構筑起來的社會等級秩序遂難以維系,社會失衡與關系失序也就成為了應然。思想意識的巨變隨之而來,諸子百家為重建社會秩序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救世方案。落后的生產(chǎn)力水平,舊的經(jīng)濟關系決定了早期國家形態(tài)的特征。國家形態(tài)走向成熟也必然有其經(jīng)濟基礎。
恩格斯說:“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fā)展是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并對經(jīng)濟基礎發(fā)生影響。并不是只有經(jīng)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①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雖然永遠存在于一切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中,但他們的性質和作用在各個時代卻各不相同。二者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體現(xiàn)特定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各自呈現(xiàn)特殊的歷史色彩,形成具有不同歷史內(nèi)容的對立統(tǒng)一體,并且隨著彼此間矛盾的推移而發(fā)生不同的轉變。西周推行宗法分封時,生產(chǎn)力水平并沒有多大的發(fā)展,周王實際上是以國家力量強行將親戚功臣分封到各地建立新的諸侯國,而諸侯國還是以血緣宗法為紐帶,這對歷史發(fā)展是消極還是積極的呢?應該說積極作用更大一些。因為新建立的諸侯國不僅加強了與中央政府的關系,還統(tǒng)領了所在地域的較小部族,相對商朝來說是進了一步。這一變化不是經(jīng)濟狀況決定的。那么,進入東周時期周王“共主”地位的喪失、地方分權體制逐漸解體,這個變化一定全部歸因于社會經(jīng)濟變革嗎?用單一的經(jīng)濟因素來分析難免牽強,以上問題是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其中重要關節(jié)是列國的區(qū)域開發(fā)和地緣政治的拓展。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中華文明的起源決非純粹是由中原向四周輻射的結果,相反四周也不斷地為中原的發(fā)展提供活力。兩者反復互動,取長補短。西周“封建”各諸侯國,它們實際是包含著宗族血緣與區(qū)域地緣二元因素的混合體。各諸侯國之內(nèi),都有不同部族的土著方邦居住,三晉地區(qū)則是長期與狄戎諸族交錯雜處。西周以親緣化解與融合地緣的政策非常成功。在每個以大國為中心的區(qū)域內(nèi),接觸-沖突-交流-適應-整合的過程走了一圈又一圈,到戰(zhàn)國時期,以大國為核心,若干區(qū)域地緣政治的特色已十分明顯。此外,長期的兼并戰(zhàn)爭與各諸侯邦國內(nèi)部的各種權力斗爭,都起著助燃爆破的作用。
其實,西周建立初,邦國之內(nèi)、邦國之間都存在不少的空隙地帶。由國君直接管轄的郡縣,其中不少便首先是在邦國空隙地帶或邦國與邦國交界的空隙地帶設置的。這就是區(qū)域人口與地緣經(jīng)濟發(fā)展的標志。郡縣與原來的封邑不同,官員都是由國君直接任命而非世襲。尤其到了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逐漸抽去了世襲貴族一層,剩下的只是君主與被統(tǒng)治者兩橛,沒有中間許多階層的逐級分權”。②“大一統(tǒng)”就是地方行政系統(tǒng)制度創(chuàng)新的推廣和全面實施。秦的大一統(tǒng)建筑在諸國各自區(qū)域統(tǒng)一的基礎之上,這沒有疑問。③
對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轉型”進行歷史解釋,即是分析從封邦建國體制走向中央集權體制這一歷史轉變過程,如果僅是從經(jīng)濟層面尋找原因,即是單一的經(jīng)濟決定論,難以令人信服。而實際上鐵制農(nóng)具與牛耕技術普及都比較晚。同樣,單純用經(jīng)濟因素來分析秦為何統(tǒng)一也牽強。由經(jīng)濟領域的變化帶來的各階層人的身份、地位的變化,貧富分化的加劇,社會角逐的激烈等,反過來成為了一種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百家爭鳴也為新時代的轉型提供了思想資源。進一步概括而言,西周時期已經(jīng)具備國家機器與機構,但是這一時期是將地緣關系與血緣關系加以糅合的國家形態(tài)。基于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的辯證運動,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動蕩時期,如各國的變法改革愈來愈多地打破了血緣關系,而縣制的建立愈來愈強化了地緣的關系與黏合。
恩格斯對于國家起源的論斷是基于“家庭”這一血緣概念在“私有制”這一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過程逐漸被打破,由國家這一地緣因素與特性彰顯的形態(tài)所取代的過程。因此,在運用唯物史觀解釋這一時段國家形態(tài)變化的時候,恩格斯的論斷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從國家產(chǎn)生這一問題本身看,則需要重新梳理。我們不僅要關注家庭與私有制對國家起源的論述,還要關注馬恩在其他論著中的一些相關論述。不然會陷入理論與現(xiàn)象的悖論中。這也警示我們對于唯物史觀要有全面、靈活的理解。
同理,對秦國何以能完成統(tǒng)一等問題的追索,也要關切統(tǒng)一性與矛盾性。歷史發(fā)展的解釋需要更多的是合力論,并不是唯生產(chǎn)力而論。即便是同一生產(chǎn)力,也可以適應不同的上層建筑,而同一生產(chǎn)關系可以容納多層次的生產(chǎn)力。15至16世紀英法確立的君主專制政體也允許甚至鼓勵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以工業(yè)化為根本推動所引發(fā)的現(xiàn)代化運動、現(xiàn)代社會具有的多樣化特性,以及當下中國改革開放的發(fā)展,也顯示了同一社會政治制度下,不同生產(chǎn)力完全可以相存并舉。
運用唯物史觀觀察和分析歷史問題,是中學歷史課程的核心能力。馬恩對人類社會生產(chǎn)是如何產(chǎn)生其他種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矛盾的經(jīng)典論斷,構成了當下進行歷史教學的基本認知路徑與原理。歷史發(fā)展與變化是異常豐富和波云詭譎的,歷史過程的矛盾性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唯物史觀作為我們研究歷史的行動指南,更多地指向為具有統(tǒng)攝性的思想與方法,不可以用作公式來套用與剪裁歷史事實。教師既要準確地把握唯物史觀,用以觀察歷史發(fā)展的各種關系和基本矛盾,又要充分意識到歷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歷史教學不要求教師講授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理論,而是要求教師將歷史唯物主義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之中,落實到歷史解釋。歷史解釋也不是理論化的說明,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史實基礎之上。有史實根據(jù)的解釋才能被學生接受。教條化的解釋只能培養(yǎng)僵化的思維。馬克思主義以實事求是為基本原則,唯物史觀的合理性也在于實事求是。在歷史教學中,運用唯物史觀千萬不能忘記實事求是。
【作者簡介】張子輝,中學高級教師,上海市松江區(qū)立達中學歷史教師。
【責任編輯:王雅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