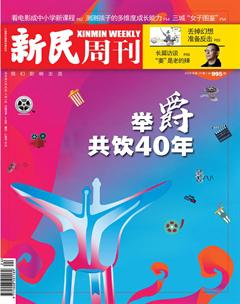殺死一只百足之蟲后
杜雅萍
武昌革命新軍幾位基層小兵倉皇中的幾槍,像大清王朝慌亂無章的喪禮上無序的炮仗,響徹長空的槍炮,嚇跑了沒膽作祟的僵尸,皇帝遜位、共和締造,大清這只已死的百足之蟲終于涼透了。
歷史書喜歡貼標簽,為歷史人物地貼上標簽,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分析法實在是誤人子弟。與現實里復雜多變的人一樣,生活在異時空的人絕非單面人。梅毅先生在《辛亥革命:啟蒙、光榮與夢想的革命》一書中,將辛亥年間參與大歷史變革的人物小心地放入當時歷史語境中,他發現,在中國社會新陳代謝變化節點上,很少有人能超越自己的出身和階級。
在辛亥革命中,走在前臺的是軍人,北洋系黎元洪、袁世凱成為共和的實際締造者。相比美國國父華盛頓和富蘭克林、日本維新三杰,民國總統是老于世故的官場權謀者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是權術士而非改革者。領袖底色遜色太多,這也是百年中國泥足深陷的深層原因之一。
甲午戰敗、庚子亂局,清廷政局已經搖搖欲墜,抱殘守缺是死,除舊布新也是死,武昌起義的主力新軍,是政府正規軍。辛亥槍響,清廷愁云慘淡,慌了手腳。慈禧死后,上層親貴政權連統御全局的長袖善舞的權謀者都找不到了。這給野心者以機會。袁世凱出山,“武昌之亂,不必長毛。攝政王乃一高墻內養成的王爺,未經世事;瑞澂、張彪二人,皆平庸之輩,安能鎮亂!”
事實上開明、能干的八旗權貴也有,但因身份和其他原因,被排擠出決策圈。比如死在辛亥前夕的端方,“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許多的第一:曾創辦湖北第一座圖書館,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幼兒園,創建江蘇第一座無線電通信臺,首先引用西方放映機,最早派女子公費出洋留學,主持了江蘇第一次民意選舉代表,創辦了南京最早的官辦外語學校,他還是第一個從伯希和手中搜購敦煌文書的清廷學者官吏。”
他的政見與實際政務,與立憲派和革命派并無本質差別。如果他在革命后成為地方官,大概會得到模范總督之類的名聲。這樣的能臣被上層親貴排擠,又因身份原因無法與社會底層的革命派愉快玩耍。兩頭不靠的結果是成為革命的祭品,端方死時,身無余財,行李里只有一套《紅樓夢》。
雖然強權是政治穩定最省事的手段,卻不是最佳手段。政治倫理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如果違背大勢,倒行逆施,就會斷送半世聲名。比如袁世凱親手結束千年帝制。本來是功在千秋的豪杰之名,卻因為自己要做皇帝落得聲名掃地。因為洪憲丑聞,袁世凱被打入歷史黑名單,變成“壞人”后,后人自然會戴上有色眼鏡看他。
不論道德只就政治能力而論,袁世凱、黎元洪等清廷官場混出來的老油條的手段與手腕完爆革命黨人愣頭青們。袁世凱的北洋系經過十幾年經營,相對團結務實。而革命黨則派系林立,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與意氣之爭從未停歇,革命黨內部同樣非常微妙。
武昌首義三位低級軍士,完全是被推到歷史風口浪尖的時勢造出的英雄,他們自身缺乏在復雜的環境里保全自身的智慧。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這場革命的縮影。“中國人長久以來,一直地域觀念嚴重,各私其地,各私其人。即使是當時獨立的各省,皆有明顯的割據傾向。”
我們的歷史書好言大義,極少從現實政治實務操作角度切入分析歷史人物。梅毅君的這本書則從歷史的細節入手,巧妙地回避了觀念之爭,而是從操作層面分析人物的能力值,尤其是政治人物,從智商、情商、胸襟、氣量、眼光等角度來分析人物,就特別顯得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