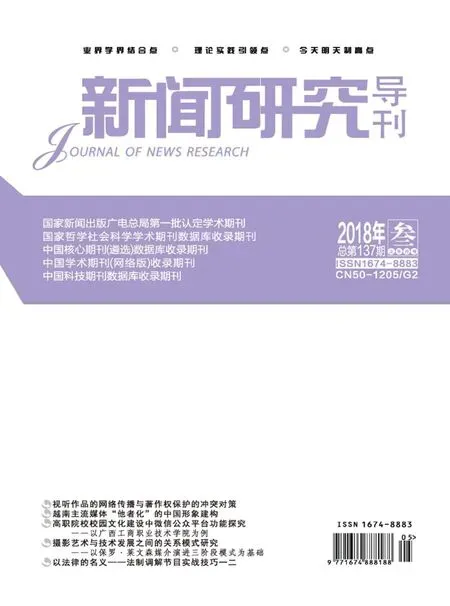淺議民俗儀式在農村文化認同建構中的作用
——以河南省焦作市蘇家作村“龍鳳燈舞”為例
宋晨綺 羅 彬
(新疆財經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一、蘇家作村民俗儀式概述與發展
(一)蘇家作村“龍鳳燈舞”概述
河南省焦作市城鄉一體化示范區蘇家作村,是當地有名的人口較多、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村。除經濟發展在當地農村領先外,該村還注重發展文化。2003年,蘇家作村被河南省文化廳命名為“河南省民間藝術之鄉”。“龍鳳燈舞”是該村一直以來重視傳承的一項民俗儀式活動,創于1812年,距今已有200年歷史。“龍鳳燈舞”在表演前會進行火神廟祭祀活動,表演后舉辦廟會,“龍鳳燈舞”是這項民俗儀式的核心。該表演特色是在“龍燈”的基礎上加了“鳳燈”,是該民俗儀式的首創。2008年,“龍鳳燈舞”被確定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龍鳳燈舞”文化向心力形成淵源
蘇家作村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原屬于河南省博愛縣,后劃分為新區。博愛縣因為處于河南山西交界處,形成了不同于河南話的獨特方言。并且,該村人口主要由“毋”“宋”“杜”“王”幾大姓構成,且各個姓氏宗譜完善,祠堂修建設施齊全,每年都有祭祀活動與輪班當值活動。蘇家作村的家族觀念較強,根據宗譜名字第二個字排行,可以清楚互相之間的輩分,人們的行為規范也與家族相關。“龍鳳燈舞”將主要姓氏大家族聯系起來,因此文化向心力氛圍濃厚。
清朝年間,蘇家作村在每年春節及農歷二月十九祭祀火神時,制作含有吉祥如意象征元素的燈籠,如龍、鳳、獅子、麒麟等,懸掛在自家門口。慶祝節日或祈求來年豐收,并進行一些大型燈籠表演,龍燈舞和鳳燈舞就是其中的代表。“龍鳳燈舞”始于清朝,據當地村民口頭流傳,是道光年間民間藝人毋黑蛋創造的。“龍鳳燈舞”古時一直由村里的鄉紳大戶組織表演,并且互相較量以彰顯家族財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龍鳳燈舞”主要由農民傳承,因為物資缺乏,早期的“龍”“鳳”和其他花燈都是村民撿塑料瓶廢紙糊制而成。改革開放后,由于國家及當地政府對于文化的保護與重視,“龍鳳燈”逐漸加入了現代科技與審美元素。
(三)“龍鳳燈舞”民俗儀式(見表1)

表1 蘇家作“龍鳳燈舞”儀式一覽表
(四)蘇家作村“龍鳳”品牌與附加價值
圍繞“龍鳳燈舞”,蘇家作村樹立了良好的品牌意識,積極發展相關周邊產業文化,以最大化增加其附加價值。
第一,龍鳳廣場與龍王雕像。“龍鳳燈舞”被認定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后,蘇家作村取“龍”“鳳”二字作為自己的文化符號,修建了龍鳳廣場、龍鳳小區,創建了“蘇家作”酒品牌。龍鳳廣場由國家撥款、村里有威望的村民捐款以及全村集資建成。龍鳳廣場豎立著龍鳳燈創始人毋黑蛋的雕像,作為對這項民俗儀式的歷史紀念。2012年,中國農歷“龍”年春節,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板塊“尋找中國龍”報道了“龍鳳燈舞”的表演,當地村民以此為榮,并將龍作為“龍鳳燈舞”的圖騰崇拜,龍鳳廣場上也修建了龍王雕像。
第二,“火神廟”。農村聚落一直與信仰、宗族分不開,節日慶典也多與敬拜神靈主題相關。祭祀雖然是一種封建迷信行為,但是往往寄托了村民樸素的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希望;同時通過集體祭祀,強化了本村生活秩序和公眾道德規范。蘇家作村的村廟叫“火神廟”,“龍鳳燈舞”最初就是為了每年二月十九祭祀火神。龍鳳廣場建成后,蘇家作村重新修葺了火神廟,也為“龍鳳燈舞”的日常表演賦予了儀式感。
第三,民俗文化節。蘇家作村重視發展本村的旅游與文化項目,目前正在進行復原蘇家作村“古城墻”項目。蘇家作村村委會制定了“龍鳳燈發展五年規劃”,正在申報建設龍鳳燈文藝展覽館,利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將“龍鳳燈舞”的技巧,由靠口耳相傳、親手教授的傳統老辦法逐步過渡為現代傳播手段,以進一步實現“龍鳳燈舞”的傳承。2018年春節,蘇家作村舉辦了民俗文化節,吸引當地及周邊的民俗儀式及民俗活動來龍鳳廣場參加展演,豐富了焦作市的農民文化活動。
二、民俗儀式對于文化認同與價值的塑造
(一)個人價值與群體認同
個人價值在與他人交流、與集體交往中反饋到“本我”,而形成新的“自我”。群體中,群體認同與歸屬感十分重要。“龍鳳燈舞”的主要成員為農民,尤其是丈夫外出打工的留守婦女。在表演中,他們可以實現群體交流與自我價值的提升,因此,“龍鳳燈舞”的參與演員往往是不計報酬的,群體認同及自我價值的產生對他們更為重要。另外,核心“四條龍”的演員,根據每條龍不同又分為4個小組,構成一個小群體,而這4條龍分別代表蘇家作村主要的“四大街”,每條街的成員又主要居住在所代表的街,表演時會互相競賽,因此,每個組的小群體認同感也較強,強化了農村社區的向心力。
(二)儀式傳播中的文化增值
文化傳播使得人們在文化活動的參與以及發展中,重新構建對于文化的認知,因此而產生文化增值,放大文化的原有價值或者意義。在傳播中,文化增值可以帶來量的增值和質的增值。在農村民俗儀式的傳播,一方面從量的增放上,隨著傳播面的擴散,民俗儀式傳播帶來的文化內涵增加;另一方面可能會帶來質的裂變,民俗文化與當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合,產生新的農村文化。在文化的傳播過程中,村民也在不斷完善這種儀式,并且賦予其新的內涵。龍鳳燈中傳統對于封建神明的原始崇拜慢慢轉化為對于國家繁榮富強才可以國泰民安、人民和樂的美好寓意。
(三)民俗儀式與國家符號
民俗儀式是國家與社會連接的紐帶,民俗儀式常常使用國家符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改善農民精神風貌,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在新時期,民俗儀式得到了充分多元的發展機會,有豐富的文化表現形式,但并不意味著與國家的脫節。相反,民俗儀式的變遷往往符合國家共同體意識與主流價值觀。蘇家作村“龍鳳燈舞”的表演節目中,龍和鳳本身就代表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符號,《舞起龍鳳慶豐收》《百鳥朝鳳賀團圓》以及儀式所需要的團隊協作精神與“愛國”“和諧”“友愛”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符。民眾也可以通過民俗儀式活動,構成國家文化符號、參與國家活動的一部分。
三、民俗儀式傳承的現實啟示
(一)意見領袖在農村社區中的作用
這里的意見領袖指的是民間權威人物。對于農村建設來說,農村家族關系結構復雜,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過國家權力控制,更需要農村尤其是農村社區良好關系的維持。比如,“龍鳳燈舞”的組長多由村民較為信服的人擔任,這些人從一定意義上屬于承上啟下的意見領袖,既有一定的先進知識,又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而在民俗活動中又與村民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系,村民對其比較信服,有一些鄰里之間的瑣事煩惱也會找這些意見領袖解決。
(二)集體記憶的構建
集體記憶是一個群體共同傳承或者構建的事物。社會的集體記憶需要個人主動、積極地參加集體活動,在集體活動中交流。人們在活動中構建了社會活動,同時也使集體記憶得以更新和延續,同時,集體記憶可以強化個人記憶。經濟的發展以及“碎片化”時代的到來造成社會的割裂與分化,集體記憶構建尤為重要。對于農村社區建設來說,集體記憶的構建強化了居民的文化認同,蘇家作村村民不論是“龍鳳燈舞”的演員還是觀眾,都認為過年過節一定要看過或者參加過“龍鳳燈舞”表演才算過年。而對于這種民俗儀式的扶持和傳承,使得集體記憶可以延續。
(三)農民的心理歸屬感
隨著城市的發展,農民對于城市的向往,造成了“空心村”的出現。要解決“空心村”的問題,需要政策經濟、社會保障等多措并舉,同時,增強農民對于生活空間的心理歸屬感,也是其中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蘇家作村能夠成為當地有名的小康村,除積極建設社會基礎設施外,對于文化的重視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在我們的認知上,耍龍舞獅的演員多為男演員,但蘇家作村參與“龍鳳燈舞”的演員多為留守婦女。農忙結束后,丈夫外出打工,她們參與“龍鳳燈舞”的演出,一方面提升了女性對于自我價值的認知,另一方面減小了留守農民的心理落差,增強了他們的歸屬感,同時維護了農民的心理健康。
四、結語
蘇家作村火神廟祭祀及“龍鳳燈舞”的傳承,以及“龍鳳”品牌的延續,積極拓展更多文化變現的機會,對于當地經濟與旅游的發展,特別是對于農民文化認同的構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需要文化助力,因此要從民俗儀式的傳承對文化認同的建設中得到啟示。此外,民俗儀式的發展要注重政府的宏觀把控,尤其要注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確引導,才可以使民俗儀式走向正確的道路,為國家的文化發展添磚加瓦。
[1]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5-29.
[2]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5-88.
[3]鐘建華,王項飛.儀式:崇拜與有序的神圣編輯[D].中央民族大學,2008.
[4]陳力丹,王晶.節日儀式傳播:并非一個共享神話——基于廣西仫佬族依飯節的民族志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4):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