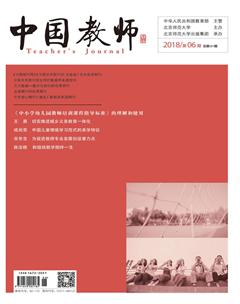鄉村教育的守望者
張倩
一、求學之路(1947—1958年)
我出生在一個中農家庭,家庭條件一般。我的爺爺在舊社會是私塾先生,差不多清末民初的時候,爺爺在隔壁下洼村教書,一次教三五個學生。那時候教書,基本上都是背《百家姓》《三字經》等內容,小孩兒背書跟唱戲一樣,搖頭晃腦的。爺爺雖然是私塾先生,但父親沒讀多少書,只有叔叔讀過幾年。
1.五年小學與三年初中
我家有兄弟姐妹五個,一個姐姐、三個弟弟和我,在男孩子中我是老大。那個時候不怎么重視教育,父母看我踏實又是個男孩子,在我8歲的時候就讓我跟著別人讀書。因為我的成績一直很好,都是前幾名,所以就一直讀下去了。
我在楊集鄉讀了五年小學,在官莊鄉讀了三年初中,小學一個班里差不多有60個人,初中一個班大概有50個人。小學時學習語文、數學、衛生常識、自然、歷史和地理,初中的時候學語文、幾何、代數、植物學,那時候植物學主要是學習莊稼的種植和培育,還有各種樹木的生長區域等。
2.半年的“短師”和兩年的帶薪學習
讀完初中之后,我報考了“短師”。為什么選擇當老師呢?一方面是家庭因素,因為家庭條件一般,我想盡快有一個差不多的工作能養活自己;另一方面就是我對教育比較感興趣,而且教師這個職業在農村還是很受人尊敬的。所以我放棄考高中,沒怎么猶豫就上了“短師”。我在縣里的泌陽師范學校上了半年的師資訓練班,俗稱“短師”。半年后畢業,學校分配了工作,我就回到了官莊鄉任教。
在讀“短師”的半年里,除了前兩個星期,我們一直有實習任務。剛開始是每周一起去城關小學聽兩節課,聽了大概三個月。后面三個月就是學校組織我們上講臺試講,到畢業,基本上每個人能夠上臺講兩次,每次講完之后會有老師指導,小組討論,指出各自的優缺點。
剛去官莊鄉,趕上縣里在全縣各學校選拔一部分人才帶薪學習,一個鄉有三四個名額,我也被選上了,就去縣里又學習了兩年。
二、下放前的教學和生活(1958—1962年)
1.教師的選拔和師資質量
我們這兒選教師,一是要看學業情況,二是要看家庭成分。學業上,那時候的教師大部分都是“短師”畢業的;成分上,當時的政治出身主要分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中農和貧農。因為我們家屬于中農,我從上學開始學業成績也一直很好,所以我是符合條件的。
2.學校的工作環境
1958年,我回到官莊鄉,開始正式任教。我教三年級,班里有57個學生,我既教語文又教數學。那個時候教學任務很重,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課、改作業,有時候半夜還在改。當時家離學校很遠,一個月也回不了一趟家。
3.當時的生活
1958年的時候,我們這兒的糧食大豐收,紅薯長得特別大。但當時在“大煉鋼鐵”,村里的年輕勞動力都被叫去煉鋼,糧食沒人往家里拉,只好在地里挖紅薯窖,把紅薯都埋到地里面,打算第二年吃。誰知道,第二年,紅薯都爛了。再后來,就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沒東西吃,只好把爛掉的紅薯煮一煮充饑。那幾年真的很難熬,通常我上完一、二節課,到三、四節就餓得不行了,那也沒辦法,還得上課、改作業。可能是那時候餓怕了,落下了病根兒,我現在也不能餓,稍微餓一點兒就頭暈眼花,得趕緊吃點兒東西才能緩過來。
4.教師待遇
剛工作的時候,我的工資是20塊5毛錢。當時實行票制,老師每月的限額是29斤面粉、一斤油。自然災害那幾年,學校食堂買了很多白菜說是要應急,后來也壞了。學校把這些花銷都分攤到老師身上,所以我們到手的工資是很少的。
三、下放時期的生活(1962—1964年)
1962年,國家進行學校合并,下放教師。下放之后,我們幾個老師就自己組織,在下洼村辦了耕讀小學,招附近幾個村的學生。因為沒有教室,所以我們就看誰家有閑置的房子,給人家說說好話,等人家同意了就在閑置的房子里教書。房子里沒有桌椅板凳,我們就自己壘泥巴臺當課桌,學生從家搬凳子。過了一段時間,人家要用房子,我們只能再找地方。那兩年,挪教室都挪了三四回,每挪一次都得重新壘桌子,那幾年真是沒少壘桌子、涂黑板。
四、郭莊小學的教學和生活(1964—1999年)
1964年重新走上崗位后一直到退休,我都在郭莊小學,所以我對這個學校印象最深,感情也最深。
1.學校生活與“轉正”之路
說起我的教學,我還是挺自豪的。我教的班級,在全鄉評比時基本上都是第一名,雖然郭莊小學只是個村小,但教學質量連當時鄉里的小學都沒法兒比。教了這么多年,我覺得,只要老師嘴勤、腿勤、手勤就能把學生教好。那時候老師的負擔其實也挺重,一周上六天課,只有周日一天休息。說是休息,實際上每周日都會開會,也不怎么能顧到家里,基本上每天都在學校。平常既有早自習又有晚自習,早自習是所有年級都上,晚自習是四五年級上。早自習是6:30—7:30,晚自習是19:00—20:00。學生也挺不容易的,那時候家里沒有表,都是憑感覺去學校,一般都去得很早,天還沒亮,小孩兒害怕,所以我們村的小孩兒都是一起去,邊走邊喊給自己壯膽。
那時候大家是集體勞動,年底按照工分分糧食。農民一般情況下一天是十個工分,干活多了會有十幾個工分,老師一天是七八個工分,所以農民每個月的工分比教師要高,最后分得的糧食也比老師多。那時候家里孩子都多,有的老師為了養活家里,教著教著就不教了,辭職去當農民。
1987年,我通過了“轉正”考試,成績是全鄉第一、全縣第三,終于又成了公辦教師。1989年,因為我表現一直很不錯,所以駐馬店地區教育局給我頒發了小學教師考核免試證,免于《教材教法合格證書》和《專業合格證書》考試。1997年,我被評為“小學高級教師”。
2.教師培訓進修及選拔評定
現在黨和政府對教育很重視,這一點我很欣慰,終于盼到了教育的春天。現在教師的培訓和進修很豐富,我們那時候教研組基本上沒起到什么作用,也沒有教師能被選拔出去參加培訓和學習的機會,鄉里和縣里的情況會好一些,偶爾有培訓和進修,我們村小基本都沒有,全靠教師自我學習,邊教邊學。
優秀教師的選拔和職稱評定,一般是一年評一次,參考教齡和教學成績,也要看平時工作狀態,在學校評選之后鄉里評選,然后再交給縣里教育局審批,一個鄉一年也就三五個名額。有一年,楊莊大隊、姚莊大隊還有我們郭莊大隊三個隊在郭莊小學評選,一共才評選2名。大家都覺得,評上的老師,說明教學有一定的成績,這也是領導和學生及家長肯定,需要繼續保持;沒評上的老師,說明表現不夠好,要再接再厲。職稱評定多少對教師還是起了一些鞭策激勵作用的。
3.師生關系與家校關系
在郭莊小學的時候,學費加上雜費可能也就每個人五毛錢,但那時候大家都窮,五毛錢的學費仍然有很多孩子交不上。一般來說,上學是能上幾年的,但男孩居多,女孩很少,而且上學晚,有的十一二歲了才來上一年級,讀了三四年就不讀了,或者讀到小學畢業,初中畢業的算不錯了,高中畢業的真不多。當時農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都不怎么重視教育,但是家長們都很尊敬老師,覺得我們有學問,懂得多,愿意聽我們的話。一般情況下,家長見到我們都會問:“俺家那孩兒擱①學校聽話不?不聽話就使勁揍他,俺不心疼。”家長們沒啥文化,說的話都很實在。那時候家長并不太關注學生的成績,主要關注的是孩子在學校有沒有按照老師的要求去做。在家長的眼里,我們老師就是權威。
就師生關系來說,我比較嚴厲,大部分學生都很怕我。在學校,學生覺得老師啥都懂,啥都知道,所以都會有點兒崇拜老師,有的學生聽老師的話多于聽父母的話。學生不聽話的時候,我就拿煙袋鍋敲他們腦門,邊敲邊說“栗子核桃棗,吃了再來討”。學生們挺怕我拿煙袋鍋敲他們,所以基本上還是聽我話的。
秉持“嚴師出高徒”的信念,老師多多少少都會體罰不聽話的學生。有一次,一個小男生在學校特別調皮搗蛋,我把他怪②哭了,他回家之后跟爸媽說了,他爸媽特別不高興,就找上門來質問我,不依不饒。最后,找人多次多方面溝通之后,家長才罷休。其實我們也都是為了學生好,想幫家長好好管管孩子。
4.教師地位和形象
在我的印象里,在農村,老師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老師也比較受人尊重,家長也都普遍信任老師。
但就當時的工資和購買力來說,教師的待遇真的不咋地③,只能說是勉強度日。那時候按教齡、按級別發工資,全縣統一標準。新參加工作的教師工資低,就兩百塊錢左右,我教齡長,還是高級教師,可退休時工資才四百塊錢左右。有一段時間,我們實行講課發補助,講一節課補貼八分錢,很多人爭著搶著講課。執行了一學期,上面發不起錢了,就停止執行了。
訪談后記
由于張伯和老師年歲已高,身體條件不太允許他一次說太多的話,所以訪談進行了兩次。第一次去的時候,張老師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電視機就放在他面前,離他很近。詢問了老師的身體并說明來意之后,張老師關掉電視欣然接受了訪談。雖然有些細節張老師已經記不太清了,但說起當年的事,他滿是感慨,感慨鄉村教師的不易、鄉村教育的艱難,更感慨如今教育發展的迅猛。訪談過程中,張伯和老師幾度情緒高漲,仿佛重新置身那時的環境,有點哽咽。第二次去訪談的時候,張老師身體抱恙,正躺在床上打點滴,但精神狀態還不錯。訪談最后,談起當今的教育,張老師滿是欣慰,對黨和政府如今對教育及教師的重視及措施贊不絕口,感慨自己終于等到鄉村教育有了新曙光和光明燦爛的未來。
訪談的整個過程中,我感觸最深的就是鄉村教育和鄉村教師的艱辛和不易,同時也被當時發生的故事深深地感動著。張老師數次提到,一個好的老師必須要有責任心,有責任心的老師才能教出有用的學生。他還說,盡管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白眼,但從不后悔自己當了一輩子鄉村教師,如果再有一次職業選擇,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當老師,因為他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人生價值,為鄉村教育和鄉村的孩子們帶去自己的光和熱,他無怨
無悔。
作為一個從鄉村教育中走出來的學生,我對鄉村教師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們也許不善表達,也許偶爾會體罰學生,甚至也許有些迂腐,但他們最接地氣,最實在,最淳樸,最為我們著想,最希望我們能從鄉村走出去,能建設國家,能反哺農村。
同時,我也對鄉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感觸頗深。由于歷史和地域的原因,中國的城鄉教育差距很大,中國農村教育的未來發展任重而道遠,希望越來越多的教育者能奉獻鄉村,傳承教師精神,讓一大批“張伯和”老師們鄉村教師的火炬代代傳遞下去。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讀者,希望鄉村教育的未來一片光明。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