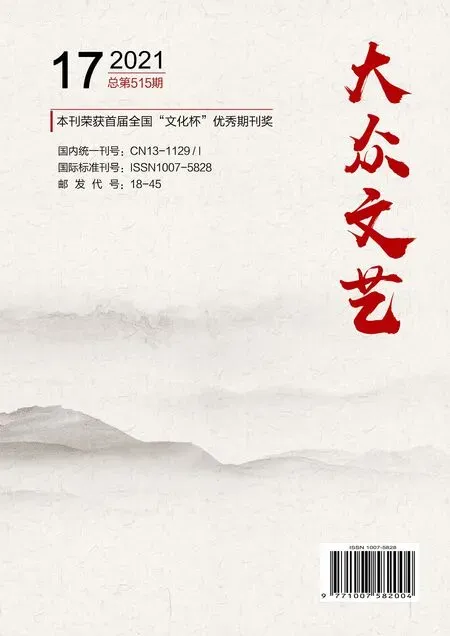空間與人性
——曹七巧人性之解讀
張愛(ài)玲以其特有的銳利目光探討人性,她的代表作《金鎖記》正是這樣一部經(jīng)典作品。主人公曹七巧的不幸來(lái)自一場(chǎng)不可選擇的失敗婚姻,自她嫁進(jìn)姜公館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一場(chǎng)人性異化的悲劇。本文擬從空間對(duì)人性影響的角度出發(fā),分析曹七巧人性異化的原因及其內(nèi)心深處對(duì)人性復(fù)歸的渴望從而探索作者對(duì)空間建構(gòu)的獨(dú)到匠心。
一、空間理論概述
本文探究的空間包括三部分:物理空間、社會(huì)空間與權(quán)力空間。物理空間作為經(jīng)驗(yàn)和感知的空間,是物質(zhì)維度的空間,偏重于客觀性和物質(zhì)性。
社會(huì)空間主要依據(jù)列斐伏爾在《空閑的生產(chǎn)》一書中的相關(guān)理論來(lái)闡述。在該書中,列斐伏爾認(rèn)為,空間不僅僅是一個(gè)物理概念更是一個(gè)社會(huì)概念,社會(huì)秩序的建構(gòu)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的重組形成了抽象的空間。空間的活動(dòng)主體——人,在與周遭社會(huì)的微妙反應(yīng)中不斷影響空間狀態(tài),但同時(shí)又被空間潛移默化的限制或改變,進(jìn)而影響整個(gè)社會(huì)形態(tài)的發(fā)展。這樣動(dòng)態(tài)循環(huán)的過(guò)程反映出社會(huì)與空間彼此成就又互相制約的關(guān)系。
米歇爾·福柯在《空間、知識(shí)和權(quán)力》中明確指出空間對(duì)于權(quán)力運(yùn)作的重要意義,這一命題是權(quán)力空間理論發(fā)展的奠基石。他縱觀人類發(fā)展的歷史,將橫軸上的權(quán)力史與縱軸上的空間史進(jìn)行結(jié)合,總結(jié)出空間之于個(gè)人所產(chǎn)生的生產(chǎn)作用,同時(shí)空間所帶有的權(quán)力暗示與統(tǒng)治話語(yǔ)能夠制約人的思想和行為。德·塞爾杜在《日常生活的實(shí)踐》中也涉及到權(quán)力空間的理論,他認(rèn)為空間差異的產(chǎn)生往往是權(quán)力運(yùn)行的結(jié)果。空間是掌權(quán)者的空間,他們管理和統(tǒng)治空間,而弱者在空間中處于被動(dòng)地位,難逃邊緣化的困境。
二、闖入姜公館——異化的誕生
姜公館作為一個(gè)住所首先具備著客觀的物理空間屬性,關(guān)于空間的大小文中這樣寫道:“那兩年正忙著換朝代,姜公館避兵到上海來(lái),屋子不夠住的,因此這一間下房里橫七豎八睡滿了底下人。”擁擠的內(nèi)部空間體現(xiàn)出一個(gè)沒(méi)落家族難以掩藏的局促,暗示這樣一個(gè)大廈將傾的封建家族在戰(zhàn)亂之中已失去曾經(jīng)的社會(huì)權(quán)力話語(yǔ)。但現(xiàn)實(shí)的慘淡尚不足以讓一群可憐人互相取暖,在這閉塞的空間中仍有高下之分,好壞之別,時(shí)代悲劇中的一群困獸彼此撕咬互不放過(guò),上演可笑的悲哀。姜公館狹小、擁擠的空間同時(shí)還意味著個(gè)人隱私的缺失,為八卦與茍且提供了土壤;關(guān)于空間的明暗,作者借曹七巧之口道:“怎怪我不遲到——摸著黑梳的頭!誰(shuí)教我的窗戶沖著后院子呢?”黑暗的空間增添了曹七巧內(nèi)心的不平,這些不平是矛盾的源頭,是異化的開端。更糟糕的是,沒(méi)有人在乎她在暗處的改變,不公的遭遇沒(méi)有換來(lái)任何的同情和幫助,尖銳、狹隘的言辭不過(guò)是高宅大院中最無(wú)意義的一句牢騷。她的掙扎顯得可笑而愚蠢,個(gè)人空間的一小片黑暗也很快被整體表象的光鮮遮掩:“姜家住的雖然是早期的最新式洋房,堆花紅磚大柱支著巍峨的拱門,樓上的陽(yáng)臺(tái)卻是木板鋪的地。”新舊雜糅的風(fēng)格、慵懶昏黃的基調(diào),符合故事開篇三十年前的時(shí)間設(shè)定,帶著回憶的暖意和澀味。這樣和諧的氛圍、安逸的空間,仿佛不會(huì)發(fā)生不幸,亦或者發(fā)生怎樣的不幸都不聲不響,不痛不癢。可以說(shuō)姜公館是“鎖”住曹七巧的籠子,在這個(gè)看似不大的空間中,她摸不到出去的方向,甚至也不具備邁出門的勇氣,她總是倚在門邊,承受這種尷尬的定位。
姜公館住著一大家族,它承載著各種關(guān)系及人們的價(jià)值觀念、道德取向等非實(shí)體的東西,并不是純粹的物理空間,包含社會(huì)空間的屬性。在姜公館這個(gè)社會(huì)空間中,曹七巧是以一個(gè)“闖入者”的身份存在的,她本身的社會(huì)資源和生活方式?jīng)Q定了她不屬于這個(gè)空間。一個(gè)下人眼中低三下四的人,嫁給得了軟骨病沒(méi)有實(shí)權(quán)的丈夫,如何能在這個(gè)勢(shì)利的大家族中活的有尊嚴(yán)。粗俗的談吐下人都瞧她不起,何況他人,她是姜公館最孤獨(dú)的人,被孤立、被嫌棄,沒(méi)有朋友更沒(méi)有援手,長(zhǎng)期在這樣的空間里她能夠想到自我保護(hù)的方法便是用尖銳的言辭中傷別人,在別人的痛苦中獲得短暫的勝利和存在感。
《金鎖記》中的姜公館保持著鮮明的家長(zhǎng)制特征,老太太是絕對(duì)的權(quán)威,從高到低,權(quán)力的分層清楚、明晰。曹七巧努力想要融進(jìn)這權(quán)力的的世界,苦于沒(méi)有尊貴的身份作為通關(guān)證。社會(huì)空間限制了她與下級(jí)和同級(jí)的對(duì)話,權(quán)力空間又限制了她與上級(jí)的對(duì)話,她是一個(gè)發(fā)不出聲的可憐人:“她在門檻上站住了,問(wèn)小雙道:‘回過(guò)老太太沒(méi)有?’小雙道:‘還沒(méi)呢。’七巧想了一想,畢竟不敢進(jìn)去告訴一聲,只得悄悄下樓去了。”兄嫂來(lái)訪竟喪失了自我的話語(yǔ)權(quán)與主體性,甚至連下人也默認(rèn)沒(méi)有對(duì)話的機(jī)會(huì)和必要,是怎樣的羞恥。這種羞恥源自一種不甘,曾經(jīng)在麻油店的美好過(guò)往給予的自信,讓她不能忍受遭遇如此不堪的生活,承受周遭的冷眼與嘲笑。她對(duì)于姜季澤的感情更多的是渴求一種平等的對(duì)待和認(rèn)同。“七巧待要出去,又把背心貼在門上,低聲道:‘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這是她對(duì)平等與尊嚴(yán)的最后一次掙扎,但結(jié)局依然凄愴,于是死了心,不再期待,看清了在這個(gè)環(huán)境中生存的砝碼,就是權(quán)力,就是金錢。將不甘壓抑在胸,積淀成對(duì)金錢、權(quán)力不盡的渴望,終于成為自己討厭的模樣。
這也正如德·塞爾杜所強(qiáng)調(diào)的,權(quán)力對(duì)人的空間地位會(huì)產(chǎn)生影響,權(quán)力的高低擴(kuò)大了空間的差別。弱者往往在物理空間上被主體區(qū)隔與劃分,進(jìn)而在社會(huì)空間中感到被壓迫、被排斥,而長(zhǎng)時(shí)間喪失話語(yǔ)權(quán)的抑郁與孤獨(dú)使得他們最終走向人性的異化和覆滅。作者通過(guò)對(duì)物理空間、社會(huì)空間以及權(quán)力空間的建構(gòu),間接闡釋了曹七巧必然走向人性異化的原因,體現(xiàn)出空間場(chǎng)所對(duì)人性的影響。
三、回憶麻油店——復(fù)歸的渴望
麻油店可以說(shuō)是曹七巧內(nèi)心的烏托邦,是她人性善的起點(diǎn),也是回憶自己悲哀一生,最后想要回歸的人性終點(diǎn)。
對(duì)麻油店的描寫在小說(shuō)中出現(xiàn)兩次,第一次是哥哥和嫂子來(lái)看曹七巧:“從前的事又回來(lái)了:臨著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膩的柜臺(tái),芝麻醬桶里豎著木匙子,油缸上吊著大大小小的鐵匙子。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里,一大匙再加上兩小匙正好裝滿一瓶——一斤半……”這段文字從顏色、陳設(shè)、動(dòng)作等細(xì)節(jié)描繪出回憶濾鏡下往日的美好,體現(xiàn)出曹七巧對(duì)過(guò)去的懷戀,對(duì)麻油店和那條街所構(gòu)建出的空間她是有著一定的依戀情愫的,因此這里的空間被賦予了濃重的主觀情感,對(duì)曹七巧而言是一個(gè)“地方”。正如周尚意在《人文主義地理學(xué)家眼中的“地方”》一文中總結(jié)段義孚先生的“地方”觀點(diǎn)時(shí),認(rèn)為“地方”就是一種主體感受。
這個(gè)“地方”是曹七巧所想回歸的心靈家園,在這個(gè)家園的構(gòu)建中,空間的布局簡(jiǎn)單而開闊,不像姜公館的擁擠和陰暗,那里明亮而自由。人與人的社會(huì)地位差不多,生活方式也相投,可以自在的開玩笑,簡(jiǎn)單、直接、真誠(chéng)、快活。更不會(huì)有權(quán)力的壓迫,各做各的生意,不必看誰(shuí)臉色。最重要的是可以平等的對(duì)話與溝通,擁有真正的愛(ài)情,不會(huì)有人為錢接近她,她也不必為錢疏遠(yuǎn)誰(shuí)。“喜歡她,也許只是喜歡跟她開開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們之中的一個(gè),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duì)她有點(diǎn)真心。”縱然沒(méi)有多愛(ài)也總歸是有盼頭,不似這凄愴一生,被金的枷鎖束縛,到頭來(lái)什么真心也沒(méi)有,白白歲月蹉跎。
“真心”是曹七巧生命最后的追求和遺憾,也是張愛(ài)玲對(duì)人性之真的探尋。這個(gè)“真”,曹七巧在第二次回憶中獲得了希望,回憶中的男子不只是第一次想到的朝祿,還有麻油店那整個(gè)空間中的其他男子。她對(duì)這一空間是絕對(duì)信任的,認(rèn)為隨便選擇哪一個(gè)男人都會(huì)擁有幸福的可能。在這個(gè)空間中曹七巧放下對(duì)別人,包括對(duì)自己的提防,正視內(nèi)心壓抑的對(duì)愛(ài)情的渴慕、對(duì)幸福的追求;作為一個(gè)女人容顏彈指老的遺憾;對(duì)傷害兒女人生的悔恨;不受掌控的命運(yùn)的無(wú)奈。
文章的最后,作者寫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méi)完——完不了。”曹七巧的人生是社會(huì)的悲劇也是人性的悲劇,這樣的故事也許完不了。但每一個(gè)“曹七巧”心里也許都有一個(gè)“麻油店”,在那里人能夠復(fù)歸到自然、本真狀態(tài),獲得精神上的釋然與平和,這大概也是作者所向往的人性的歸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