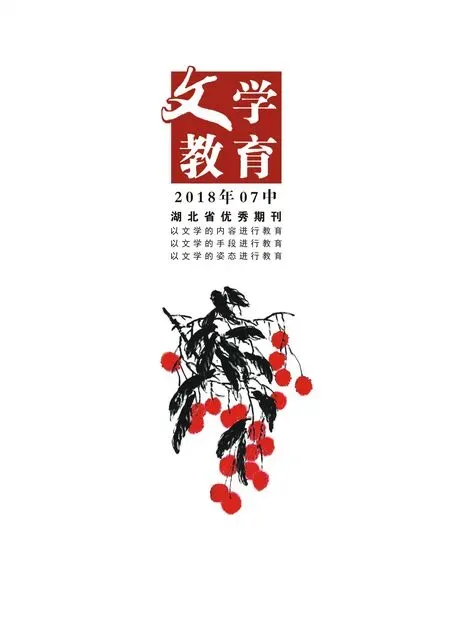讀何兆武《上學記》有感
韓 煜

“我們哀歌的,是從未擁有過的往昔”。讀完《上學記》,酣暢悅然之時,我突然想起這句話,用在這里真是再恰當不過。
聯大的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學習自由,行動自由。作者提到在西南聯大轉系很方便——學分念夠了就可以隨便轉,他本人就先后讀過四個系。雖然這與時處戰亂體制松散等多方面因素有關,可事實證明收效良好,那也不失為現今辦學的一種借鑒。現在大學中轉專業政策尚不完善,并且有些學校規定成績夠好才能轉。對比之下,是不是當下的某些制度過于持重了呢?畢竟大學生選擇專業也是一個難題。大學四年正是學生人格觀念建立形成的時期,在成長的道路上必然會迷茫和犯錯,大學在不觸及原則性質的問題上始終應當是寬容的,允許徘徊,允許試錯。也許一系列繁瑣規定也是從側面提醒學生要慎重選擇,但無論如何都應秉持這樣的原則——好的制度是靈活的,符合人性的。我曾聽過一個“悲慘”的故事,大致是一個學生考進了某重點大學的數學系,想轉專業卻始終不成——因為不喜歡也不擅長高等數學所以成績不好,而成績不好自然就沒辦法轉專業,就這樣頂著名校生的光環陷入了絕望的惡性循環。但愿這只是個例。
那是個政治混亂的年代,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立場,可以海闊天空的胡扯,也可以激烈的辯論,可政見不同并不影響大家的交往和感情。當時這一群在戰火紛飛中讀書的青年聚在一起談論國事,不為別的,只因他們胸中有一腔翻騰的熱血和一股子朝氣,不計較利益得失,更無關權術游戲,我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大概都只抱有一個單純而光明的目的——為祖國,為社會,為人民,謀取一個美好的明天。其中滿含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精神。也正是因為這個統一的目的,一致的愿望,才不至在思想上或感情上產生隔膜。
自由是學術之生命。何先生認為沒有標準是件好事。于我而言,我所經歷的恰恰是有標準的一代——標準教科書,標準解讀和標準答案。似乎強制灌輸多于引導,似乎發散的思維總被抑制。前段時間中國總有人問,為什么現代無大師?為什么中國出不了諾貝爾獎?我想也許何先生的話可以作為一種不無道理的回答:“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么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
學術自由也使老師的風格、興趣和思想得以在課堂上展現。不同的老師給學生提供不同的角度,學生在綜合分析之后形成自己的判斷,自己的思想,師生相互啟發,共同進步。“學術上不應該排資論輩”——師生之間的辯論常見于院子里教室里,成為“一景”,我想這才是學術該有的樣子,學術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死氣沉沉,枯燥迂腐,它也可以是生龍活虎,有聲有色的,是頭腦的風暴,思維的碰撞,靈感的火花和對真理的探求。良師益友在旁,學術氛圍濃厚,能在兵荒馬亂中開辟出這樣一塊小天地,自由地放飛思想,誰能說,那不是亂世中的天堂?
“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后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這實在是一種昂揚堅定的真正的樂觀主義精神。讀到這里,我有些明白,是什么,支撐著那個年代的人們前行。這讓我想起《命若琴弦》,信仰是什么?就是那張本無意義卻又被賦予了人生全部意義的白紙。就是憑著這種沒來由卻又無比堅定的希望,那一代人扛著中國走過了艱難的歲月,最終看見了真的希望。而這種樂觀主義也給予他們自己的人生以滋養,一群特定的年輕人在一個特定的年代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特定的價值與幸福,就那一刻來說,也算是一種圓滿。樂觀之所以被稱為樂觀,就在于它高估了現實。作為已經知曉后繼歷史的讀者看當時作者的希望,我在讀到兩個“非常美好”的時候,覺得悲哀又心酸,諷刺又無奈。我想,假如事先知道了以后的世界和生活也沒有那么美好,甚至還可能面臨一些大大小小的浩劫,那人還要有希望嗎?我給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命運,際遇總是反復無常,看清生活的真相卻依然熱愛它才是真正的成長。
書中描寫也能讓我們一瞥那時文人的面貌。于危難處見精神,于細節處見人格。梅貽琦先生跑警報時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在緊急關頭依然保持風度,這是一種文人修養內化于心的體現。戰亂時期吃穿住行都可以湊合,做實驗卻不行。治學精神可見一斑。老師有老師的堅守,學生有學生的執著,這種師生共同的堅持,著實令人感動。
讀這本書,我能感受到何兆武先生的真誠與溫暖。先生淡泊名利,率性真實,并沒有過多掩飾或修改。學生時代對老師的不敬,劉文典先生與沈從文先生之間的矛盾,汪曾祺的不修邊幅,楊振寧的年少輕狂……他把那時人們日常真實的面貌以自己的視角還原出來,通過他的口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人的一段獨一無二的歷史,也讓我們重新認識了那個時代的學者文人們。
讀罷上學記,西南聯大帶給我的震撼仍未消散,仿佛武陵人初見桃花源,心向往之。
我們失落了些什么,又該找回些什么?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批評的聲音出來了,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會有更多的批評或反批評,真理會在許多種聲音中越辯越明。而在這個過程中,謹忌煽動和憤青,不要被雜亂的洪流裹挾,我們需要的,是更嚴謹深入的獨立思考。正如何先生所說,“一個人,一個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視自己的缺點,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氣,真正進步。”
失落的天堂,于我們,是失落,于他們,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