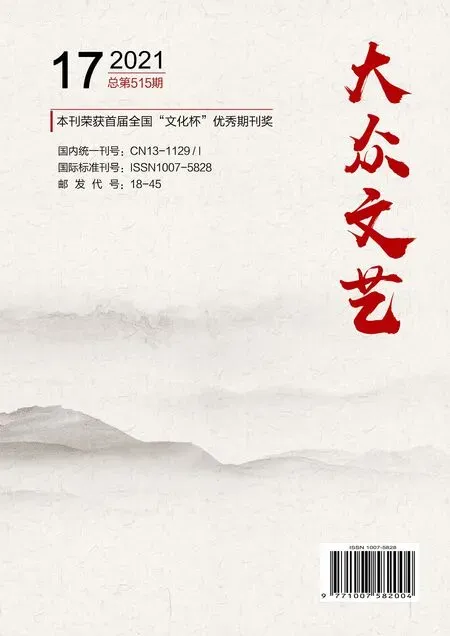藝術家的話語及其價值
當我們在看一幅畫時,當對畫面的形式或意義有所疑惑時,作為觀看者的我們內心總會禁不住在問:“畫家想表現什么?”。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的余音回蕩于專業史學家,理論家,批評家和業余藝術愛好者所構成的等廣闊領域。而這一問題的背后存在這樣一種藝術家和其作品的關系問題。也即是說,對于藝術作品來說,創作它的藝術家是一個很好的闡釋者嗎?藝術家的解釋具有權威性嗎?藝術家理解自己的作品在人類文明中所處的位置以及作品和歷史,社會之間的深層含義嗎?藝術家的解釋是開顯其作品意義的終極文本嗎?本文的出發點正是基于對上述諸問題的思考。
在肯特里奇的《贊陰影》一文中,肯特里奇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提醒自己:“記住你是位藝術家,而不是學者。但要避免六小時無知的招搖。”這段別有意味的話似乎蘊含著某種弦外音,其中暗含著這樣的前提,即藝術家和學者是有所區別的。同時值得我們思索的是,無知又意味著什么?藝術家相對于學者(當然是指在某一領域有所建樹的稱職的學者)而言是無知的嗎?要考察藝術家和學者的差別首先要對二者的本質有所了解,那么所要進行的工作便是按照科學的慣例進行大范圍采樣(范圍可涵蓋時間和空間,即縱向的由古及今和橫向的地理跨度),在采樣的基礎上進行歸納。然后把歸納的結論進行比對,其中牽涉的工作除了對比科學和藝術兩門學科,還要對比從事這兩個領域的個體的思維方式。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科學式的論證方式,因其所采用的根本原理或者元理論是以數學,哲學(其中包含邏輯學)和經驗科學為基礎。那么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便是“藝術家以何種方式去做這樣的論證“?藝術家能夠同時承擔學者的工作去進行科學嚴謹的分析和寫作嗎?回應這些問題首先要考察的便是藝術家的思維方式。讓我們從施坦伯格的《賈斯帕瓊斯---最初的七年藝術》中援引這樣的例子。施坦伯格在文中歸納了賈斯帕約翰斯作品的六個特點:
1.不管是物體還是符號,其作品的主題抑或描繪對象都是人造物。
2.所以主題都是我們周圍的普通物品。
3.所有主題都擁有一種常見的形狀。
4.他們要么是整體的實現,要么是完整的系統。
5.他們傾向于限定畫作的形狀或向度。
6.他們是扁平的。
7.畫面中的各元素之間無主次和等級區分。
8.他們可以與隱忍而不是行動聯系在一起。
而在二人對作品的討論中,卻出現如下有趣的對話:
1:關于《有四張人臉的靶子》的討論:
問:你為何正好將他們從眼睛底下切斷?
答:要是我將他們整個都放進去的話,盒子放不下。
2關于《青銅》的討論:
問:為什么電燈泡的青銅雕塑斷成了燈泡,插口和電線?
答:因為,當各個部件從鑄造車間翻出來后,那個燈泡無法插入插口了。
問:你不可以再做一個嗎?
答:可以的
問:那你喜歡這種支離破碎的樣子,你是有意選擇如此的?
答:當然。
由以上討論中,約翰.施坦伯格總結道:“約翰斯不會看到自由選擇與外在必然性之間的區別。”我們從約翰斯的話語中也確實看到施坦伯格這一斷言的正確性。同時也看到了藝術家作為作品的精神源頭和締造者,卻無法成為作品含義的令人信服的闡釋者。這一結論頗具幽默色彩。卻又是一種事實。但是約翰斯的作品僅僅是源于一種創作的機緣巧合?施坦伯格對這一問題并沒有進行深入分析。如果試圖對這一問題繼續追問,接下來所要面對的便是用于表意的兩種不同的符號體系——圖像和語言,其對應的兩種思維方式正是視覺思維與語言思維。而約翰斯的例子正體現了二者的區別。
圖像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表意符號,其運行方式遵循著不同的規則。在知覺心理學領域中有這樣一個兒童識別媽媽面孔的實驗:“實驗給4—6歲的兒童呈現媽媽和陌生人的快樂,生氣面孔照片,照片外鑲嵌不同顏色的方框,提示兒童作按鍵或不按鍵反應,按鍵正確時面孔和方框消失,按鍵錯誤則照片上出現紅叉。結果發現,被識別媽媽的電腦成分振幅明顯大于陌生人,說明兒童加工媽媽面孔的速度更快。“從中可以看出,兒童所進行的操作及選擇所運用的是知覺。也就是說,這樣的心理過程完全無需借助語言分析,而完全憑借視覺思維完成。從中可以看出,視覺思維有其特有的知覺運作方式。在視覺領域,可視物的整體和局部無需語言對其命名,他們本身在視覺系統里便是符號,這種符號可以直接被感知并通過視覺思維做出感覺上的歸納,推理和演繹,這些心理過程無需借助語言符號的再確認并統攝到語言邏輯中進行歸納,推理。但是視覺思維雖有其內部的邏輯性和完整性,但是存在于人類的文明之中,必須遵循人類文明的一種基本傾向,即我們無法通過一個圖像來說明另一個圖像。對圖像的闡釋必須通過語言這一超大符號體系(這一說法來自索緒爾)進行意義上的再確認。
阿恩海姆在《藝術與視知覺》中的斷言有力的指出了視覺思維和語言思維在當今人類文明中所處的位置以及二者的關系:我們繼承下來的文化現狀不僅特別不適宜于藝術生產,而且還反過來促使那些錯誤的藝術理論滋生和蔓延。我們的經驗和概念往往顯得通俗而不深刻,當他們深刻的時候,又顯得不通俗。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忽視了通過感覺到的經驗去理解事物的天賦。我們的概念脫離了知覺,我們的思維只是在抽象的世界中運動,我們的眼睛正在退化為純粹的度量和辨別的工具。結果,可以用形象來表達的觀念就大大減少了,從所見的事物外觀中發現意義的能力也喪失了。這樣一來,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其意義的事物面前,我們倒顯得遲鈍了,而不得不去求助我們更加熟悉的另一種媒介——語言。“那么如果通過語言,在掌握視覺思維的規則之外,便要掌握語言規則。而藝術家(至少是部分的藝術家)便是那些掌握了視覺思維規則而未很好的掌握語言規則的人。與其說藝術家“不會看到自由選擇與外在必然性之間的區別” 毋寧說藝術家在知覺系統中完成分析選擇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這一心理過程,卻不能很好的駕馭語言系統對其加以再確認并合乎語言邏輯對其合理表達。
接著再讓我們看看其他藝術家的語言表達。在隱士畫家哈莫修伊的只言片語中,我們將看到藝術家語言的某些特點。當有人問及哈莫修伊畫面中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時候,哈莫修伊的回答是”線” 。此時我們腦海中若浮現出哈莫修伊那寂靜而帶有神秘色彩的畫面時,“線”是如何存在于其畫面中呢?顯然,哈莫修伊畫面中從來不存在波提切里式的線,即那種清晰的線條。甚至可以說哈莫修伊的畫面形式是在消解波提切利式(或者說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那種清晰而明確的輪廓線。線在波提切利的時代,或者那么在今時今日,我們對線的基本認知都很相似。比如拿出一支筆,在一張空白的紙上隨意畫出一條線,這便是我們認知中常見的線:其走向有某一方向性,并且痕跡清晰。而哈莫修伊的畫面中,事物的邊緣顯然缺少清晰性,但從形式的角度來觀查畫中事物的邊緣仍然具有支撐整體畫面構成的美學意義。因此,我們可以把哈莫修伊的線理解為對常規意識中的線的破除,也可理解為擴大了線的概念和外延。而這一視覺思維的結論在哈莫修伊的言語中顯然缺少清晰的表達。因此,為了讓他人能夠與畫家的視覺邏輯同步,我們必須用語言闡釋其視覺邏輯。還有一個文森特梵高的例子,在《藝術與視知覺》中,阿恩海姆例句了梵高對《小酒館》這一作品的繪畫動機,梵高聲稱要通過畫面表達安靜的感覺,而畫面中的色調卻有著激烈的碰撞和躁動。阿恩海姆對此歸結為畫家的感知和觀者不對應。
從上訴例子可以看,藝術家要利用另一種工具——語言進行表達,就勢必進入一個遵循另一種規則的戰場并利用他不熟悉的武器進行戰斗。然而不管是錯誤的論證也好,不嚴謹的推理也罷,或是措辭的不恰當,對概念或文本的誤讀,這些都不同程度的展現了藝術家創作的心理過程。這種展現超越了藝術家的主觀意識層面,其背后蘊含著不同時段和地域的社會思潮,某種人性中的精神訴求抑或隱秘的精神現象。而這些正需要學者把其作為線索而后采取科學的研究方法并依托文本進行更為深刻和全面的揭示,從而梳理人類主體精神世界和作品外在形式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