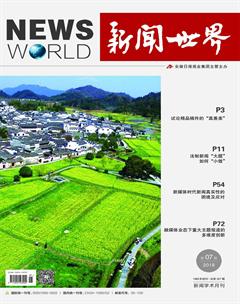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數(shù)字化傳播策略研究
胡成林 羅艷
【摘 要】速度快、范圍廣的數(shù)字化傳播突破了傳統(tǒng)傳播方式的局限,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帶來(lái)了新的傳播渠道。本文主要從三個(gè)方面探討了數(shù)字化傳播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帶來(lái)的新渠道:移動(dòng)二維碼帶來(lái)的延伸閱讀、VR(虛擬現(xiàn)實(shí))技術(shù)帶來(lái)的虛擬再現(xiàn)、數(shù)字化影像技術(shù)帶來(lái)的文化復(fù)原。數(shù)字化傳播給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信息化傳播帶來(lái)的創(chuàng)新,為當(dāng)前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新模式,這對(duì)增強(qiáng)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關(guān)鍵詞】少數(shù)民族文化;數(shù)字化傳播;傳播路徑
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繁榮發(fā)展,既是中華民族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體現(xiàn),也是我們建設(shè)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重要力量。隨著我國(guó)現(xiàn)代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少數(shù)民族文化正面臨著嚴(yán)峻的挑戰(zhàn)。而信息化時(shí)代,數(shù)字化傳播憑借其顯著的傳播優(yōu)勢(shì),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傳播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契機(jī)。
一、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數(shù)字化傳播概述
隨著我國(guó)現(xiàn)代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保護(hù)和傳承問(wèn)題已經(jīng)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一方面,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繁榮發(fā)展,既是中國(guó)民族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體現(xiàn),也是我們建設(shè)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下,一些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正面臨著文化認(rèn)同危機(jī),因“后繼無(wú)人”而面臨消亡的危險(xiǎn)。當(dāng)前,我國(guó)政府正在積極探索如何采用有效手段應(yīng)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化面臨的困境,拓展少數(shù)民族文化在當(dāng)代文明中的生存空間,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數(shù)字化傳播正是在這種時(shí)代背景下產(chǎn)生的。
數(shù)字化傳播是為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的需求而出現(xiàn)的一種新型信息傳播活動(dòng)。數(shù)字化傳播把各種數(shù)據(jù)和文字、圖示、動(dòng)畫(huà)、音樂(lè)、語(yǔ)言、圖像、視頻信息組合在一起,是集合了語(yǔ)言、文字、聲像等特點(diǎn)的新的傳播途徑,能提供多種網(wǎng)絡(luò)傳播方式來(lái)處理包括捕捉、操作、編輯、貯存、交換、放映、打印等多種功能。[1]數(shù)字化傳播技術(shù)可以將無(wú)形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有形化和情境化,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lái)記錄少數(shù)民族文化發(fā)展,再現(xiàn)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內(nèi)容,從而創(chuàng)新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傳播渠道。
二、數(shù)字時(shí)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承路徑優(yōu)化
現(xiàn)代數(shù)字科技手段的應(yīng)用使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傳播和發(fā)展有了更多有效的選擇,同時(shí)也將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hù)帶到新的層面和高度。本文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數(shù)字化傳播主要從以下三個(gè)方面進(jìn)行探討。
(一)移動(dòng)二維碼:傳播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重要路徑
近年來(lái),在大街小巷我們都能看到移動(dòng)二維碼的身影,它的便捷之處在于能夠在幾秒時(shí)間內(nèi)進(jìn)行付款和對(duì)各類(lèi)信息進(jìn)行解碼。例如我們拿手機(jī)掃一掃分布在報(bào)紙雜志上,衣服鞋子上,食品包裝上的二維碼就可以獲取相關(guān)鏈接信息,從而快速得到我們想要的圖片、文字、音頻和視頻等,而且還可以在相關(guān)信息下方留言互動(dòng),進(jìn)行深入的了解。移動(dòng)二維碼就相當(dāng)于一張網(wǎng)絡(luò)通行證,它能夠?qū)⒉煌襟w融合起來(lái),在受眾和移動(dòng)終端(手機(jī))之間架起一座信息互換、信息延伸的橋梁,最終實(shí)現(xiàn)文化的個(gè)性化和多元化交互體驗(yàn)。
根據(jù)中國(guó)市場(chǎng)調(diào)研在線(xiàn)發(fā)布的《2018年中國(guó)手機(jī)行業(yè)調(diào)查與未來(lái)報(bào)告目錄》顯示,中國(guó)手機(jī)普及率達(dá)到95%左右,使用人數(shù)已經(jīng)達(dá)到12.8億,使用者集中在15-50歲之間的人群。龐大的移動(dòng)二維碼適用群體,便捷的二維碼技術(shù),給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播提供了一個(gè)良好的契機(jī)。
民族博物館是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陣地,但傳統(tǒng)的博物館一般是簡(jiǎn)單的二維平面文物陳列室,是一種靜態(tài)、單調(diào)的線(xiàn)性文化展示,這種單向的文化傳播模式無(wú)法使參觀(guān)者得到一種及時(shí)的文化信息反饋,容易使參觀(guān)者喪失主觀(guān)參與的興趣,原本希望通過(guò)文物與歷史對(duì)話(huà)的愿望就可能被靜態(tài)展示中的“走馬觀(guān)花”所斷送,從而影響到文化展示中的傳播效果與效率。新疆是一個(gè)多民族聚居的地區(qū),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在平鋪式展板信息中容易使參觀(guān)者喪失對(duì)文化參觀(guān)的主動(dòng)性,最終變成被動(dòng)接受。
《新疆民族風(fēng)情陳列》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里的第二個(gè)館,這里通過(guò)蠟像、民族生活場(chǎng)景復(fù)原等方式,展現(xiàn)了在新疆生活的主要民族如維吾爾、哈薩克、回、蒙古、滿(mǎn)、俄羅斯等12個(gè)民族的民俗風(fēng)情。參觀(guān)者要想在有限的觀(guān)展時(shí)間里弄清每個(gè)民族的特色,僅靠博物館里的解說(shuō)牌和講解員,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但移動(dòng)二維碼提供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不僅能使參觀(guān)者與文物進(jìn)行對(duì)話(huà),還能滿(mǎn)足他們的針對(duì)性需求,激發(fā)他們的自主學(xué)習(xí)欲望。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參觀(guān)者只需掃一掃文物旁邊的二維碼就能完成信息的快速傳輸,實(shí)時(shí)調(diào)取自己感興趣的深層信息,同時(shí)還可以有選擇性的保存網(wǎng)址鏈接,空閑時(shí)候可以進(jìn)行延伸拓展閱讀,從而實(shí)現(xiàn)“手機(jī)—展示信息”之間“物物相連”的信息互動(dòng),使文化以動(dòng)態(tài)的形式存在。
2018年5月18日是第42個(gè)國(guó)際博物館日,其主題是“超級(jí)連接的博物館:新方法、新公眾”,在這個(gè)萬(wàn)物互聯(lián)的數(shù)字時(shí)代,移動(dòng)二維碼可以實(shí)現(xiàn)文化與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空連接,二維碼中的視頻、音頻和文字等可以讓我們的博物館變身為講壇、課堂或者書(shū)吧,使博物館成為連接公眾與多元文化的紐帶,這種新的傳播方式可以使參觀(guān)者獲得一種深刻而又新鮮的文化體驗(yàn),也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一種新的渠道。
(二)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虛擬再現(xiàn):增強(qiáng)受眾參與體驗(yàn)的一種方式
2016年被稱(chēng)為VR元年,VR技術(shù)被應(yīng)用到各行各業(yè),例如“VR+新聞”、“VR+游戲”、“VR+電影”和“VR+醫(yī)療”等等,一時(shí)間“VR+”成為熱點(diǎn)。同年12月,福建省的“VR+紅色福建”成為全國(guó)首個(gè)VR展廳,在這里VR技術(shù)被應(yīng)用到了紅色文化傳播過(guò)程中。近年來(lái),VR技術(shù)也被廣泛應(yīng)用到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和保護(hù)中,以及其他文化領(lǐng)域。
早在2003年,中國(guó)故宮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會(huì)社合作打造的VR作品——《紫禁城天子的宮殿》,讓觀(guān)眾可以在三大殿、養(yǎng)心殿等古跡中自由自在地游覽,體驗(yàn)皇家文化的宏偉博大。這種震撼人心的視覺(jué)效果,讓人們?cè)谳p松愉悅的環(huán)境下學(xué)習(xí)有關(guān)故宮的歷史,同時(shí)也讓故宮的形象深入人心。
我國(guó)許多少數(shù)民族居住在山林、高原、草原等邊陲地區(qū),一些文物古跡受到現(xiàn)實(shí)條件的制約難以走出去。例如:滋養(yǎng)吐魯番的千年水源生命線(xiàn)——坎兒井,極具民族特點(diǎn)的地下水利灌溉系統(tǒng),目前只能透過(guò)“實(shí)物搭建”的形式在吐魯番坎兒井博物館中展現(xiàn),受到空間、運(yùn)輸困難等的限制,難以走出新疆。但是利用VR技術(shù)我們可以模擬坎兒井實(shí)物,搭建具有代表性的數(shù)字化“坎兒井”展廳,使其打破時(shí)間和地域限制,滿(mǎn)足人們觀(guān)賞、研究等需求。數(shù)字虛擬展廳完全不受空間、運(yùn)輸?shù)葪l件的限制,可以展示到世界的每個(gè)角落,使大型實(shí)物展品在傳播過(guò)程中突破地緣局限,形成主題巡回展覽。這既能促進(jìn)少數(shù)民族文化與世界的交流,也有利于增進(jìn)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
文化的另一個(gè)動(dòng)態(tài)展現(xiàn)就是 VR閱讀,這是新媒體時(shí)代的一種新興閱讀方式,其特別之處就在于通過(guò) VR技術(shù)提供的全景畫(huà)面,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地閱讀,隨時(shí)隨地與書(shū)中的人物環(huán)境進(jìn)行互動(dòng)。
《大開(kāi)眼界:恐龍世界大冒險(xiǎn)》是國(guó)內(nèi)第一部VR技術(shù)科普讀物,在2016年北京圖書(shū)訂貨會(huì)上誕生。它利用VR技術(shù),虛擬出一個(gè)“真實(shí)”的遠(yuǎn)古自然環(huán)境,讓閱讀者“真實(shí)”的感覺(jué)到各種恐龍就在眼前活動(dòng)著,在這里他們可以一邊穿梭在恐龍的家園里,一邊學(xué)習(xí)有關(guān)恐龍的各種知識(shí)。這種沉浸式“閱讀”能給讀者帶來(lái)一種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yàn)和震撼人心的漫游樂(lè)趣,從而提高閱讀效率和閱讀興趣。同樣,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經(jīng)典故事,也可以通過(guò)VR技術(shù)呈現(xiàn)在孩子們的書(shū)本上,讓他們?cè)谧灾魈剿鬟^(guò)程中加深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認(rèn)識(shí),使少數(shù)民族文化能得到更好的傳播。
眾所周知——出于對(duì)文物的保護(hù),稀有珍貴的原始文獻(xiàn)只作保存不能借閱,不能為大眾所觸碰,這實(shí)在是一種文化的遺憾。但是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VR技術(shù)可以彌補(bǔ)人們的這一遺憾,利用VR技術(shù)將這些稀缺珍貴的文獻(xiàn)在虛擬世界中還原,使讀者零距離瀏覽、翻閱它們,這樣既能滿(mǎn)足讀者的求知欲,又有益于珍貴文獻(xiàn)的傳播與傳承,且不用擔(dān)心文獻(xiàn)遭到破壞。讓普通讀者擁有閱讀珍貴文獻(xiàn)的機(jī)會(huì),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爭(zhēng)議問(wèn)題,也能夠起到很好的化解作用,從而避免文化誤讀、誤解問(wèn)題。
(三)數(shù)字化影像技術(shù):斷層文化再現(xiàn)或復(fù)原的一種渠道
文化發(fā)展的非連續(xù)性即為文化斷層,關(guān)于文化斷層論,孫關(guān)龍?jiān)l(fā)表過(guò)《斷層文化論》一文,他認(rèn)為文化普遍有斷層,是斷續(xù)發(fā)展的,而不是至今所有書(shū)籍中所主張的連續(xù)發(fā)展,不間斷地積累的。[2]世界上任何古老的民族都會(huì)遇到一個(gè)共同的問(wèn)題——文化斷層,其主要表現(xiàn)為文化失落、文化裂變、文化絕滅、文化提升等。
“田野調(diào)查”和“參與觀(guān)察”是利用數(shù)字化影像技術(shù)傳播少數(shù)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修復(fù)斷層文化的最佳方法。“田野調(diào)查”是指研究者在一個(gè)地區(qū)長(zhǎng)期生活,通過(guò)自己的體驗(yàn)和調(diào)查去獲得第一手資料;“參與觀(guān)察”則是指研究者深入到民族地區(qū)親身參與地方活動(dòng),以成員身份進(jìn)行隱蔽性觀(guān)察并記錄和拍攝下當(dāng)?shù)孛褡逦幕闹饕獌?nèi)容。
在歷史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一種文化的系統(tǒng)認(rèn)識(shí)如果沒(méi)有被完整地保存下來(lái),就會(huì)出現(xiàn)文化斷層,這種文化就容易被人遺忘,逐漸走向消亡。例如:寄托著民族情感的錫伯族刺繡,是錫伯族民俗文化的象征載體,也是錫伯族歷史文化的見(jiàn)證,有很高的歷史價(jià)值和藝術(shù)價(jià)值。但近年來(lái),受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的影響,錫伯族刺繡一度出現(xiàn)因“后繼無(wú)人”而面臨消亡的危險(xiǎn),于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數(shù)字化影像技術(shù)可以為這種民族文化提供選擇性修復(fù)。
錫伯族刺繡善于將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通過(guò)手藝表達(dá)出來(lái),賦予其豐富的內(nèi)涵。早期的錫伯族刺繡具有北方漁獵文化的顯著特征。明末清初,錫伯族被編入八旗,其刺繡品以軍服和官服為主,也應(yīng)用于旗袍、坎肩、枕頭、門(mén)簾、茶具蓋布等生活用品方面。西遷至新疆的錫伯族,受當(dāng)?shù)匾恍┥贁?shù)民族文化的影響,刺繡內(nèi)容也增添了新的地域特色。
錫伯族刺繡一直在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背后承載了什么樣的歷史故事,每一種刺繡圖案又被賦予了什么樣的意蘊(yùn),這些又為我們留下了怎樣的民族精神與文化血脈?要想理清這中間的發(fā)展脈絡(luò),我們就需要通過(guò)“田野調(diào)查”和“參與觀(guān)察”去獲取有關(guān)錫伯族刺繡的一手資料,然后利用數(shù)字化影像技術(shù)將錫伯族刺繡帶回西遷之前,將真實(shí)變遷過(guò)程以故事的形式還原給觀(guān)眾。使得人們從故事中了解刺繡,從花紋圖案中了解文化底蘊(yùn),把簡(jiǎn)單的文化符號(hào)與其背后所傳達(dá)出來(lái)的民族文化精神聯(lián)系在一起,放在新媒體平臺(tái)中進(jìn)行傳播和擴(kuò)散,將民族歷史與當(dāng)代文化認(rèn)知溝通起來(lái),還讀者一個(gè)文化過(guò)程體驗(yàn)的完整性。數(shù)字化影像技術(shù)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再現(xiàn)或復(fù)原,可以為人們提供一種文化的系統(tǒng)認(rèn)知,從而提高人們的文化解讀和創(chuàng)新能力,促進(jìn)文化的繁榮發(fā)展。
結(jié)語(yǔ)
數(shù)字化傳播給少數(shù)民族文化帶來(lái)了新的敘事方式,也為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能夠擴(kuò)大自己的關(guān)注度和傳播度,獲得一個(gè)新的發(fā)展模式。但是少數(shù)民族文化數(shù)字化傳播也存在一些問(wèn)題,比如“ VR閱讀”模式尚不成熟, VR人才也比較短缺,而且數(shù)字化傳播是建立在強(qiáng)大的網(wǎng)絡(luò)基礎(chǔ)上的,但是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網(wǎng)絡(luò)建設(shè)還有待提高,這就決定了少數(shù)民族文化只能走出去,難以走進(jìn)來(lái)。所以數(shù)字化傳播在具體應(yīng)用過(guò)程中還有待完善和提升,這需要我們進(jìn)行更深層次的探索。
注釋?zhuān)?/p>
[1] 蔡夢(mèng)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數(shù)字化傳播研究——以數(shù)字出版為視角[J].中國(guó)傳媒科技,2017(03):86—90.
[2] 譚濤,夏思永.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斷層現(xiàn)象探析[J].體育成人教育學(xué)刊,2007(03):9—11.
(作者:胡成林,新疆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新聞與傳媒學(xué)院2016級(jí)傳播學(xué)碩士研究生;羅艷,新疆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新聞與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
責(zé)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