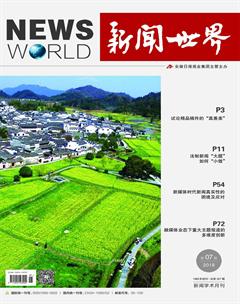人際交往視角下的新媒介技術應用
劉士超
【摘 要】與傳統媒體時代相比,新媒介技術下的人際交往呈現出更為場景化的特點。本文探討了新媒介技術對于人際交往的影響,認為新媒介技術在人際交往方面創造出了新的生態環境,并在維系強關系、發展弱關系以及進行社群聚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負面影響,例如私人信息公開化的風險,在場離席的尷尬和時空斷層造成的等待和焦慮。對此,應從“媒介批判意識”和“新媒介交往能力”兩方面來整合新媒介素養,以提升新媒介技術下對媒介的駕馭能力。
【關鍵詞】人際交往;新媒介技術;場景; 新媒介素養
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出現后,網絡在線已經成為了多數人的生活常態,作為一種媒介技術,網絡極大地延伸了我們對于空間和時間的感知能力,新媒介技術在創造新的信息環境的同時,也在重塑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交往行為和生活方式。借助新媒介技術,我們可以與他人之間實現即時交流,在第一時間獲取訊息。感官的延伸還意味著個人生存空間邊界的擴展,能夠建立與遙遠地方之間的聯系,創造并維系“遠距離的親密感”。[1] 然而,在因新媒體技術而產生的迅疾的傳播速度、龐雜的信息以及非對稱的信息交流環境中,社會開始向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液態社會”轉變,人與人的關系狀態,也開始變幻不定。
一、連接、維系與價值認同:人際交往新生態
新媒介技術在改變人際交往方式的同時,也在改變人際傳播中的自我認知。數字化人際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面對面的互動形式,通過電子設備傳遞的多媒體樣態并不比現實中的人際互動缺少人性,相反,身體的離場可以減少在場交流時所生成的畏懼、壓力和自我意識沖突,從而放大人們內心中更真實、更底層的情感,而新媒體中非語言符號的廣泛使用又能夠彌補情感內容的缺位。
(一)強關系的時空突破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中國是一個 “熟人社會”。因此在中國的人際交往歷史中,強關系始終發揮著重要的紐帶作用,人們通過強關系相互連接,編織成一張張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際關系網絡。新媒介技術對強關系的主要作用體現在跨時空親密度的維系以及提供多樣化表意的場景上。“當人際傳播從現實情境轉向身體不在場的非同步語境時,交際中的角色就會激發適應性傳播行為,如進行有目的的前臺呈現或和減少不確定因素等,由此產生理想化的人際認知”, [2]并營造更高強度的互動親密感。
(二)弱關系發展新生態
陌生人關系是一種隨時可能改變的狀態,在傳統的媒介環境下,除有特殊需要外,人們并沒有主動與陌生人交際并且建立弱關系的強烈需求,但是在社交媒體時代,這一狀況發生了極大改變。網絡打破了陌生人之間社會交往的邏輯邊界,匿名性與傳播的泛文本化模糊了人們交往的心理邊界。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數不勝數的傳播渠道增加人們建立弱關系的機會,也提升了由弱關系轉化為強關系的幾率;其次,在紛繁復雜的虛擬空間中,窺伺、尋求認同、宣泄壓力等需求也被廣泛激發出來。
相比較于熟人關系,因新媒介技術而產生的交際場景創造出了陌生人社交的新生態。人們可以在各種場景:網絡游戲、BBS論壇、新聞評論區、直播圍觀的過程中與大量陌生的“他人”進行接觸,從而在互動中完成自我呈現與價值認同,建構和維持新一級的人際交往關系。
(三)人際交往的價值聚合——網絡社群的崛起
新媒介技術提供給用戶的一大價值是溝通渠道的互通,網絡在完成對傳統媒體“去中心化”的同時,也在構建著以每個用戶為節點的“泛中心化”。用戶變成了網絡世界中的一個個傳播節點,這些節點最終構成了一個扁平化的網絡傳播系統。用戶在這個系統當中不僅僅生成內容,而且接受并消費內容,實現了“人人都是互聯網傳播中心”的技術性民主。
網絡社群的建立是一種通過人際傳播建構場景的過程,它“改變了以地緣為劃分的社區概念,也突破了朋友圈、熟人圈和陌生人的界線”。 [3]由于互聯網的技術特性,通過新媒介進行的網絡傳播會降低社會行為規范對于群體的約束力,這在網絡社群中表現為高度趨同性的言語行為,他們有著對同一事件更高的關注度和期望值,其成員在一致言行和目標中獲得了情感能量和價值認同,除此之外,在網絡社群中還存在有強弱關系相互轉化的可能。
二、沖突與挑戰:新媒介技術下的人際交往困境
在新媒體時代,社會呈現出更多的“液態流動性”,原有的時空界限被打破,我們每時每刻都受到不同信息的影響。與此同時,新的媒介技術為網絡虛擬空間的傳播節點——每一位用戶打開了更多的出入口,并開始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新的感知尺度也帶來了更多不確定的結果。在人們追逐人際關系的過程中,也可能要面對很多挑戰,例如信息圍捕、離場的尷尬、等待的焦慮等等。
(一)圍捕與潛入:私人信息公開化的潛在風險
由于社交媒介的可視性,特別是社交軟件的跨語境信息流動,使得用戶在使用社交媒介過程中存在被“監視”的可能。“圍捕”(hunting)和“潛入”(creeping)發生的頻率和強度都在增加。 [4]以網絡為基礎的新媒介技術能夠實現跨時空的信息傳播和資源共享,這也使得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開始模糊。其邊界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個人對自身隱私控制權的變化。
私人信息公開化的另一風險在于,虛實空間個人形象的非對稱交疊。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認為,人們會預先設計或者展示自己的形象——并努力取得良好的展示效果。這一點在社交媒體上尤為突出,社交平臺上人們的自我呈現和印象管理,需要精心設計和刻意展示來獲得他人的認同和支持。然而,這種通過嚴格把關來向外界開放的虛擬形象與現實生活中的個人角色存在矛盾,而這種矛盾一旦被激化,便會對自我形象產生沖擊,形成難以預知的后果。
(二)尷尬與落差:在場缺席的現實情境
傳統媒體時代,屏幕的單一與連接的稀少意味著對現實生活的相對關注和目標共享。但在移動互聯網的社會環境中,手機將每一個個體分割開來。它“開啟了人們彈性組織其日常生活的可能,而這樣的彈性更清楚的反映便是人們對于時間、空間認知的轉變……傳統序列、固定性的時空框架的液化,人們不再受限于某種會共享的時間,也不再被‘在場所束縛”。 [5]移動互聯網以及智能終端的普及,產生了大量“在場的缺席”。我們越來越習慣于借助網絡媒介進行交際,反而會對現實中的交往產生不適。
如今的手機已經成為了一種符號化的象征,向現實交流場景中的他人傳遞出特定意義——“暫時離場和自我隔離”,互動的另外一方會將玩手機理解為“缺場”的互動者的進場,作為互動的一方不如缺場的進場者重要。這種社會比較會帶來強烈的認知失調,不適應甚至情緒上的負面反應,比如尷尬、憤怒等情緒反應就會油然而生。在親密關系中,這種由于比較產生的負面情緒更加明顯。[6] “在場而缺席”的實質是虛擬空間對于現實空間的壓迫和擠占。原本面對面交流本身所要求的對對方關注這一互動規則事實上遭到了挑戰。
(三)等待與焦慮:時空斷層下的碎片疊加
新媒介技術本身的傳播特性和功能設計,使得人們對于時效的追求不斷增加,但對等待的忍耐程度卻越來越低。即時通訊軟件的出現也促使用戶對即刻回應懷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能夠時時保持聯絡。“在理性規劃時間的社會中,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組織、乃至組織之間的時間越來越零碎、也更難協調,等待是協調所必須付出的成本。”[7]
一方面,由于信息爆炸和即時通訊的存在,等待回應的不確定感變得更加強烈,使得人際交往時刻處于緊迫感中;另一方面,當各種信息和端口分割了人們的有限精力,各類社交軟件、資訊APP打破了時空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傳播開始變得碎片化,雖每一個信息界面的使用只占用很少的時間,但是由于界面開啟的簡易性,碎片變得極易疊加,時間的零碎化加劇了人們對時空斷層的感知。時空斷層并不是一個人所處的狀態,而是交往雙方共同構建的情境,由于其本身便具有身份的不對稱性,交際雙方對于彼此重要性的認知具有必然的差異。
三、駕馭媒介
信息社會的知識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傳統媒介時代,面對浩如煙海的信息和知識,人們常常感到壓力和無所適從。雖然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越來越多,但用戶處理信息的能力卻無法和信息更新以及信息渠道增加的速度相匹配。與傳統大眾傳播相對“安逸”的被動接納不同,新媒介所帶來的主動傳播必然會增加對于自身的消耗。因此,我們有理由警惕新的媒介技術對自我的異化,提高對于新媒介技術的駕馭與控制能力。尤其當新媒介技術產生的風險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時,提升媒介素養就不再是一句空話。
當前,以社會性、個性化和主體性為特征的新媒體構建了一個全新的信息環境,這對用戶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新媒介素養應著重注意“媒介批判意識”和“新媒介交往能力”的提升。 [8]批判意識的培養需要用戶保持對媒介信息的反思與獨立判斷,其本質是為了抵制媒介文化對受眾的負面影響,培養受眾自身的批判能力和主體意識;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詹金斯將新媒介素養概括為“11大核心技能”,其中幾乎每一項都在強調個體與他人之間的交流,每一項都在強調個人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互動,其核心精神就是在虛擬網絡世界中個體應該具備的與他人進行社會交往的能力,即“新媒介交往能力”,[9]應對新媒介條件下人際交往的種種挑戰,應當從提升媒介批判能力以及新媒介交往能力開始。
結語
新的媒介技術大大延伸了人們的主體性和自反性,由此帶來的是整個交往行為以及認知心理的變化。技術的觸連與介入使“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從固定社會關系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但又可能令其陷入因交往關系復雜化和淺層化所帶來的認同困境之中。[10] 學者陳力丹也指出:傳播技術的發展和不斷的更新換代,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幸事,它的動力不是人的真實需求,而是擁有資本的網絡開發商對利潤的無限追逐。不可否認,新媒介技術為人際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突破時空界限,連接到每一位用戶,并構建了新的交往情景。但同樣的,也應當對技術所造就的潛在可能保持一定的警惕與節制。
注釋:
[1]陳力丹,毛湛文.時空緊張感:新媒體影響生活的另一種后果[J]. 新聞記者,2014(01).
[2]L. Crystal Jiang &Jeffrey; T. Hancock. Hancock, "Absence Makes the Communication Grow Fonder:Geographic Separation,Interpersonal Media, and Intimacy in Dating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63, 2013, pp556-557.
[3]劉磊,程潔.顛覆與融合:論廣告業的“互聯網+”[J].當代傳播,2015(06):84-86+89.
[4]胡春陽.經由社交媒體的人際傳播研究述評——以EBSCO傳播學全文數據庫相關文獻為樣本[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11):96-108+128.
[5]曹家榮,黃厚鏈.流動的手機:液態現代性脈絡下的速度、時空與公私領域[C].世代重要議題—人文社會面向研討會論文,2011
[6]張杰,付迪.在場而不交流?移動網時代的人際交往新情境建構[J].國際新聞界,2017(12):154-170
[7]王淑美.網絡作為時光機:日常網絡使用與時間意義之初探[C].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
[8]李德剛,何玉.新媒介素養:參與式文化背景下媒介素養教育的轉向[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12):39-40.
[9]Jenkins,Purushotma,Clinton,Weigel &Robinson;,2006
[10]華維慧.“秀”:技術“中介化”與人際傳播中的“自我”分析[J]. 編輯之友,2017(08):57-60.
(作者: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