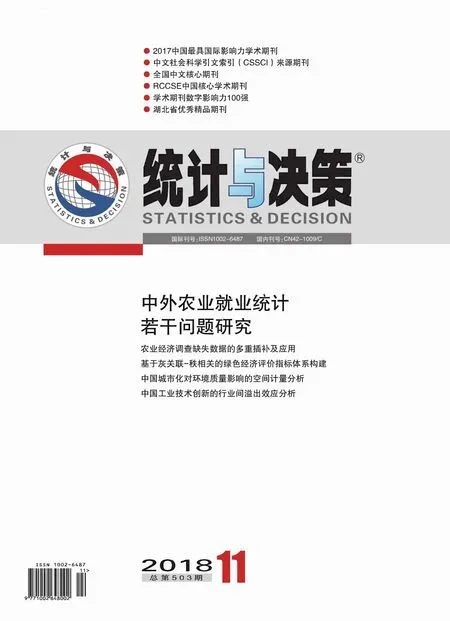貨幣、房價與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區制關聯性的實證
胡靜,黎東升
(1.長江大學經濟學院,湖北荊州434023;2.浙江科技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0023)
0 引言
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關鍵時期,傳統的投資拉動難以為繼。“新常態”下經濟的健康發展既要擴大消費與內需,也要防范房價劇烈波動而引發的經濟風險。在此背景下,客觀評價我國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貨幣、房價與居民消費支出間的動態關聯性,不僅對于相關部門貨幣政策決策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而且對于建立穩定房價的長效機制、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學者們圍繞資產價格與消費的關系進行研究形成了部分經典理論,如托賓“q理論”、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論、杜森貝的“棘輪理論”等。從房價對居民消費的作用渠道來看,大致可歸納為:“財富效應”[1];“擠出效應”[2]、“抵押效應”[3]。也有學者針對房價對居民消費支出的經濟效果進行研究,但并未得到一致結論。房價波動對最終消費的經濟效應分為正向[4-6]、中性[7-10]及負向[3,11,12]。
現有成果主要從房價上漲的角度考察了房價與居民消費間的線性關系,而現實情況是房價雖以上漲為主,但也在金融危機及“限購限貸”政策影響下經歷了短暫下跌。且房價對消費的最終影響受多種因素疊加作用,從而可能表現為二者存在非線性關系,即區制關聯性。故本文將構建MS-VAR模型實證研究我國貨幣供應、房價與居民消費間的非線性關系,以揭露不同經濟狀態下變量間的動態關聯性,為有關部門經濟決策提供有益參考。
1 MS-VAR模型設計
1.1 模型說明
本文采用內生識別結構轉換的MS-VAR模型,該模型由Hamilton(1989,1994)[13,14]提出,優勢在于它允許模型參數隨著樣本數據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觀測的區制狀態變量轉換而變化,且該狀態變量遵循馬爾科夫區制轉換(Markov-Switching,MS)過程。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其中,st為不可觀測的區制變量,p為滯后期,從區制i到區制j的轉換概率為:

m為區制數。更準確地說,st服從遍歷不可約的m個狀態馬爾科夫過程,其轉制矩陣可表示為:

矩陣中每一行有:pi1+pi2+...+pim=1, i=1,...,m。
MS-VAR模型可進一步表示為:

模型中截距、均值、系數、方差均可隨區制轉變而變化,由此將MS-VAR模型進一步分為MSI-VAR、MSM-VAR、MSA-VAR、MSH-VAR,以及均值和方差均可變的MSMH-VAR、截距和方差均可變的MSIH-VAR、截距、系數和方差均可變的MSIAH-VAR等混合模型[15]。
1.2 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
因我國住房市場化改革主要針對城鎮地區,且房產已成為城鎮家庭的重要資產,故本文重點考察房價波動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文中所涉及廣義貨幣供應量(M2)、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P)①、城鎮家庭人均消費支出(C)均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數據顯示2003年后我國房價波幅明顯,截至2016年底已經歷完整的漲跌周期,故選取2003—2016年季度數據,并將環比CPI轉換為以2003年初為基期的CPI數據,再分別對M2、P和C進行價格處理,獲得實際值,在此基礎上得到2004—2016年M2、P和C的季度同比實際增長率,分別記為RM2、RP和RC,合計52組樣本。同比數據不存在季節趨勢,故無需進行季度調整。首先分別對RM2、RP和RC進行平穩性檢驗,表1為Eviews8.0軟件的ADF檢驗結果。

表1 變量ADF檢驗結果
由表1可知,RM2、RP、RC均為平穩變量,符合VAR模型的構建要求。為直觀顯示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以上變量的變動趨勢,將2004—2016年各變量季度數據以圖1表示。

圖1 2004年第1季度—2016年第4季度RM2、RP、RC的變動趨勢
由圖1可見,2004年以來,多數時候廣義貨幣供應量穩步增長,2008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短期內大幅增加廣義貨幣供應量,而隨著危機的退去,貨幣供應增速再次恢復平穩。從房價來看,RP多為正值,僅在2008年、2012年和2014年前后為零值以下,即這些年份中房價下跌,研究期間內房價已經歷完整的漲跌周期。從居民消費來看,RC波動頻繁,且均為零值之上,說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居民消費整體保持上漲。此外,從貨幣、房價和消費間的相互關系看,RP與RM2走勢基本一致并略有滯后,表明二者密切相關,不斷增加的貨幣供應或主要流向房地產領域并推動了房價上漲。RC相對RM2和RP而言波幅較小而頻率較高,即使在RM2和RP劇烈波動的金融危機期間,RC波幅也較為有限,且從圖1難以確定RM2和RP對RC的具體影響方式,其原因可能是三者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且消費本身具有“黏性”,短期內受外部因素影響有限。故下文采用MS-VAR模型實證研究不同狀態下貨幣、房價與消費間的區制關聯性。
1.3 MS-VAR模型形式的確定
按通常做法,MS-VAR模型滯后期的選擇參照線性VAR模型的確定標準,故先建立線性VAR模型并依據LL最大及AIC、SC最小原則確定滯后期。以下運算均在Givewin2.3和OxMetrics3.4環境下運行,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滯后期的LL、AIC及SC的值
依表2,當滯后期為2時,LL值最大,且AIC、SC的值同時達到最小,故模型滯后期為2。
再確定MS-VAR模型的區制個數。從圖1來看,各變量均表現為在部分年份波幅較大,其余年份波幅較小,且RM2、RP、RC均存在上升與下降兩種狀態,結合本文研究內容,將選擇模型的區制個數為2。再依據LL、AIC、SC、HQ等指標綜合比較MSM-VAR、MSI-VAR、MSA-VAR、MSMH-VAR、MSIH-VAR及MSIAH-VAR等不同形式模型的擬合效果,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形式的選擇
由表3可見,模型MSIH-VAR的LL值雖小于模型MSIAH-VAR,但其他AIC等指標均較之更優,且多數指標也優于線性VAR模型,又考慮到不同模型下系數的顯著性,MSIH-VAR模型下多數系數顯著,說明該模型擬合效果較好,故采用MSIH(2)-VAR(2)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2 基于MSIH(2)-VAR(2)模型的實證分析
2.1 模型估計結果
基于前述分析,對RM2、RP、RC構建MSIH(2)-VAR(2)模型并進行參數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MSIH-VAR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
首先從三個方程的系數來看,系數大多在1%或5%的水平上顯著,模型擬合良好。再從兩區制下截距項來看,區制1下截距項多不顯著,區制2下截距項均顯著,意味著區制2下各變量當期值分別受滯后期值的影響較區制1大;又考慮到區制2下標準差均大于區制1,故區制1表示貨幣供應和房價波動較為平緩的經濟狀態,區制2表示二者波動較為劇烈的經濟狀態。
從RM2方程來看,貨幣供應具有明顯“慣性”,即受其滯后期值的影響較大。每單位滯后1期RM2的變動將帶來1.0619個單位當期值的同向變動,每單位滯后2期RM2的變動將帶來0.3290個單位當期值的反向變動,但綜合來看,前期貨幣供應對當期值影響為正。此外,滯后1期房價變動對當期RM2影響為負,滯后2期房價變動對當期RM2影響為正,但前期房價變動對當期貨幣供應的最終影響無法確定,或意味著房價上漲過快,政府部門將傾向于采取偏緊縮的貨幣政策,反之則采取略寬松的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還受除房價外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故滯后期RP對當期RM2的最終影響并不確定。另外,滯后期RC的系數不顯著,前期RC對當期RM2的影響無法判斷。
從RP方程來看,房價變動同樣具有“慣性”,滯后期房價對當期值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在“慣性”作用下,通過貨幣供應精準調控房價走勢較為困難。另外,當前房價還與前期貨幣供應顯著相關,滯后1期RM2每變動1單位可引起0.6160個單位RP的同向變動,意味著不斷增加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或是房價攀升的重要因素。前期RC與當期RP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說明前期居民消費增加對其當期住房消費具有“擠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價上漲。
最后從RC方程來看,滯后1期RM2與當期RC間存在正向關系,滯后2期RM2與當期RC間存在反向關系,滯后期RM2對當期RC的最終影響無法確定。類似的還有房價與消費間的關系,滯后1期房價的上漲將“擠出”當期消費;滯后2期房價的上漲將拉動當期消費,當期消費受前兩期房價變動的共同影響。
2.2 兩區制特征
2.2.1 兩區制的劃分
圖2分別表示區制1和區制2的估計概率。由圖2可知,處于兩區制下的樣本數量相當,說明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貨幣供應、房價波動較為劇烈的情況時有發生,變量在波動平緩與劇烈的兩種經濟狀態下頻繁轉換。以區制2為例,處于波動劇烈狀態下的樣本區間主要集中于2004年下半年、2005年、2007年、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年底、2012年一季度前后和2014年一季度前后,其余時期貨幣供應和房價波動較為平緩。

圖2 兩區制概率圖
從實際情況看,在實行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初房價基本保持平穩,房價明顯上漲大約始于2004年二季度,數據顯示,2004年一季度房價同比增長率僅為3.5%,而二、三季度即增至6.3%和7.4%,四季度價格在慣性作用下延續上漲態勢,但漲幅趨于平緩。正如圖2中,房價自2004年二季度進入波動較為劇烈的區制2內,四季度暫時處于波動較為平緩的區制1。為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政府于2005年3月底出臺“國八條”(《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首次調控房價,房價增速應聲而落,漲幅收窄。但貨幣供應并未收緊甚至比2004年更為寬松,M2同比增長率由2005年一季度的11.2%上漲至四季度的15.7%,寬松的貨幣供應抵消了調控政策的影響,房價在2005年三季度又掉頭向上,三、四季度房價同比增長率分別高達16.2%和17.6%。可見,2005年內貨幣供應和房價波動頻繁而劇烈,處于圖2中區制2階段。在此背景下,政府又于2006年內密集出臺各項調控措施,在一系列調控組合拳下,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逐步降溫,2006年一季度房價同比增長率即降為10.8%并在年內逐步下降,同時M2同比增長率也由一季度的16.1%逐漸降至四季度的12.4%,可見2006年貨幣供應、房價波動較為平緩。2007年里央行延續了前期偏緊的貨幣政策,M2同比增長率繼續下調,年內進行了5次加息、10次提高準備金率,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房價卻再次出現過熱勢頭,尤其是一線城市前期被壓抑的購房需求出現反彈,房價“報復性上漲”。9月政府規定二套住房首付不低于40%,利率不低于基準利率1.1倍,12月擴大外商投資房地產業的限制范圍,調控效果才逐漸顯現,全國房價于2007年四季度趨于平緩。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房地產市場步入低谷,前三季度貨幣供應與房價波動平緩且均處于較低水平。第四季度為擴大內需開始降準降息、降低交易稅費、并推出“4萬億計劃”,M2同比增長率大幅提高,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M2平均季度同比增長率約為26.1%,一系列刺激政策再次助推房價上漲,2009年內房價同比增長率約為18.3%,貨幣供應與房價再次位于波動劇烈的區制2內。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二套房首付比例由不低于40%提高至60%,三套以上住房暫停發放商業貸款,上海和重慶地區進行房產稅試點,各地紛紛出臺限購政策,2009年寬松的貨幣政策逐漸收緊,樓市隨之逐步降溫。2011年內房價增速雖保持平穩,貨幣政策卻前緊后松。2011年1月至7月,央行加息3次,上調存準率6次,而11月又開始下調存準率,2011年四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連續2次降息,3次降準,貨幣供應與房價再次位于區制2內。2013年繼續嚴格執行商品房限購措施,M2同比增速保持在10%左右,年內貨幣供應與房價較為平穩。在各地嚴格的限購、限貸政策下,全國整體房價大約于2014年初迎來拐點,一季度房價同比增速由正轉負,房價下跌,當年內貨幣供應與房價在較低水平上保持穩定。而在房價整體平穩的背后,各地商品房供求冷熱不均又成為2014年樓市的新特點,針對這一現象政府提出“雙向調控”,即一方面抑制熱點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另一方面關注部分三、四線城市高庫存風險和壓力。在這一指導思想下,部分城市于2014年下半年陸續放開限購,執行差異化的房貸政策。2015年在降息、降準、個人轉讓兩年以上住房免征營業稅等利好下,二季度房價再次迎來拐點,其價格同比增速又由負轉正,房價再次進入上漲通道。由圖2可見,2015年僅二季度位于區制2,該季度房價由跌轉漲,波動明顯,而該年內其余時間及2016年均位于區制1內。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房價平穩位于區制1內的實證結果與實際感受并不相符,據《2017中國高凈值客戶海外置業展望》報道,2016年全球房價年度漲幅前十均為中國大陸城市,如合肥、廈門、深圳、上海等地漲幅分別達到48.4%、45.5%、31.7%和31.1%,其主要原因為自2014年后我國房地產市場明顯分化、冷熱不均,且這種趨勢近年來不斷加大。城鎮化進程中,資金、人口等資源不斷涌向大城市,部分城市商品房供不應求,而三、四線城市庫存高企,房價疲軟,故房價整體平穩的背后是城市間房地產市場出現結構性分化。2016年下半年政府開始因城施策,對熱點城市的調控不斷加碼,而對三四線城市加快去庫存。
2.2.2 各區制間轉換概率及特征
由表5可知系統維持在區制1和區制2的概率分別為67.63%和67.95%;由區制1轉向區制2的概率為32.37%,由區制2轉向區制1的概率為32.05%。說明系統無論處于區制1還是區制2狀態,都將大概率地維持該狀態,發生區制轉換的概率相對較小。這意味著市場發展具有慣性,無論處于貨幣與房價波動平緩還是波動劇烈時期,都將在該時期持續一段時期,且在兩區制間轉換的概率相當。正由于市場發展慣性和政策滯后性的影響,使得精準調控房地產市場并非易事。

表5 各區制間的轉換概率
又由表6可見,研究期間內,系統有49.75%的時期處于區制1,平均持續期為3.09個季度;有50.25%的時期處于區制2,平均持續期為3.12個季度。這說明我國房地產市場處于區制1和區制2的時間相當,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貨幣供應與房價劇烈波動時有發生。

表6 兩區制特征
2.3 脈沖響應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廣義貨幣供應對房價、以及房價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具體影響方式,以下分別進行脈沖響應分析。
圖3為兩區制下RP對RM2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兩種狀態下,RP對RM2沖擊的響應趨勢基本相同。給定RM2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RP在初期具有明顯的正向響應,大約在第2期達最大值,隨后正向響應幅度逐漸縮小并在第10期變為負向響應,最終收斂于第25期前后。但兩區制下,RP對RM2沖擊的響應程度不同,區制2下RP的響應程度遠大于區制1,說明當貨幣與房價變量劇烈波動時,房價更易受貨幣供應的影響。

圖3 兩區制下RP對RM2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
圖4為兩區制下RC對RP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兩區制下,RC對RP變動的響應趨勢和響應程度基本相同。給定RP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RC先作出負向響應,隨后響應程度逐漸減弱,約于第5期轉變為正向響應,并最終收斂于20期。兩區制下,RC對RP沖擊的響應程度無明顯區別。說明房價上漲前期,居民購房成本增大不得不縮減開支,故前期房價上漲對居民消費主要體現為“擠出效應”,而隨房價的持續上漲,由此帶來的“財富效應”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故隨后又帶來居民消費支出的增加。從響應幅度來看,負向響應幅度遠大于正向響應,說明我國房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整體上要大于“財富效應”。此外,消費本身具有慣性,當前房價和財富的波動無法立即反應在當前消費中,故兩區制下RC對RP變動的響應方式和響應程度無明顯區別。

圖4 兩區制下RC對RP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
3 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MSIH(2)-VAR(2)模型,實證分析了我國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不同經濟狀態下貨幣、房價和居民消費支出間的動態關系,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房價波動較為頻繁而劇烈,且整體上漲明顯。政府通過利率、準備金率、購房資格等調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對房價劇烈波動起到了抑制作用,而房價在兩區制間的頻繁轉換也說明調控效果具有短期性,未能形成穩定房價的長效機制。此外,2014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地區分化現象明顯,全國均價雖略有下跌,但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上漲明顯,而其他城市庫存高企、房價下跌。這意味著對于我國房地產市場需分類調控、因城施策。
(2)實際M2從22.2萬億元增至106.3萬億元,增幅約378.8%;同期全國商品房實際均價由2564.1元/平米上漲至5127.3元/平米,增幅約100%。房價的劇烈波動往往伴隨著M2的劇烈波動,意味著建立穩定房價的長效機制的關鍵在于穩定貨幣發行及合理控制資金流向房地產領域。而前期房價變動對當期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確定,滯后1期房價變動對當期消費主要表現為“擠出效應”,滯后2期主要表現為“財富效應”,故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較為復雜,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不同特征的家庭,從而最終表現為正向或負向影響。
(3)經濟系統無論處于何區制內,均有維持原狀態的趨勢,發生區制轉換的概率較小。這意味著經濟變量劇烈波動時,政府通過調控使其短期內回到平穩狀態具有一定難度;當系統處于平穩狀態時,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穩定住貨幣發行和房價,此時的政策效果較為有效。
(4)從脈沖響應結果來看,兩區制下變量對沖擊的響應趨勢基本相同,但在系統劇烈波動狀態下,廣義貨幣供應變動對房價的影響程度明顯強于平穩狀態。即非平穩狀態下,系統具有放大沖擊的內在機制,因而政府有必要通過穩定貨幣發行、嚴控土地和商品房炒作等一系列手段建立穩定房價的長效機制,防止出現大起大落。而兩區制下,房價變動對消費的影響程度基本差別不大,說明居民消費有其特有的響應方式,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與所處經濟狀態關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