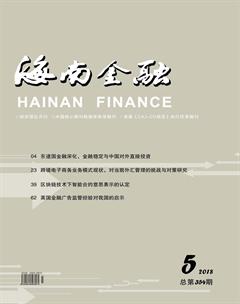雙峰監管:理論起源、演進及英國監管改革實踐
賈曉雯

摘 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雙峰監管模式因其內在的獨特優勢及在危機考驗下的良好表現,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青睞并得到廣泛應用,逐漸成為國際上金融監管體制的主流。我國在近期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中同樣借鑒了雙峰監管模式,在優化監管機構設置的同時監管目標也更加清晰明確。本文擬從雙峰監管的理論分析角度入手,并結合英國兩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實踐的經驗教訓,以期對我國下一階段的金融監管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鑒。
關鍵詞:雙峰監管;宏觀審慎;微觀審慎;行為監管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8.05.09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8)05-0069-06
一、 雙峰監管理論起源
(一)產生背景
英國在20世紀90年代前長期實行分業監管,即根據被監管對象的機構類型作為監管劃分依據,分別由對應的監管機構實施監管。隨著英國金融體系復雜化程度的顯著提升及各類型金融機構規模的快速擴張,金融領域開始出現了一系列新變化:混業經營模式形成,金融控股集團初現雛形,跨行業、跨市場的業務活動不斷涌現,不同類型機構及市場間的界限開始模糊;隨著保險、證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及衍生品市場的加速崛起,商業銀行不再是系統性風險的單一來源;金融產品及服務日益多元化、復雜化、專業化,消費者與金融機構間的信息鴻溝急劇加深,金融市場更加不透明。英國金融體系所出現的上述變化導致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并爆發了諸多風險事件,如巴林銀行因衍生品投機失敗而破產、國際信貸商業銀行因金融欺詐而破產等。
不斷產生的風險事件表明英國原有的分業監管體制與日益復雜、混業化的金融體系不相協調、不相適應。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國經濟學教授Micheal Taylor于1995提出了雙峰監管理論,以期重塑監管理念并為英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指明方向。
(二)理論主要內容
1.關于監管目標。雙峰監管理論以目標導向為原則,認為有效的金融監管應當致力于兩大目標的實現:一是系統性保護目標,即通過實施審慎監管確保金融機構經營穩健,維護金融穩定;二是消費者保護目標,即通過實施行為監管確保消費者在金融交易中被公平地對待,免受欺詐、不充分競爭及市場濫用等不當行為的侵害。
2.關于雙峰間的關系。兩大監管目標之間存在一致性:一方面,有效的審慎監管能夠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營,防止機構因資產質量惡化或流動性不足而導致經營失敗,使金融消費者免于蒙受重大損失;另一方面,有效的行為監管能夠及時對問題金融產品及不當金融交易行為進行干預,提振消費者對金融市場的信心,有助于金融穩定的實現。
同時,由于二者存在諸多差異,會導致出現目標沖突:一是立場沖突。前者著眼于金融機構的利益,后者著眼于金融消費者的利益,由于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是作為交易對手而存在,這決定了雙方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進而導致不同監管目標的沖突。二是文化沖突。行為監管的工作性質決定其監管人員構成主要為律師和會計師,而審慎監管則更多地需要經濟學家和風險管理專家,監管人員的職業文化及分析視角存在沖突。三是利益沖突。行為監管能夠及時叫停問題金融產品的發售,遏制欺詐交易行為,防止金融機構對消費者進行利益掠奪,并對其不當行為采取嚴厲監管措施,但同時也會影響金融機構的短期盈利水平,造成審慎監管指標的急劇惡化。
3.關于監管機構設置。如果由單一監管機構同時承擔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這兩種職能,往往會導致出現“擠出效應”,對不同監管目標厚此薄彼、顧此失彼,影響監管的有效性。因此,應根據不同監管目標設立兩個相互獨立的監管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與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分別負責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以消除“一身二任”所導致的內在沖突,進一步提高監管專業性。其中,金融穩定委員會負責對包括商業銀行、證券、保險公司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統一實施審慎監管,以適應金融混業經營的現實情況;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負責對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實施行為監管,確保機構的合規經營及金融市場的公平誠信。
4.關于監管協調機制安排。一方面,若金融穩定委員會獨立于央行,則意味著央行原有的銀行監管職能將被剝離,在此情況下,金融穩定委員會必須同央行保持緊密合作,便于央行及時獲取風險信息,更好地履行貨幣政策及最后貸款人等職能。另一方面,鑒于金融穩定委員會及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間存在著目標沖突,雙方需要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也可考慮建立起更高層級的監管協調機制。
二、雙峰監管理論的演進
(一)理論演進的背景
金融監管理論及監管模式的確立必須以一國金融體系的現實情況為基礎,當該基礎發生顯著變化時,金融監管理論必須隨之作出適應性的調整。Taylor首次提出雙峰監管理論后的10多年中,英國的金融體系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如規模巨大、具有高度關聯性的金融機構不斷涌現,高杠桿型金融交易業務盛行,金融風險交織程度加深且風險傳播進一步加速等。金融體系的上述變化加劇了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如何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統性風險成為重塑金融監管體制時的突出考量因素。
(二)主要變化
基于對英國金融體系新特點的認識,Taylor于2009年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基礎之上,對雙峰監管的內容做出了進一步的豐富完善,以更好地適應現實需求,并對英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再次獻言。
在新的理論體系下,明確了雙峰監管與六大監管功能的對應關系,其主要結構關系總結如下(見圖1)。
1.系統性保護目標主要通過以下三種監管功能的有效發揮得以實現:(1)宏觀審慎管理。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會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問題的出現,即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不一定能夠帶來金融體系的穩健。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并且該種不穩定性隨著金融創新活動增多、金融機構規模擴大、金融體系復雜性增強等日益加強,這就要求央行從全局視角來看待金融體系及金融風險,即通過宏觀審慎管理保障金融穩定。(2)危機管理機制。危機管理機制主要包括對問題金融機構的救助及破產清算安排兩方面內容。當金融機構陷入困境時,央行需決定是否行使最后貸款人或緊急流動性救助職能,并確定相應的抵押品;對破產機構進行有序清算,避免機構破產對金融體系造成過度擾動。(3)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當金融機構規模過大或與金融體系具有高度關聯性時,其經營失敗將會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產生。因此,對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應當實施更為嚴格的審慎監管,設置更高的資本、流動性等監管要求。
2.消費者保護目標主要通過以下三種監管功能的有效發揮得以實現:(1)經營行為監管。通過對金融機構零售業務行為進行監管,提高交易過程的透明度,使風險信息及收費情況得到充分的披露,確保消費者得到公平的對待。(2)市場行為監管。通過對市場行為進行監管確保金融市場的透明及公平,保護投資者利益,主要措施可包括制定上市標準、提高信息披露要求、打擊市場操縱及內幕交易等。(3)對中小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Taylor認為隨著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不斷涌現,在審慎監管方面應采取“抓大放小”原則,即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重點監管并實施更嚴格的監管標準,以防范系統性風險;而中小金融機構的經營失敗一般并不會對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沖擊,對其進行審慎監管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其對消費者具有持續的履約能力,避免因經營失敗而對消費者利益造成損害。
三、 英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兩次改革
(一)第一階段:從分業監管向單一監管的轉變
1997年之前,英國長期實行分業監管。英格蘭銀行(央行)負責對商業銀行實施審慎監管,住房儲蓄委員會負責對住房儲蓄機構實施審慎監管,貿易與工業部負責對保險公司實施清償能力監管,證券投資委員會指導下的眾多自律組織,如證券業協會、期貨中介及交易商協會等,負責對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進行自律性監管。隨著混業經營的不斷發展,這種碎片化、目標不清晰的監管體制的弊端逐漸顯現,監管體制亟待改革。
1997年,英國政府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大幅改革,其主要舉措如下:(1)設立單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負責對金融業進行綜合監管,并同時身兼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這兩大職能;(2)將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剝離并由FSA承接,以進一步提升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3)財政部負責確立金融監管框架及相關立法,牽頭負責對問題金融機構的救助。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到,Taylor于1995年提出的雙峰監管理論并未被采納,此次改革存在著“先天不足”,如FSA監管目標及職責分工劃分不清晰,央行與財政部、FSA之間缺乏日常合作與協調等。這種“先天不足”為英國金融監管的再次失敗埋下了隱患。
(二)單一監管體制失敗的原因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英國經改革及強化過的金融監管體制并未能成功抵御住風險的沖擊,金融體系再次受到重創,尤其是以北巖銀行擠兌為代表的一系列風險事件使英國監管體制的內在缺陷及不足暴露地一覽無余。該次危機的發生側面印證了雙峰監管理論的預見性,并可從中得出如下教訓:
1.系統性保護及消費者保護二者間沖突大于協調,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當初成立FSA的支持者們認為不同監管目標間存在著較強的協同效應,單一監管機構有助于減少重復監管,提高監管效率。金融危機的發生卻證明了單一監管機構在面對過多監管目標及監管任務時往往會顧此失彼,如危機前FSA就消費者保護問題與北巖銀行進行了頻繁的監管溝通,但是對于其資本、流動性及期限錯配的關注遠遠不足,每三年才會同其召開一次主要的審慎監管會議。
2.需要明確央行的金融穩定職能,并賦予其相應的權責及工具。1997年監管體制改革后,央行的微觀審慎監管職能被剝離,但并未從法律層面明確其是否承擔金融穩定職能,即從宏觀視角監測整個金融體系并識別可能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因素。在危機管理方面,財政部負責牽頭對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置,央行處于附屬地位,無法在風險暴露后及時介入并實施救助,限制了其最后貸款人職能的有效發揮。
3.央行與FSA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及協調。在監管協調機制方面,僅通過簽訂備忘錄的形式建立起一個松散的三方會談機制,但是該機制幾乎未發揮任何作用,央行與FSA之間未能就信息共享、政策協調、危機管理等工作開展有效合作,作為最后貸款人的央行不掌握具體監管信息,導致金融監管的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之間嚴重割裂。
(三)第二階段:從單一監管向雙峰監管的轉變
吸取上次危機的教訓,英國此次采納了Taylor提出的改革建議,先后通過《2009年銀行法案》《2012年金融服務法案》及《2016年英格蘭銀行與金融服務法案》,對原有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由單一監管模式向雙峰監管模式轉變。此次改革旨在強化央行宏觀審慎管理職能、拆分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職能、加強監管統籌及協調。
1.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并對單一監管機構的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兩大職能進行拆分,作為“第一峰”的系統性保護目標及其對應的三大監管功能由央行統籌負責。
(1)強化宏觀審慎管理。明確央行的宏觀審慎管理職責,在其理事會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負責識別、監測系統性風險并采取行動降低該種風險,以提升英國金融體系的韌性,維護金融穩定。金融政策委員會具有以下權力:一是指令權,包括制定逆周期資本緩沖要求、特定行業的資本要求、杠桿率要求、抵押貸款中的貸款-價值比率(LTV)等。二是建議權,建議其他監管部門采取措施以維護金融穩定。
同時,金融政策委員會還負責配合政府經濟政策的實施,以促進就業并維持經濟增長。為了明晰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之間的界限,金融政策委員會只在宏觀層面統籌實施金融穩定決策,由相關監管機構協助落實,其并不直接負責微觀層面的監管執行。
(2)危機管理機制。在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系統化的危機管理制度,英國未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和化解危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針對這一問題,英國建立起了危機管理的法律制度,主要由特別應對機制、銀行接管和銀行破產三部分構成,明確了財政部、央行和監管部門三方各自的職責及協調機制,重點強化了央行在危機管理方面的職責,并賦予其對系統重要性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權。
(3)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改革后,英國撤消了單一監管機構FSA,并對其原有職能進行拆分,分別由新設立的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進行承接。PRA為央行內設部門,負責對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實施審慎監管,包括1500余家商業銀行、住房儲蓄機構、投資公司及保險公司等。
2.作為“第二峰”的消費者保護目標及其對應的三大監管功能由FCA負責。新成立的FCA直接對英國財政部和議會負責,其致力于確保金融市場的良性運轉并具有三大核心操作目標:(1)確保對金融消費者進行適度保護;(2)保護并提升英國金融體系的公平誠信度;(3)促進利于金融消費者的市場競爭。
FCA具有三大監管功能:(1)對56000多家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及消費者保護進行監管;(2)對金融市場行為進行監管;(3)對PRA監管范圍之外的18000多家中小型金融機構實施審慎監管。
3.在監管協調機制安排方面,為加強宏觀審慎、微觀審慎及行為監管間的協同,新的監管體制在數據共享、交叉任職、雙重監管、爭端解決等方面建立起了全方位的協調機制,以降低監管沖突及摩擦,提高監管效率。如金融政策委員會與PRA同在央行內部,利于實現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之間的協調統一;金融政策委員會有權對PRA與FCA進行指導并提出建議,且在二者之間出現沖突時充當“仲裁人”。
四、對我國的啟示
(一)重構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的關系
基于目標導向的雙峰監管強調應根據不同的監管目標設置監管機構并清晰劃分職責,其在理論層面論證了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存在著潛在沖突,而“一身二任”的FSA則從實踐層面證明了該種沖突會導致監管失敗。我國監管部門集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職能于一身,由于審慎監管在我國起步較早,理論體系和監管實踐等均已較為成熟,所以其在影響力方面占優,行為監管處于附屬地位。這導致了我國對行為風險及金融消費者保護的重視程度不足,相關風險隱患不容小覷。因此在現有監管體制下,如何重塑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并重的理念并提高行為監管的獨立性,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二)強化人民銀行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
央行在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應處于核心地位。英國1997年金融改革對央行進行了大幅“削權”,分離了其對銀行業的監管職能,但并未賦予其相應的職責和工具來維護金融穩定,導致了央行在隨后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時的無力。上述事實證明必須明確賦予人民銀行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強化宏觀審慎管理,科學配置管理工具,指導相關監管部門做好系統性風險防范工作。
同時,根據近日確定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原銀監會及保監會擬定設立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性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人民銀行。該舉措有利于微觀審慎監管政策同宏觀審慎管理的協調統一,但由于我國人民銀行并不承擔微觀審慎監管職能,還需要加強監管合作,實現立法環節與執法環節的有機結合,并明確劃分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之間的界限,防止出現交叉及沖突。
(三)加強監管協調機制建設
由于不同的監管目標及監管功能可能存在潛在的沖突,客觀上要求各監管機構間充分共享信息,形成高效的監管溝通協調安排,并建立明確的爭端解決及決策機制,促進監管協同及監管效率的提升。應確保新設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充分發揮監管溝通及協調的平臺作用,并對相關監管部門無法達成一致的重大事項進行決議,切實提升金融監管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參考文獻:
[1]黃志強.英國金融監管改革新架構及其啟示[J].國際金融研究,2012(5):19-25.
[2]劉鵬.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危機后行為監管的發展與加強[J].上海金融,2014(4):71-77.
[3]史煒,瞿亢,侯振博.英國金融統一監管的經驗以及對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建議[J].國際金融,2016(7):3-9.
[4]孫天琦.金融業行為風險、行為監管與金融消費者保護[J].西部金融,2016(1):4-14.
[5]Taylor M.“Twin Peaks”: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M].London: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inancial Innovation,1995.
[6]Taylor M.The Road from“Twin Peaks”and the Way Back[J].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2009(16):61-96.
[7]伍曉雯.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的比較研究[J].海南金融,2016(1):50-54.
[8]王敏.“雙峰監管”模式的發展及對中國的啟示[J].陜西行政學院學報,2016(2):82-85.
[9]張曉東.金融監管體制現代化探索:緣起、邏輯與展望[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6(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