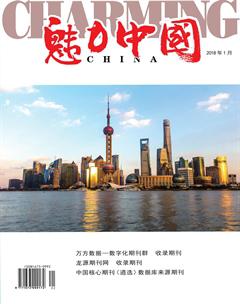淺談《詩(shī)經(jīng)》的自然意象類別
于丹
摘要:《詩(shī)經(jīng)》收集了自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三百多首詩(shī)歌,向世人們形象展現(xiàn)了周代社會(huì)生活風(fēng)貌。具體到內(nèi)容方面,詩(shī)經(jīng)可以說(shuō)是包羅萬(wàn)象,下有吟誦愛情、贊美勞動(dòng)的《風(fēng)》 ,上有宴飲歡愉、歌祖頌德的《雅》 ,還有記錄宗廟祭祀的《頌》 。其中包含的意象更是豐富多彩,本文試以意象自身性質(zhì)為劃分依據(jù),將《詩(shī)經(jīng)》中的自然意象歸為動(dòng)物意象、植物意象、氣候景物意象三類,并結(jié)合具體作品,分析《詩(shī)經(jīng)》的自然意象類別。
關(guān)鍵詞:詩(shī)經(jīng);動(dòng)物意象;植物意象;氣候景物意象
《詩(shī)經(jīng)》的時(shí)間跨度約五百年,在這段漫長(zhǎng)歷史中,華夏民族經(jīng)歷了殷商亡國(guó)、周公東征、周室衰微、諸侯興起等重大歷史變化,人們的意識(shí)形態(tài)自然也在隨之變化。具體到文學(xué)作品中,它的觀念內(nèi)容是深厚而復(fù)雜的,凝結(jié)在意象里,可以說(shuō)構(gòu)成了一個(gè)大千世界。[1]
關(guān)于《詩(shī)經(jīng)》的意象研究向來(lái)是《詩(shī)經(jīng)》研究中的重中之重。《詩(shī)經(jīng)》意象的分類也有許多不同見解,有人根據(jù)觀念內(nèi)容劃分成原始興象、比德意象、審美意象;也有說(shuō)法是根據(jù)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劃分為描述型意象、比喻型意象和象征型意象三類。本文將從意象自身出發(fā),探尋不同意象在《詩(shī)經(jīng)》中的運(yùn)用。
一、《詩(shī)經(jīng)》中的動(dòng)物意象
《詩(shī)經(jīng)》時(shí)代雖然已經(jīng)從漁獵時(shí)代進(jìn)入農(nóng)耕時(shí)代,但大家普遍對(duì)動(dòng)物的記憶依然牢固,并且蓄養(yǎng)家畜是農(nóng)耕文化的重要經(jīng)濟(jì)來(lái)源,人們有與動(dòng)物近距離接觸的機(jī)會(huì)。因此,動(dòng)物意象在《詩(shī)經(jīng)》中占據(jù)著很大的比重,涉及的動(dòng)物名稱達(dá) 115 種之多,大體可以把它們分為鳥、獸、蟲、魚、虛擬動(dòng)物五類。[2]
《詩(shī)經(jīng)》中人們對(duì)動(dòng)物意象的選擇常常與動(dòng)物自身的特征緊密聯(lián)系。例如,鴛鴦?dòng)谐呻p出現(xiàn)的特征常用來(lái)贊美男女雙方才貌匹配,愛情忠貞;大雁秋去春來(lái)用來(lái)表現(xiàn)貧民顛沛流離無(wú)處安身的悲苦;馬因?yàn)榫哂袕?qiáng)壯高貴的特點(diǎn)常用來(lái)比喻富有德行的“君子”類人物等等。下面將以《小雅·白華》來(lái)具體分析動(dòng)物意象在《詩(shī)經(jīng)》中的運(yùn)用:
“之子之遠(yuǎn),俾我獨(dú)兮”一句道出愛人已經(jīng)遠(yuǎn)去,自己獨(dú)守空房的現(xiàn)狀,奠定了全詩(shī)凄婉而讓人心寒的悲劇基調(diào)。第六章“有鹙在梁,有鶴在林” 運(yùn)用“鹙”、“鶴”兩種動(dòng)物意象,以鶴鹙失所興后妾易位。鹙,即一種頭頸無(wú)毛的水鳥,性貪惡,食魚、蛇、鳥雛等,這里可以看作是借丑陋討嫌的水鳥來(lái)暗喻勾引丈夫的妖媚女子;鶴,則是全身白色或灰色,生活在水邊,以魚、昆蟲或植物為食的一種鳥類,給人以高貴美麗的印象,因而,此處的“鶴”可以看成是女主人公的自喻。用鶴的潔白柔順與鹙的貪婪險(xiǎn)惡形成對(duì)比,一好一壞,突出“實(shí)勞我心”的不解與苦悶。
由此可以看出,《詩(shī)經(jīng)》中的動(dòng)物保留了其基本的真實(shí)性,比如外貌特征、性格特征等。人們對(duì)動(dòng)物意象的選擇、運(yùn)用往往立足于以往生活中已有的對(duì)各類動(dòng)物的喜好劃分,體現(xiàn)了主客體碰撞進(jìn)而融會(huì)的過(guò)程,使動(dòng)物在文學(xué)作品中更直接,更自然。
二、《詩(shī)經(jīng)》中的植物意象
植物意象在風(fēng)、雅和頌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國(guó)風(fēng)》部分的植物種類占據(jù)了整個(gè)《詩(shī)經(jīng)》植物總數(shù)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以大致將其分為以下九類:野菜,蔬菜,谷物,藥材,水果,花卉,樹木,纖維染料,野草。[3]
與動(dòng)物意象相比,植物意象的選取除了與其本身形態(tài)、色味等性質(zhì)有關(guān),更多的加上了一層花開花落、春去秋來(lái)的感時(shí)之情。例如,著名的《衛(wèi)風(fēng)·氓》一篇,分別以“桑之未落”和“桑之落矣”來(lái)暗示女主人公人生的兩個(gè)跨度,前者代表青春年華、后者代表年事已衰;又如《國(guó)風(fēng)·唐風(fēng)·葛生》中“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和“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兩句,描繪了墳間野草漫生,一片荒蕪的悲涼景象,可以理解成年復(fù)一年時(shí)間流轉(zhuǎn),雖然丈夫離世已久,但女子始終心系愛人。下面以《小雅·采薇》為例,進(jìn)行具體說(shuō)明:
詩(shī)歌前部分“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剛止”表面上是說(shuō)薇菜剛才長(zhǎng)出來(lái)、初生正柔嫩和已經(jīng)長(zhǎng)老了的植物生長(zhǎng)狀態(tài),實(shí)則暗示時(shí)間的不斷推移,表現(xiàn)被迫卷入戰(zhàn)爭(zhēng)之中的個(gè)人,無(wú)法把握自己命運(yùn),思家不得歸的痛苦愁緒。后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lái)思,雨雪霏霏。”運(yùn)用“楊柳”這一植物意象來(lái)寫時(shí)令,形象生動(dòng)地寫出征役時(shí)間之長(zhǎng),也暗含戰(zhàn)爭(zhēng)環(huán)境嚴(yán)酷和征役之苦。
植物意象在《詩(shī)經(jīng)》中的運(yùn)用既起到了比興、象征等修辭意義,同時(shí)兼具點(diǎn)明時(shí)間,表現(xiàn)歲月流逝的內(nèi)容意義,從而很大程度上豐富了《詩(shī)經(jīng)》的情感表達(dá)方式,能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詩(shī)歌情感。
三、《詩(shī)經(jīng)》中的氣候景物意象
山、水、云、風(fēng)、雨這些自然景物也是《詩(shī)經(jīng)》中常常出現(xiàn)的自然意象,本文將它們劃歸到氣候景物這一類別。相比動(dòng)物意象和植物意象,氣候景物意象有著更為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先秦時(shí)期,社會(huì)生產(chǎn)力低下,人們對(duì)待自然往往是一種既尊敬又害怕的態(tài)度,再加上中國(guó)自古就有的上神崇拜觀念,此類意象往往用作暗示災(zāi)難和祈求祭祀。
如《大雅·桑柔》一詩(shī),這是一首勸諫詩(shī),諷刺周厲王暴虐昏庸,任用非人,最終導(dǎo)致政治混亂。詩(shī)中“大風(fēng)有隧,有空大谷”和“大風(fēng)有隧,貪人敗類”兩句便是運(yùn)用了“風(fēng)”氣候景物意象,以此起興,既象征貪利卑鄙的群臣,也暗示著即將到來(lái)的社會(huì)災(zāi)難,深刻諷刺了厲王偏愛阿諛?lè)畛兴脑捳Z(yǔ),而聽到忠諫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進(jìn)獻(xiàn)忠言的人為狂悖,最終國(guó)家將面臨危亡的結(jié)局。
先秦時(shí)期,農(nóng)業(yè)勞作占據(jù)人民生活的很大比重,“靠天吃飯”導(dǎo)致人們對(duì)雨神有濃濃的尊敬、愛戴之情,因此“雨”這一意象往往表示出一種喜悅之情。如《小雅·信南山》這首周王祭祖祈福的樂(lè)歌中,“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yōu)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描寫了冬天陰云密布,雪花紛紛墜落,再加上細(xì)雨濛濛的圖景,表現(xiàn)出人民渴望天降雨雪,滋潤(rùn)莊稼的美好愿望。
四、結(jié)束語(yǔ)
《詩(shī)經(jīng)》作為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代表了中華文化特定發(fā)展時(shí)期的文化呈現(xiàn)方式。對(duì)《詩(shī)經(jīng)》進(jìn)行深入研究既是一種文化繼承方式,也是一種文化發(fā)展途徑,具有維護(hù)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延續(xù)性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孫伯涵. 《詩(shī)經(jīng)》意象論[J]. 煙臺(tái)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01, 卷缺失(2): 27-33
[2]丁晨. 《詩(shī)經(jīng)》中的動(dòng)物意象[D]. [出版地不詳]: 蘇州大學(xué), 2006
[3]李亞丹. 《詩(shī)經(jīng)·國(guó)風(fēng)》植物意象研究[D]. [出版地不詳]: 陜西理工學(xué)院,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