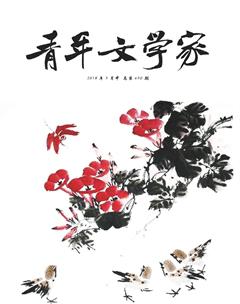“暗夜的獨行者”
摘 要:《野草在歌唱》是英國著名作家多麗絲·萊辛的作品。小說的女主人公瑪麗是“暗夜的獨行者”,在經歷了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和諧后,不堪忍受閑言碎語,她又走向了失敗的婚姻生活。面對著懦弱無能的丈夫,黑人仆人的曖昧言行,她困囿于自己的內心世界,在深深的焦慮中惶惶度日。這特殊的個人成長環境和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為瑪麗的悲劇染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最后瑪麗終于勇敢地正視自己內心的情感需求,選擇走向死亡,卻恰恰是其通往黎明的選擇,正像野草生生不息,綿延希望。
關鍵詞:瑪麗;焦慮;神經癥人格;防御策略
作者簡介:劉立爽,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4--03
前言:
多麗絲·萊辛(1919-2013)是享譽世界的英國當代女作家。她的作品深入反映了上個世紀以來人類在思想、情感以及文化上的轉變,被譽為20世紀少數擁有接觸心靈的西方小說家。萊辛以其卓越的文學成就于2007年成為第十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作家。《野草在歌唱》是萊辛的處女作,該書自1950年一經出版就得到評論界的高度關注。小說以倒敘的手法從非洲農場主妻子瑪麗被其黑人男仆殺害展開,給讀者詳盡展現了瑪麗悲劇的一生。在故事的行進中,20世紀中期英國殖民統治下南部非洲的社會現狀也在緩緩揭露。
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及精神病學家卡倫.霍妮是精神分析學說中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社會心理學的最早倡導者之一。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為精神分析提供了新的方向,其理論也被廣泛應用于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中闡釋到:“神經癥乃是一種由恐懼,由對抗這些恐懼的防御措施,由為了緩和內在沖突而尋求妥協解決的種種努力所導致的種種心理紊亂。從實際角度考慮,只有當這種心理紊亂偏離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們才應該將它叫做神經癥。”《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瑪麗就是典型的神經癥人格,她常常處于無意識的焦慮中,不會運用正確的人際關系策略與他人相處,最后防御策略失敗,走上了自我異化的道路。她就像“暗夜的獨行者”,在微光中踽踽前行.霍妮談及,當人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需求,在真實的感情和信念的基礎上與他人相處,才能改變自身的狀態。小說的最后,瑪麗終于勇敢地正視自己的內心,選擇死亡,但這恰恰是走向希望的坦途,那是通往黎明的必經之路。本文基于霍妮的理論,從社會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兩方面入手,探析瑪麗焦慮的產生,以及其無意識地應用錯誤的防御策略,最終直面真我的過程。
一.瑪麗焦慮的探析
(一)個人環境。瑪麗的童年生活于她而言是困苦的噩夢,并在其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瑪麗一家居住在落后閉塞的鄉鎮,她有一對感情冷漠的父母。父親終日飲酒,而母親惱恨起來,就跑去父親喝酒的小店抱怨家用入不敷出,只不過為了鬧一場,出出氣,“被荒唐的酒客同情她才得意.”母親常常對父親冷漠以對,她對父親“侮辱性的嘲笑”是要保留到朋友來家里喝茶時才發泄出來。瑪麗從小被母親視作心腹,在母親終日的嘮叨抱怨下,瑪麗也漸漸開始憎恨父親。霍妮認為,兒童的健康成長需要一個“溫暖的氛圍”,而家庭是兒童得到這種氛圍最重要,最基本的環境。但是,父母由于自身的原因無法使孩子體驗到安全感,不良的撫養方式使兒童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兒童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使其在內心產生一種排斥父母的力量;但又因其弱小,渴望得到父母的保護與關愛,這就是兒童內心的基本沖突,而沖突得不到解決必然產生焦慮。瑪麗的家庭環境導致她得不到基本滿足感與安全感,父母的狀況讓她對男性與婚姻產生了本能的抗拒,這為她今后走向失敗的婚姻埋下了伏筆。而從父母那繼承來的仇視黑人的教育,也在其今后的人生中不斷困擾著她。
當瑪麗終于走進寄宿學校,遠離家庭,走入社會后,她確實度過了一段開心的日子,尤其在母親父親相繼去世后,但這樣的狀況也僅僅維持到30歲,她依然維持著少女的梳妝打扮,“瑪麗喜歡別人的孩子,但是一想到自己生孩子,就心驚膽戰。看到人家結婚,她就覺得傷感,可是她又很討厭男女關系……有時候她的確感到不安,感到一種隱隱約約的不滿”。當瑪麗偷聽到朋友談論自己時,心底隱隱的不安終于泛濫,她開始變得沉悶,懶散甚至有些精神失常。她迫不及待地希望找到個男朋友結婚,擺脫現在的窘狀,但內心深處地排斥又不時折磨著她,倉皇間她選擇了迪克,一個亟需家庭溫暖又懦弱無能的農場主。但婚后的農場生活,非但沒有減輕瑪麗內心的焦慮,反倒加劇了其內心的沖突。瑪麗選擇遠離朋友的風言風語來到農場生活,貌似暫時尋求到了解脫,但簡陋悶熱的居住環境,金錢的拮據,以及要與黑仆人打交道讓瑪麗走進了更深的焦慮的漩渦。
(二)社會環境。故事發生于20世紀40年代末期,南部非洲的羅得西亞,當時南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可以預見在南非南部這片廣袤的草原上,種族隔離是必然事件。這里不僅充斥著種族歧視的焰火,白人之間也存在著比較。對瑪麗而言,帶著思鄉情調說出的“祖國”,指的就是英格蘭,盡管她的雙親都是南非人,也從未曾到英格蘭去過。由此可見,瑪麗在這個社會,是缺少歸屬感的。她心心念念的祖國是英格蘭,但是她甚至連它是什么樣的都不知道,她又討厭自己的成長環境及婚后的居住環境,這種缺失的歸屬感也在無行中加劇了她的焦慮。而與黑人奴仆摩西之間的感情羈絆,更是讓她在社會道德的衡量標準下惶惶不安。“白人文明”絕不允許白人,尤其是白種女人與黑人發生任何關系。而瑪麗自小接受的教育也從不把黑人當作“人”看。但在與摩西的接觸中,她不斷被其吸引,對黑人開始有了新的認識,這與她所接受的主流價值觀相悖。瑪麗一面希望自己遠離摩西的吸引,一面又不可控制的走向摩西,在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她恐懼著,焦慮著,甚至最后走向了自我異化的過程。瑪麗把自己關在鐵皮屋內,在這個狹小的世界里,她不用理會外人的目光,把自己抽離出去,混混噩噩,精神衰竭,在焦慮的折磨下病態的生活著。
二.瑪麗的防御策略
霍妮在《我們內心的沖突》一書中,把人際關系策略分為三類:親近人,對抗人以及回避人。這三種態度應該是相互補充,和諧統一的,但神經癥患者不能靈活應對外界,要么屈從,要么對抗,要么逃避,而不管這一行為在具體的情況下是否適當。因此,在實際情境中,神經癥患者,往往會強調其中一種人際關系策略使其成為主導傾向,而這恰恰并不能減輕內心的沖突,甚至會加重焦慮。瑪麗在不同的階段,使不同的人際關系策略占據主導地位,不能靈活的運用人際關系策略,終究擺脫不掉焦慮的困擾.
(一)親近人
十六歲時,瑪麗離開了學校,在城里的一個公司找到了工作。她開始了如魚得水的生活。這里沒有冷漠頭疼的吵鬧,她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也結交上了朋友,她喜歡這里人與人之間那種友好而又互不干涉的氛圍。在城里生活的這段日子,瑪麗主要采用了親近人的人際關系策略,表現為屈從型人格特點,即對親近的渴求,對歸屬的渴求。以親近人為主導傾向的人表現為善良,謙恭,有愛心,竭力避免不合等有沖突的人際關系。他們強烈依賴他人,特別需要感情和認同,尤其是來自伙伴的。瑪麗薪金可觀,如果想居住公寓房子,也完全可以,但是她卻住在女子俱樂部里--為收入較差的女子創辦的。她喜歡居住在這里,這能使她回想起學校的生活,她也喜歡這一群群姑娘。在女子公寓里,瑪麗是有些威信的,總有朋友待在她的房間等著和她聊會天,大家也都向她傾訴煩惱。瑪麗從不會做出大驚小怪的樣子,也從不責備人家,不搬弄是非。瑪麗的種種表現,皆透露了其此時屈從型的人格特點,她在渴求溫暖,渴求陪伴。
(二)對抗人
匆促間結識迪克并與之結婚后,瑪麗對迪克一直采取對抗人的人際關系策略,表現為攻擊型人格特點。這種類型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充分相信,并用別人的愛慕忠誠來確認對自我的評估,把高標準強加于他人,讓別人尤其是伙伴來遵守,并在此基礎上藐視他人。面對迪克,瑪麗始終保持著優越感,在婚姻關系中常常占據著主導地位。看到迪克在其面前步步退讓,她的內心是滿足的。
瑪麗剛到農場時,不得不與黑仆人薩姆森打交道,第一次與黑人相處,瑪麗不安又無錯。在不停地挑錯中,她解雇了與迪克朝夕相伴良久的老仆人,這是迪克第一次妥協。面對迪克,瑪麗始終懷有一種優越感,她一面鄙視著迪克的懦弱無能,一面又享受著迪克在她面前的卑躬屈膝,看見迪克痛苦懊悔,瑪麗是開心的。“如果她再向迪克要求一次,向他說明天花板對她是多么重要,也許他就會軟下心來去籌錢吧?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隨隨便便去要求,使他臉上顯出那種沉悶痛苦的神情。現在她已經看慣了那種臉色。不過真正講起來,她內心里倒是很喜歡那種臉色,倒是很喜歡,非常地喜歡。每當他親切地握著她的手,柔順地吻一下,懇求地問她‘親愛的,我把你弄到這來,你恨我嗎?這時候,她總是回答道‘不,親愛的,我并不恨你。只有在這種時候,她才覺得自己是勝利者,能夠原諒他,對他表示一點情意。”當瑪麗希望給鐵皮屋的屋頂安上天花板時,她在自己的心理刻畫了迪克的反應,可見迪克常常以這種狀態面對瑪麗。迪克是一個貧窮的農場主,終日忙碌于田地,卻仍然不能盈利。他的內心渴望有個家,有妻兒,渴望家的溫暖,但是由于自身的狀況,他常常壓抑自己的想法。這時,瑪麗的出現暫時讓他找到了依托。瑪麗是城里的有穩定工作的時髦女郎,但是卻跟他結了婚,回到農場生活,自然而然,在這段關系中瑪麗是處于主導地位的。在與迪克的相處中,瑪麗充分展現了她攻擊型的人格特點,以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達到間接支配的目的。她更愿意幕后使權,正如文中描述的,瑪麗甚至幻想著自己就是“蜂后”,讓迪克身先士卒,給自己帶來美好生活。
(三)回避人
在農場生活的日子里,瑪麗把自己龜縮在小小的鐵皮屋內,采取回避人的人際關系策略,表現為孤獨型人格特點,即壓制內心的渴望避免被環境所左右,不僅逃避他人,也在逃避自己。這種類型的人,壓抑否認自己的感情和沖突達到無視沖突的目的。
瑪麗夫婦是“落落寡合”的,在當地的舞會,宴會或是運動會上從來看不到他們的身影。瑪麗夫婦從未曾理會南非社會的首要準則“社團精神”,他們在這個社會似乎是遺世獨立的。對于瑪麗而言,農場的生活于她是格格不入的。這里悶熱,處處可見不知名的草木與蟲子,灌木像是能把人淹沒,她的內心是恐懼不安的。在這樣的情境下,瑪麗把自己的內心封閉起來,疏遠他人,過起了隔離性的生活。瑪麗原是從城里的風言風語逃脫出來的,她不希望自己是別人所言的樣子,但農場的生活卻打破了她的美好期望。這里破舊困苦,是她難以忍受的,她更加不希望別人窺探到她如今的不堪。斯萊特夫人懷著真切地心情想與瑪麗交朋友,看到瑪麗把面粉袋染色做了窗簾,她由衷地夸贊瑪麗把房間布置的很美。但瑪麗心里卻氣憤得要命,表情也很僵硬,她覺得斯萊特夫人在以銳利地眼光評判這個不起眼的屋子。在之后的交往中,即使斯萊特夫人表達友好的關心,邀請瑪麗參加聚會,融入團體,瑪麗卻也會以公式化的書信回絕。她把自己超然于這個社會,采用回避人的態度,疏遠他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內心是渴望友情與關愛的,在疏遠他人的同時也在疏遠自己。
三.瑪麗的自我救贖
瑪麗把自己封閉在小小的鐵皮屋里,在與他人異化,甚至自我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她的內心時刻處于焦慮不安中,一方面抗拒與黑人傭人摩西的接觸,一方面又深受摩西的吸引。瑪麗掙扎在社會準則的邊緣,最后選擇走向摩西。她完全不再理會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精神意志抽離,假使這個鐵皮屋里的世界是和諧無爭的。直到托尼無意間撞破了她與摩西的曖昧,瑪麗猛然驚醒,她哭喊著讓摩西離開,卻在他離開后終于開始正視自己內心情感的需求。她意識到死亡的來臨,原想依靠托尼的拯救,但最終選擇了讓自己死在摩西的刀下。當瑪麗開始正視自己內心的沖突時,她的焦慮也就無所遁形,盡管解脫的代價是死亡,但瑪麗把無盡的希望留下了,種族平等的愿望在時代變遷的呼聲中越來越高!
結論: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的開創者,霍妮指出“我們的情感和心態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生活環境,取決于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如果我們未能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對個人所產生的種種影響,就不能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野草在歌唱》中主人公瑪麗就深受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影響,在焦慮不安中惶惶度日,表現了典型的神經癥人格。她就像“暗夜的獨行者”,直到敢于正視自己內心的真正情感需求,才走向黎明。盡管以生命為代價,但希望永存。
參考文獻:
[1]多麗絲·萊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2]卡倫·霍妮:精神分析新法[M].雷春林,譯.上海義藝出版社,1999.
[3]卡倫·霍妮:我們內心的沖突[M].工作虹,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
[4]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M].馮川,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