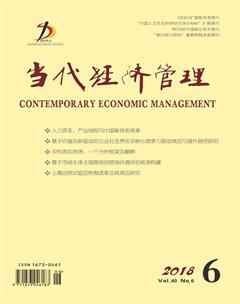經濟波動、資源配置效率與金融風險防范機制構建
賈甫
[摘 要]現有的金融風險防范理論和實踐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市場均衡是經濟的理想運行狀態,經濟波動會造成資源配置低效率。但是,從跨時期和跨地區視角來看,經濟波動可能會轉化成企業、地區乃至國家的“先發優勢”或“后發優勢”,因而是更長跨度、更大范圍內的一種資源配置機制。就此而言,經濟波動像壟斷、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一樣,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相應地,金融風險是這一基本特征的產物和表現形式。據此,文章指出了現有金融風險防范理念的誤區,并給出了可能的金融監管改革方向。
[關鍵詞]金融風險;經濟波動;擴大再生產;哈羅德-多馬模型;資源配置;金融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8)06-0086-06
一、引 言
2014年8月至2017年6月,中國經濟同時出現了四個現象。第一,外匯儲備減少。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外匯儲備減少了約1.7萬億美元,而2016年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國家中,第九名巴西的GDP是1.77萬億美元,第十名加拿大的GDP是1.55萬億美元。第二,股市波動。2014年8月,上證指數為2 100點左右;2015年6月12日達到峰值5 178.19點,10個月上漲了3 000點。但是6月13日出現了反轉,當日跌去103.36點,跌幅達2%;接下來10個交易日,跌幅均超過3%;2015年8月26日上證指數跌到2 850.71點的谷底。目前,指數勉強反彈至2014年12月的水平。第三,銀行“資金荒”。2017年,銀行再次出現“資金荒”,隨之出現的是銀行理財收益率、債券利率提高。第四,房價上漲。從2015年12月開始,房地產市場再次開啟上漲模式,一線城市的房價漲幅超過了2014年8月份前的漲幅。2017年5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和環比指數分別為9.5%和0.7%;70個大中城市二手住宅價格同比和環比指數分別為7.8%和0.6%。①
外匯儲備減少、股市波動、房價大漲和銀行“資金荒”同時發生并非巧合,也并非獨立,而是相互聯動、具有內在關聯性。大致邏輯是:首先,外匯儲備減少引起國內貨幣供給被動減少,貨幣供給減少引起資產價格下降,而資產類型不同,其流動性存在差異:金融資產如股票流動性強,價格迅速調整;房地產流動性差,價格調整存在時滯。其次,由于商業銀行主導著中國的金融體系,而銀行的大量資金直接或間接地投向了房地產市場,所以在房價調整壓力下,銀行出現了“資金荒”。第三,國際資本流出或國內企業海外投資是外匯儲備減少的直接原因,而國內房價過高及其泡沫風險是資本流出的重要原因。
可見,如上四個經濟現象的疊加,歸根結底是金融問題,因而其波動涉及金融安全。對此,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那么,在經濟下行等因素綜合作用下,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安全,這是本文的研究主題。
二、對金融風險產生及防范機制的研究
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金融在其中的作用不同。按照金融發展水平及其與宏觀經濟的聯系,大致可以將其分為金融未發展、金融滯后發展、金融與經濟平行發展、金融超前發展四個階段。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基本上處于滯后階段,所謂滯后發展階段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經濟發展對金融市場的依賴度很高,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支撐作用,但是金融管制依然存在,金融體系實際上處于從屬地位。因此,當前中國的各種潛在金融風險實際上是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既有金融體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經濟結構矛盾和經濟體制轉軌不到位的因素。鑒于此,關于金融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一是從實體經濟視角探討金融風險的產生。許偉、陳斌開(2009)基于1993~2005年的季度數據,討論了銀行信貸和中國經濟波動的關系,發現信貸沖擊解釋了大部分短期消費、貸款以及貨幣余額的波動, 對產出、投資的波動有一定解釋力。郡莉莉、王一鳴(2012)運用一個包含三種金融市場沖擊的模型研究發現,產出波動由金融市場沖擊導致,該比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而上升。李旭東(2012)指出,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主要源自宏觀經濟壓力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所帶來的不良后果。易誠(2013)指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反彈,使商業銀行承擔了巨額債務,削弱了貨幣信貸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毛振華(2016)指出,企業部門的債務風險是影響當前宏觀經濟風險的關鍵問題。馬建堂等(2016)指出,在經濟下行和資產貶值的壓力下,前期經濟高增長階段積累的高杠桿率風險逐步暴露,而經濟下行又增加了去杠桿的難度。國際經驗表明,高杠桿率往往伴隨著經濟泡沫和系統性金融風險,一旦集中爆發,金融危機恐難以避免(益言,2016)。
二是從金融監管視角探討金融風險的防范。周小川(2011)指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標是維護金融穩定、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強的、體現逆周期性的政策體系。辜勝阻(2014)指出,當前金融體系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是部分金融活動游離于體制外而監管不到位,原因是監管體制的過度管制,因此,必須逐步建立“混業經營、統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楊駿、邢科(2015)認為,現有基于機構監管理念的“一行三會”金融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防控金融風險、調控經濟波動的需要,需要借鑒國際經驗,重塑金融管理體制,理順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關系,重新定位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部門職責。陸磊、楊駿(2016)對中央銀行傳統目標及其政策手段局限性進行了深刻反思,指明了金融穩定重回中央銀行目標菜單后,中央銀行協調其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的邏輯框架以及有效政策工具的變革方向。
但是,在金融開放條件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功能差異進一步擴大,如果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合二為一,可能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因此,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應該分設,兩者之間進行合理分工(錢小安,2002)。謝平認為,“一行三會”各管一處,監管比較好,只是在一些交叉的業務上存在問題,需要繼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和框架,但不宜大變。吳曉求建議,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采取“雙峰模式”,一方面央行保持體系穩定;另一方面前置性安排使市場風險衰減(張焱,2017)。童中文等(2017)發現,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具有協同性。張泉泉(2014)提出,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體系,應明確政府與金融機構的作用和職責,充分利用金融與財政處置風險的優勢。吳念魯、楊海平(2016)提出,將各類微觀審慎監管部門及各類行政主管部門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對宏觀審慎管理作出優化。
總體上,已有研究從宏觀經濟、金融市場失靈兩個角度探討金融風險起源,并給出了兩種風險防范機制:其一,從宏觀經濟失衡出發,主張運用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防范金融風險;其二,從金融市場失靈出發,主張加強金融監管。事后來看,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從未有效遏制金融危機的爆發,甚至政府失靈本身就是問題所在。這表明,現有的金融風險防范機制具有現實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三、經濟波動與金融風險的起源
金融風險防范理論和實踐其實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均衡或出清是經濟的理想運行狀態,而經濟波動是對均衡的偏離。這種偏離既浪費資源、導致低效率,又造成失業、收入下降和社會不穩定,屬于反常現象。究其原因,經濟學家把其歸咎于信息不完全、外部性、不完全競爭、公共產品、分配上的馬太效應等市場失靈問題。因此,需要外力來修正此類反常經濟活動,這就是政府干預的理論依據。但是,所謂的壟斷、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的存在,都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不構成政府干預市場的正當理由(張維迎,2015)。據此推論,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基本特征的產物和表現形式,因而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一)市場經濟與周期性經濟波動
1825年,英國發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經濟危機。自此開始,歐美國家大約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經濟危機,如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和1872年都有發生。與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時代遙相呼應,自19世紀中葉以來,學者根據各自掌握的資料提出了不同長度和類型的經濟周期理論,如基欽周期(3~4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庫茲涅茨周期(15~25年)和熊彼特周期。馬克思也生活在經濟危機頻發的時代,對經濟危機有直觀感受和第一手材料,因而對其進行了探討,例如他指出:“現代工業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不同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 ②
經濟周期源于供求失衡。對此,馬克思、哈羅德、多馬分別從不同的理論基礎、不同的假設條件出發,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論。在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模型中,只有當Ⅰ(v+Δv+m/x) =Ⅱ(c+Δc)時,或者Ⅰ(c+v+m)=Ⅰ(c+Δc)+Ⅱ(c+Δc),且Ⅱ(c+v+m)=Ⅰ(v+Δv+m/x)+Ⅱ(v+ Δv++m/x)時,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供求出清,不會出現生產過剩或產品短缺。但是,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的消費和投資行為,取決于無數的微觀主體決策,而他們具有不同的消費或儲蓄偏好、收入水平和投資預期等,所以一個微小的Δv、Δc和x擾動,就會造成經濟波動,出現有些部門產品過剩而另一些部門產品短缺的矛盾。
哈羅德-多馬模型同樣表明,經濟要保持均衡增長就要求實際增長率GA等于企業家感到滿意的增長率GW,并等于人口增長率n。其中,GA=s/v,GW=s/vr。哈羅德認為,理論上這一條件可以存在,但現實可能性極小。如同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模型一樣,實際增長率是許多各不相同的決策者的預期、決策和外部環境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儲蓄比例s、資本/產量比v和勞動力增長率n分別由若干獨立因素決定。
可見,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是供求失衡的根源。對此,馬克思和凱恩斯主義者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決思路:馬克思從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出發,提出了公有產權取代私有產權的解決方案;而凱恩斯主義則主張私有產權下的政府干預。這些方案無一例外地都是政府干預型的。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剝奪地產、征收高額累進稅,壟斷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等等。但是,從蘇聯模式、中國的產權改革成就和西方國家的周期性經濟波動來看,政府干預只會引起新的經濟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周期性經濟波動問題。
(二)經濟波動與資源配置效率
長期以來,學者從周期性經濟波動中看到的是經濟蕭條、工人失業、貧富分化、資源浪費和社會不穩定等現象。正是基于這一觀察和憂慮,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政府干預,消除經濟波動根源。但是,這種認識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局限。第一,樣本和時間跨度問題。在19世紀中葉,雖然經濟危機頻繁,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但是經濟危機還是新事物,經濟學家所能觀察到的樣本數量非常有限,理論上難以根據一個短期內的小樣本判斷經濟波動的長期影響。第二,缺乏比較研究。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替代方案,而這些方案只是理論性的,當時并未付諸實踐,無法證偽其現實可行性,而后來的兩種替代方案(計劃經濟和凱恩斯主義)表明,替代方案不完全有效。第三,放大經濟波動的成本和政府干預的收益。人類長期生活在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短缺經濟條件下,這造就了人類的風險厭惡偏好和勤儉節約習慣,而突然出現由產品過剩引起的經濟危機完全顛覆了人類的固有習慣,因而對經濟波動懷有抵觸和厭惡情緒。在經濟研究中,具體體現為學者無意識放大經濟波動的成本和政府干預的收益,縮小市場自我糾錯的能力。
實際上,當把經濟波動的時間跨度拉長,同時引入可比較的參照系后,我們發現,經濟波動是資源配置的跨期安排,也是產品創新、產業升級的重要動力機制。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有需求,利潤最大化行為和行業或企業競爭與產品短缺不兼容,因此,經濟波動的表現形式是產品過剩。第二,對于產品過剩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首先,產品過剩是資源錯配問題,以中國房地產市場為例,庫存過多引起上下游產業產能過剩,如鋼筋、水泥、家具、家電等,而生產這些產品的資源本可以投向其他產業,生產更多其他產品。其次,資源錯配的后果是資源配置低效率,但低效率的程度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取決于資源錯配的持續時間。具體而言,如果經濟波動是一種短周期,如基欽周期(3~4年)和熊彼特周期中的短周期,從而產能過剩是一種短期現象,那么資源錯配時間較短。企業一旦度過了經濟周期的谷底,就可以把過剩產能轉化為經濟復蘇階段的生產優勢,從而獲得“先發優勢”。在此意義上,不存在所謂的資源錯配及其低效率問題,經濟體系只不過是進行了跨時期的資源配置安排,即以一個時期的資源配置低效率為代價換取另一個時期的資源配置高效率,類似消費者的跨期消費,從而確保長期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
相反,如果經濟波動周期較長,如朱格拉周期(9~10年)、庫茲涅茨周期(15~25年)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從而資源錯配時間較長,那么在經濟復蘇來臨之前,企業可能已經被沉重的財務負擔壓垮,從而造成工人失業、廠房閑置和產品廢棄等。在此情形下,資源錯配的后果就不僅是低效率,而且是資源浪費。但是,在經濟波動實踐中,尚不存在如此極端的案例,即使存在企業破產,它們的廠房、產品、原材料和工人通常會被其他企業并購和雇傭,成為其他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和市場份額,甚至進軍國際市場的資源基礎。因此,即使資源錯配具有長期性,也不存在純粹的資源浪費問題。
更重要的是,企業并購或重組通常發生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的市場競爭中,所以兼并在本質上是高效率生產替代低效率生產的過程。同時,由于并購企業擴大了生產規模,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所以就有可能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利益,從而在微觀上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此外,被并購重組的潛在風險、競爭壓力和經濟波動沖擊,促使企業進行預防性技術投資,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或者提高產品質量,改進產品設計,從事產品多樣化生產,這些都會增進資源配置的微觀效率。實際上,在產能過剩促使部分企業退出現有生產領域之前,一些企業已經率先進行技術和產品研發,引領新產業,打造新經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在熊彼特的經濟周期理論中體現得最為顯著。同樣地,在新產業出現、傳統產業消失的過程中,也存在區域之間的產業轉移問題,因此,從跨地區的角度考察資源配置,產能過剩也屬于資源錯配,而不是資源浪費。與跨期的資源再配置類似,跨區的資源再配置在本質上是一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過程。舉例來說,產業轉移接收地可以迅速復制先前的生產技術、銷售渠道、資源供給商和市場經驗等,盡快從事生產,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③ 據此推理,在全球范圍內的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背景下,這種“先發優勢”有助于抑制收入分化。
綜上,從跨時期和跨地區或跨國的視角來考察,經濟波動既沒有造成資源浪費,也沒有造成資源配置低效率,而是轉化成了企業、地區乃至國家的“先發優勢”或“后發優勢”。就此而言,經濟波動并非經濟反常現象,而是更長跨度、更大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機制。這一機制看似只是對短期的反常經濟運行做出被動修正,實則在于通過創新(“先發優勢”)和模仿(“后發優勢”)實現長期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因此,經濟波動像壟斷、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一樣,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三)經濟波動與金融風險
對于經濟波動,可以獲得兩個重要結論:(Ⅰ)經濟波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產物,這些因素既包括新追加的可變資本Δv、不變資本Δc、企業家在利潤中的消費支出比例x、儲蓄比例s、資本/產量比v和勞動力增長率n等微觀層面的因素;也包括貨幣供給、利率等體制性因素;還包括戰爭、革命、選舉、新資源發現、科學或技術突破等體制外因素。(Ⅱ)從資源的跨時空配置角度看,經濟波動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一種機制。
現在的問題是:在結論(Ⅱ)不成立的條件下,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措施能否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對此,從結論(Ⅰ)可知,在各種影響因素中,唯有貨幣因素在政府的控制范圍之內、可預測的,而其他因素都在政府的掌控范圍之外、不可預測。因此,對于政府而言,宏觀經濟運行其實就是一個“黑箱”,政府的信息有限性把其作用限制在有限的干預工具上——貨幣等少數體制性工具。考慮到不可預測性因素的數量和影響大于政府掌控的貨幣等體制性因素,而且體制性因素通常又是不可預測性因素的函數,因此,體制性因素本質上具有不可控性、不可預測性,這進一步限制了“有形之手”的作用。正是在此層面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干預本身是經濟波動的根源。
因此,對于微觀經濟主體而言,經濟波動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約束條件,具體而言,企業在經濟波動條件下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在經濟波動條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于是,在經濟波動和凈收益最大化條件下,不管是企業還是消費者,其經濟行為都呈現出周期性波動特征。即,在經濟繁榮階段,微觀經濟主體增加融資、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消費和金融投資比例;在衰退階段,微觀經濟主體減少融資、削減生產規模、降低消費和金融投資比例。這種順周期投融資行為一方面引起金融機構信貸擴張、金融市場繁榮和微觀主體債務膨脹;另一方面造成產品供給增加和產品供過于求。直至某個臨界點,所謂的經濟拐點就會出現:企業產品滯銷,償債困難,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上升,惜貸現象普遍,這反過來加劇微觀經濟主體債務負擔。至此,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之間形成了一個脆弱的關系:任何一方頂不住壓力,出現違約,就會引發金融風險蔓延,嚴重時則]變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簡言之,金融風險源于微觀經濟主體的順周期經濟行為,而后者與實體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相關。據此推],在經濟波動中,如果一部分經濟主體采取順周期行為,另一部分主體采取逆周期行為,那么集體行動的結果可能是中性的,或不具顯著的順周期性特征,由此避免金融市場的順周期性現象及其波動。然而,在經濟繁榮階段,對每個微觀經濟主體來說,在其他主體選擇策略既定的條件下,其最優策略是選擇擴張生產和提高金融投資比例,否則其市場份額就會被競爭者搶占,或者承受通貨膨脹和資產貶值損失。最終,集體行動的結果是:各主體的實際財富沒有增加,只是造成了資產泡沫,這就是風險點。
四、金融風險防范機制構建
金融風險是宏觀經濟波動和微觀主體的順周期行為共同作用的產物,微觀經濟主體的順周期行為是宏觀經濟波動下的最優行動,而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也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一種機制,因此,金融風險是市場經濟內在特征的產物。
(一)金融風險防范誤區
經濟波動及其金融風險的內在特性表明,現有的金融風險防范理念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誤區。 第一,金融風險防范工具僅限于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首先,如同政府把公共產品、外部性、非對稱信息、壟斷和交易成本等看作市場失靈而非市場的內在特征一樣,政府把經濟波動看作市場失靈而非市場經濟的內在特征;其次,像政府應對老問題的策略一樣,認為“有形之手”是解決經濟波動的有效手段,而忽視了市場機制解決經濟波動的可能性。
第二,誤認為防范金融風險就是防范金融機構破產,卻忽視了這一做法的真實成本或金融風險的實際轉嫁。實踐中,存在兩種金融風險轉嫁方式:其一,在允許金融機構破產因而發生金融危機的情形下,金融風險由其相關利益主體如金融機構股東及其投資者按照事前合約規定分擔;其二,在不允許金融機構破產或政府實施救助條件下,雖然金融機構避免了破產,股東及其投資者避免了財務損失,但是金融機構的資金損失并未消失,而只是通過政府救助方式,如政府直接注資、國有化和組建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等,將損失轉嫁給了納稅人。政府救助的長期經濟后果就是金融機構的敲竹杠、道德風險和“大而不倒”風險,而這些問題會進一步鼓勵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和政府尋租問題。
第三,誤認為金融分業監管是造成金融風險的根源,因而成立大一統的金融監管機構是實現監管缺失或監管重疊的有效替代。以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為例,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強制金融機構分業經營,“保險業、證券業和銀行業等金融子行業實行分業經營”。隨后,證監會、保監會和銀監會陸續設立,陸續建立起了分業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客觀上,金融分業監管容易導致監管真空和監管重疊,引起監管套利。例如,中國金融體系存在表內受到嚴格監管的銀行和表外受到較少監管的“影子銀行”問題,后者主要包括銀行理財、券商資管、信托融資、委托貸款、表外商業匯票、小貸公司、擔保典當和地下融資等,而近幾年的債務膨脹主要是借道影子銀行實現的。然而,金融分業監管相當于部門制衡機制,即使出現決策失誤,也僅限于部門,而不會波及所有金融機構,因此相比大一統的金融監管體制,分業監管的負面影響顯然被夸大了。
(二)金融監管改革方向
綜合考慮金融風險的內在特性和金融監管誤區,筆者認為,金融監管理念轉變是金融監管改革的首要著力點,具體而言:第一,金融市場波動既是實體經濟波動的表現,具有不確定性,也是微觀經濟主體決策失誤的沉沒成本,具有不可救助性,所以金融監管的首要行為準則是中立、穩定、連續和可預測,避免金融監管成為金融市場波動和金融風險爆發的沖擊因素;第二,切實執行金融機構破產機制,打破長期以來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困局,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作用,使經濟參與主體承擔投資損失,而不是轉嫁給外部經濟主體,切實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保障納稅人利益;第三,在金融混業經營迅速發展的時代,成立統一的金融風險監管機構不失為一種最優選擇,④ 但是要從制度上設計好新、舊監管部門的權責利、機構安排和分工合作等,防止落入監管層級增加而監管效率下降的陷阱,同時建立統一監管機構的制衡機構或問責部門,防止絕對權力使其成為新的尋租部門。
[注 釋]
①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② 詳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699頁。
③ 20世紀70年代末之后,歐美國家進入了“滯漲”階段,面臨產能過剩問題,急需傳統產業轉移渠道,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這可以看作是產能過剩在全球范圍內的一次配置,整體上提高了全球經濟增長率。
④ 2015年7月14日和15日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參考文獻]
[1] 辜勝阻.防范經濟轉型期的金融風險[J].中國金融,2014(14).
[2] 郡莉莉,王一鳴.金融發展、金融市場沖擊與經濟波動——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2(12).
[3] 陸磊,楊駿.流動性、一般均衡與金融穩定的“不可能三角”[J].金融研究,2016(1).
[4] 李旭東.以宏觀審慎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N].人民日報,2012-11-23(007).
[5] 馬建堂,等. 中國的杠桿率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J].財貿經濟,2016(1).
[6] 毛振華.去杠桿與金融風險防范[J].中國金融,2016(10).
[7] 錢小安.金融開放條件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分工與協作[J].金融研究,2002(2).
[8] 童中文,等.金融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的協同效應——考慮金融系統性風險防范[J].金融研究,2017(3).
[9] 吳念魯,楊海平.經濟金融風險傳染的防范與治理——基于資產負債表視角的分析[J].西南金融,2016(2).
[10] 許偉,陳斌開.銀行信貸與中國經濟波動:1993-2005 [J].經濟學(季刊),2009(3).
[11] 楊駿,邢科.經濟新常態、創新驅動和金融改革——“十三五”期間我國金融業改革的邏輯和重點問題[J].上海金融,2015(5).
[12] 易誠.產能過剩與金融風險防范[J].中國金融,2013(19).
[13] 益言.從國際經驗看中國去杠桿[J].中國金融,2016(7).
[14] 張焱.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須加快監管改革[N].中國經濟時報,2017-01-11(001).
[15] 張泉泉.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誘因和防范:金融與財政聯動視[J].改革,2014(10).
[16] 張維迎.經濟學原理[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17] 周小川.金融政策對金融危機的響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和主要內容[J].金融研究,2011(1).
Economic Fluctuation,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Jia F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exis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re based on a hypothesis: market equilibrium is the ideal situation in economic movement,while economic fluctuation can lead to inefficiency. But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first-mover advantage or second-mover advantage of enterprises,regions or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so it is a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a longer span and wider range. In this case,economic fluctuation is also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rket economy like monopoly,externalit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us financial risk is the product and form of this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xisting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ideas and gives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 reform.
Key words: financial risk;economic fluctuation;expanded reproduction;Harrod-Domar model;resource allocation;financial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