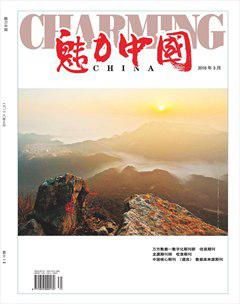歷史進程中的戲曲改革態勢
明巧玲
作為璀璨的古代文化的組成部分,戲曲藝術取得很高成就,它以特有的光輝自立于世界藝術之林。然而,規律是無情的,任何燦爛的文化都表現為一個歷史的過程,都具有時代性。作為法則,時間對于每種文學藝術都一視同仁地行使它的權威,使其成為歷史。隨著漫長的封建社會的結束,中國古代文化也譜寫完最后一章。
中國戲曲形成后,經歷了宋金院本、雜劇和南戲、傳奇、地方戲曲四個發展階段。由于這些變化都是以封建社會為歷史背景,所以它們不但從內容到形式都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而且就總體而言,它們都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屬于古代文化范疇。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作為一股政治力量而出現。從舊文化過渡到新文化。經歷了從醞釀、準備到嬗變的過程,直至五四運動才完成這次歷史性的轉折。一種全新的、與時代同步的文學觀念和體制在巨變中擔承,從而使我國文學跨入世界現代文學的先進行列。這一場新舊文化裂變的沖擊波必然要沖擊到作為中國民眾主要舞臺欣賞對象的戲曲,而戲曲藝術自身也在這時提出了變革的要求。昆曲、戈陽腔、梆子腔和皮黃腔是中國近代戲曲的有代表性的四大聲腔體系,它們的動向很可能表明我國戲曲的發展趨勢。早在清中葉,昆曲和戈陽腔已經開始衰落;梆子腔的衰落始于清末,皮黃腔在清初失去了發展勢頭。這就是說,伴隨著封建社會的結束,中國戲曲的幾種主要聲腔體系都進入了衰退期。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在向人們展示一條規律,即作為封建社會產物的戲曲藝術,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時代要求創造出一代新戲曲,延續這種藝術的生命。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戲曲不止一次地被作為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受到嚴厲批判。建國以后,我們全盤繼承下來的戲曲藝術,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都屬于古代藝術的審美范疇。當改革開放的大潮涌來之際,現代藝術應運而生,西洋音樂的引進,民族音樂的迅速發展,反襯出戲曲音樂的陳舊感;現代舞蹈的勃興,話劇在表演領域的開拓,也都向戲曲提出挑戰。戲曲在東、西藝術的比較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容與形式,檢閱自己的觀念和實踐。戲曲理論家、導演和表演藝術家從中受到了藝術思維的啟迪,擴大了藝術視野,提高了審美能力,豐富了藝術經驗,從而有機會再更大的藝術天地里去把握、領略戲曲的內在規律及概括生活的藝術手法和技巧,深化思考我國戲曲的現狀與未來。然而,西方各種思想與文化思潮的潮涌而來,很多人在品種花樣繁多的西方現代藝術面前,一時眼花繚亂,失去了鑒別與選擇的重心;社會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錯綜復雜的背景下登場表演,影響所及,戲曲改革中的民族虛無主義,全盤西化的觀點時隱時現;人們在新奇審美欲念的驅使下產生的對藝術反映現實生活的直接性與靈活性的與之有力競爭;加上戲曲這種古老藝術與現代生活的某些隔膜,戲曲一時又對自身缺乏自覺與清醒,對觀眾多樣性的審美意念較少體貼與諒解,于是乎往日最有群眾基礎性的民族戲曲藝術受到了冷落,感到了落寞,逐漸走向了低迷。面對不景氣的現實,正確的態度應是及時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找出與之對應的現實背景和自身原因,自覺去振興,去改革。由于理論反映的遲鈍,藝術實踐上的盲目,在部分人中卻產生了對戲曲存在價值的懷疑,動搖了改革戲曲應有的勇氣和信心。他們不是把目光投向自己民族藝術的懷抱,了解人民的真實好惡與選擇;反而一味地向西方藝術傾斜與偏袒,甚至迎合庸俗的審美情趣,拿出一些非東非西,不倫不類,捏合雜湊的所謂藝術品塞給觀眾,一時舞臺上簡直像時裝表演,一味地花樣翻新。如此一來,不僅敗壞了戲曲在群眾中的聲譽,失去了社會多數觀眾對戲曲改革振興的期望與支持,而且,一些人失去了應有的鎮靜與理智,幾乎以為戲曲真的要壽終正寢了,大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之勢。
中國戲曲是在世界的東方這片土地上伴隨著炎黃子孫的生存和繁衍產生和發展的。炎黃子孫在漫長的歲月里按照自己對自然與人生的理解,憑借自己的審美意識、審美經驗與審美理想構造的燦爛藝術宮殿,是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與豐富的美學意蘊的民族藝術。它以合語言、歌舞、音樂、美術等多種藝術為一體的綜合性的藝術性格向世界展現它令人驚嘆的風采,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獨立于世界藝術之林。在遠自漢、唐,近自兩宋至今近兩千年的歷史演革中,中國戲曲在適應時代的選擇上曾磨礪出自我調節的能力,在生存競爭中煥發自己的青春,留下了豐厚的戲曲遺產。只有在繼承這些優良藝術傳統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行革新。面對戲曲出現的低谷的現實,人們對戲曲前途的憂慮悲觀情緒,尤其是盲目崇拜西方藝術的民族虛無主義錯誤思潮的影響,如何正確地繼承戲曲遺產,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充分的戲曲史料表明,中國戲曲所走過的道路,是以“先驅者傳給它的特定思想資料作為前提”“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合乎規律”的繼承發展道路,元雜劇中的曲牌聯套的音樂形式,明顯是從它以前的諸宮調和其它北方音樂形式繼承借鑒而來;明清傳奇的音樂體系是繼承發展南戲和北元雜劇音樂的優秀音樂遺產的再創造。不僅一個劇種的發展離不開對它以前藝術的繼承,而且一個有創造性的戲曲作家或一部由新開拓的劇目,都無不存在著對以前作家作品的藝術借鑒。如果湯顯祖失去了對楚辭、唐、宋、詩詞的繼承,就不會有《牡丹亭》語言的精煉、含蓄、濃麗典雅的風格。如果沒有元慎的《鶯鶯傳》、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的藝術遺產作借鑒,王實甫很難寫出《西廂記》。戲曲表演藝術更是如此。要么是從前輩表演藝術家處繼承;要么是從姊妹藝術汲取營養。以此為“前提”“條件”,來創造自己的表演個性,形成獨特的風格,創造新的戲曲流派。京劇麒派藝術創始人周信芳在談到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的表演藝術成就時說:“在傳統的戲曲中,有群舞,也有獨舞,但似乎更注重獨舞。蘭芳同志繼承了傳統戲曲豐富的遺產,更進一步創造了許多旦角獨舞。如《霸王別姬》的劍舞,《天女散花》的舞綢子和散花舞,以及其它戲里的水袖舞等等。所有這些事實說明,戲曲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不僅積累了豐富的藝術遺產,而且還有著繼承遺產,創造發展的優良傳統。正是繼承與借鑒給了戲曲生存創造的旺盛活力,使自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藝術層次上不斷地自我完善,保有藝術青春。這種生命力是建立在對民族審美觀、價值觀、美學理想的真正理解與獻身上的生命力。是這種生命力在向我們證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戲曲經受住了生存與發展的考驗。它啟示我們,只要按照戲曲繼承創造的規律去發展戲曲,戲曲不僅不會消亡,而且會脫離困境,走出低谷,在對自身遺產與外來藝術的有益借鑒中繼續發展。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任何事物都要發展,都要取眾之長,避己之短,如果不競爭,不出新,勢必要被歷史遠遠地拋在后邊。藝術之道,本來說是在不斷探索、變化、革新、創造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是在對其母體的不斷叛逆中出現的。戲曲要革新,但需要謹慎、穩步地創新,不要把遺產中好的東西改掉。所以戲曲藝術總是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通過自我機制的調整或更新,順應時代的發展。這種調整和更新,一方面表現為對原有戲劇體制和樣式的改造,使其發生變異,另一方面表現為對 新的戲劇體制和戲劇樣式的創造,板式變化體及梆子腔和皮黃腔就是這樣出現的。特別是戲曲這門綜合藝術,任何一種新因素的加入,都會牽動其它各個部門,造成不平衡,甚至紊亂,在一定時期內破壞原有的特性和完整。這樣,就提出了戲曲改革的更深一步要求。在現階段,戲曲藝術那種以變化求發展的規律仍在發揮作用。這主要表現為現代戲和新編古代戲應運而生,并在逐步改變戲曲舞臺的結構,且不斷地進行艱苦的改革嘗試,有著成功與失敗的感受。 我們都在探討戲曲改革,如果僅僅局限在某個藝術部門,局限于一出戲或某種手法,與時代的要求是不適應的。不抓住戲曲觀念的更新,很可能在原有的老路上徘徊。
當下,我們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時代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變化。人們的各種觀念都在隨之發生變化。戲曲改革的成功要做許多復雜的工作,要經過多次的探索,會遇到反復失敗的考驗。特別是這種古老藝術的現代意識的培養與蓄積,將比較凝固的表演“程式”與現代生活方式、生活節奏融洽,更是一個在戲曲現代化的過程中難以突破而又非突破不可的難點。但是,在目前戲曲大好形勢下,這種難點一定會取得根本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