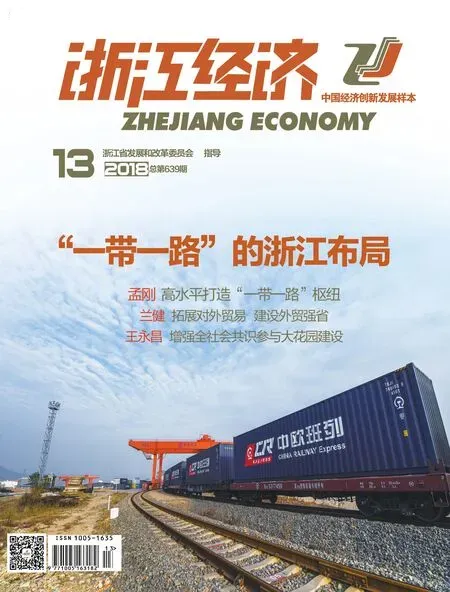正確認識中美貿易矛盾
□葛守昆
貿易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特朗普口口聲聲講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吃了虧,將中美貿易順差的責任完全加在中國頭上,加以無端的指責,實在是未分清青紅皂白。而出口導向戰略為中國贏得了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矛盾,在新的歷史時期這種戰略需要適時加以調整

今年以來,從年初開始的中美貿易矛盾一波三折,先將特朗普的加征關稅定性為貿易戰,后來矛盾表面上稍有緩和,又改口稱貿易爭端,近來又正式加征關稅,又重回貿易戰的定性。面對如火如荼、難解難分的中美貿易戰,究竟如何認識?許多人云里霧里、若明若暗,缺少理性而過分感情用事,當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搞清楚中美貿易矛盾是從哪里來的,如何評價,如何應對?
近40年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
中美貿易之間的矛盾肯定不是歷史就有的,也不是由來已久,但跟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轉換有很大關系。改革開放之初,經濟主要依靠內生增長,在國內市場自求平衡。當時對外匯的需求也不怎么旺盛。但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大趨勢和大環境下,通過一系列的開放政策,產生了對外部市場、外資等的大量需求,尤其是前30年人口高速增長形成的就業壓力,還有財政包干、分稅制極大地刺激了各級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的強烈沖動,迫切需要依靠國際市場做大范圍經濟平衡,因此出口成為主導的經濟帶動戰略。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經濟“大循環戰略”,即“大進大出”發展中國經濟。在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以后,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更加鮮明和突出,由此帶來了進出口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的顯著增長,形成了大量的順差。
據相關年份的統計公報,197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很小,只有350億美元,出口僅167.6億美元;到加入WTO的2001年,對外貿易總額達5098億美元,其中出口達2662億美元;到2017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77923億元,折合4.5萬億美元左右,出口達到2.4萬億美元左右。中國經濟在1978年出口依存度(出口占總產值的比重)只有2%左右,到2017年,達到15%左右。在1991年之前,中國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逆差,進口大于出口;到了2001年,即使有了順差(出口大于進口),但順差也只在200億美元左右;到了2017年,貿易順差已經達到4000億美元左右,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特征。
大辦開發區和出口加工區是出口導向經濟戰略的重要體現
如何出口換匯?開始主要靠低端的初加工、農副產品出口,只能換取一點可憐的外匯,根本不能滿足對外匯的需求。后來,從中央到地方,普遍的思路就是大辦開發區,搞工業加工區,集中生產出口產品。建立深圳、廈門、珠海、汕頭“四個經濟特區”,初衷就是市場經濟為主、外商投資為主、加工出口為主,走的是大進大出的路子。后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建設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全國各地大辦經濟開發區,都是大規模利用外資,吸引外商到中國投資辦廠、加工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先是港資、臺資,再就是歐美和日本、韓國等國資本的投資。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每年利用外資的規模基本上都在1000億美元以上。在投資方式上,先是合資合營,后來主要是獨資。開始主要是東部沿海省市,后來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向中西部地區梯次推進。
開發區成為出口創匯的核心區,開發區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在80%左右,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又占整個出口的40%-50%。據有關統計,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7%左右,在江蘇占到73%,江蘇的蘇州則占到92%、昆山占到100%,出口第一大省的廣東應該比江蘇的占比還要高。這充分反映了中國出口的重要特征,就是依靠外商投資企業作為主力軍。實際上,包括到今天這個階段,盡管情況也在有所變化,由于自身的國際市場開拓、技術、資本和管理等方面的局限性,外商投資對出口的貢獻依然不可小覷。當然,也反映了在這個過程中,各級開發區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就業提供者(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需要就業的勞動力),當然同時也是土地資源提供者。在出口創匯中,我們得到多的主要是“打工者”的工資,還有稅收和少量的土地占用費。實際上,這也構成了一種關系,即外國資本與我們“打工”的關系,當然包含著貿易中的矛盾。
貿易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
產業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規律。中國這么多年為什么出口增長速度很快?在客觀上,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國際的因素,包含著國際產業資本利潤最大化的需求,反映著產業資本跨越國界的邊際投入產生較多的邊際收益。比如有一段時期,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本土生產一輛汽車,單車利潤只有145美元,而在上海同樣生產一輛汽車,單車利潤則達2350美元。這主要是勞動力成本差異造成的,在加工流水線上,在上海使用一位工人,與美國使用一位工人,在勞動生產率上幾乎沒有區別,但單位時間的用工成本區別卻很大。大量外商到中國開發區、出口加工區投資辦廠,將部分產業轉移到中國,在勞動生產率差距不大的條件下,主要看中的是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價格,邊際投入有較多的邊際產出,獲得明顯多于本國的超額利潤。
這一方面體現了產業運動的規律,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資本追逐利潤的規律。現在世界上,包括國內的實際工作和研究部門,往往只看到中國出口產生的順差,卻忽視包括美國在內的產業資本在中國獲得的巨大利益。特朗普口口聲聲講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吃了虧,將中美貿易順差的責任完全加在中國頭上,加以無端的指責,實在是未分清青紅皂白。有些出口明明是包括美國企業來華投資辦廠形成的產品出口,不能全部算在中國的賬上。因此,這方面要多做客觀的評價分析,尊重國際產業運動的規律。
新時期經濟貿易戰略需做較大的調整
出口導向戰略為中國贏得了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機遇,改變了貿易逆差的局面,特別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就業的矛盾,但是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矛盾。比如,伴隨著出口的增加、資源能源的緊張,導致大量的進口依賴;開發區泛濫和過度的產品加工,環境容量捉襟見肘,增加了治理修復的難度等。在一定時期里,出口導向戰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新的歷史時期,這種戰略需要適時加以調整。
以貿易平衡取代對順差的追求。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在一段時期內可能服從于順差和增加外匯的目的,但是從長期來看,應該著眼于貿易平衡的思路。即通過出口滿足進口的需求,特別是進口生產力的需求。這也是著名的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的經濟思想。如果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僅僅滿足于互通有無,對經濟增長的能力和質量沒有什么改進,對外貿易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深化改革,促進內生型經濟增長。多年來,外資企業的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明顯偏大,將外資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的產品返銷當作中國的貿易出口,明顯加大了中國貿易順差中包含的大量水分,由此也引發了外商投資國與貿易出口國之間的矛盾。有必要加大改革徹底深化的份量,凡競爭性的國有企業必須成為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擺脫與政府利益模糊關系。在規范企業驅利行為、促進公平競爭前提下,加強私有產權保護力度,培育更多的私有制經濟主體,擴大私有制企業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
強化科技創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優勢,最終主要是科技創新的優勢。中美貿易之間的矛盾曠日持久,貿易爭端并非今天才開始,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也不是心血來潮。其實,中美貿易到了今天的時代,即使沒有特朗普,隨便是哪一位共和黨人當選總統,甚至是民主黨的希拉里成為總統,都不能排除發生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有人指責中國“盜竊”了美國的技術秘密,這完全是無端的指責。美國的科技技術就那么容易被“盜竊”?筆者不相信!至于外商投資帶來的技術外溢,不宜算在某個國家的賬上。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依靠走捷徑、簡單跟蹤模仿,必須從教育開始,有長期的基礎創新,尊重知識分子,保護知識產權。其實,人類就其本性而言,就包含著創新的內在沖動,關鍵要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
減少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前些年,有些地方為了完成出口任務,表現出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于正常的對外貿易。對此,同樣要深化改革,減少由政府出面的投資貿易,比如貿易洽談會,淡化政府的貿易色彩,促進企業成為真正的貿易主體。
堅持市場多元化戰略,適度調整國別貿易結構。在現有的貿易結構中,對美國出口貿易過于吃重,比重偏大,宜做逐步調整。重要的是推進市場多元化戰略,比如,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對相關國家的地區擴大出口貿易的比重,加大對欠發達國家、新興國家的貿易份額,以多邊貿易抵銷單邊貿易的不平衡,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