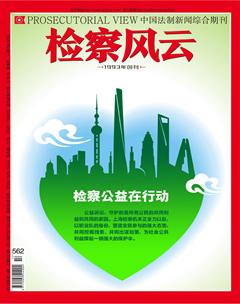民生痛點的法律監督
彭力立
近年來,社會矛盾凸顯的熱點多聚焦在生態環境、食品藥品、信息安防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領域。從被稱為“中國公益訴訟第一案”的松花江污染案,到紫金山酮酸性溶液滲漏事件,從毒奶制品頻發至個人信息被廣泛外泄,一個個民生痛點折射國家公共利益正在遭受頻繁侵害。在公益訴訟缺位的情況下,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往往無人起訴,違法者逍遙法外。由此,順勢而為,公益訴訟應運而生!
公益訴訟填補救濟缺位
公益訴訟,指的是針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由法律規定的特定機關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制度。從外延來看,包括民事和行政兩個方面。從提起主體來看,包括法律規定的特定機關和社會組織兩類主體。但囿于社會組織有民間屬性,在對抗公權力侵權(比如,行政機關未將危廢交由處置危廢資質的單位進行處置)時往往難以匹敵。因此,由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救濟公共利益的效果不甚理想,勝訴案例寥寥。
在此背景下,冀望公權力介入公益訴訟的呼聲漸增。順應民意,201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2015年1月6日,《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公布,并賦予檢察機關成為公益訴訟人的資格。這意味著,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不僅有民間力量,更涵蓋 “職業隊”!
全面推開檢察公益
2015年5月5日,《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方案》審議通過。同年7月1日,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福建等13個省份就生態環境和環境資源等領域開展為期兩年的檢察公益訴訟試點,“官告官”由“紙上”走向踐行。據《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兩年試點中,860家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9053件,覆蓋所有授權領域。2017年6月30日試點到期后,檢察公益訴訟被寫入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自同年7月1日起在全國推開。之后,各地檢察機關又辦理了公益訴訟案件10925件”。
2018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以“公益訴訟起訴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訴訟,對公益訴訟案件程序、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機關的訴訟權利義務等內容作出規定。
公益訴訟引發蝴蝶效應
隨著公益訴訟機制的確立,公益勝訴案例數量正在逐步積累。比如,河南首例食品安全檢察公益訴訟案。2018年4月,河南省南樂縣人民法院對由屬地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潘××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作出一審判決,在判處被告人刑罰的同時,對刑事附帶民事部分判處以空心膠囊銷售價款的10倍賠償19.46萬元。又比如,我國第二起勝訴的行政公益訴訟案。福建省××縣人民法院對由屬地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縣環保局行政不作為案作出裁判,責令被告將危險廢棄物進行合法處置。
同時,公益訴訟撬動了辦案模式的改革。比如,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檢察院試行“三檢并行”的辦案模式。以前,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只負責辦理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案件,公訴部門負責審查起訴刑事案件。這造成公訴、民行“單線”監督缺乏聯動的窘境。義烏市人民檢察院自2018年1月15日起,推動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負責對涉嫌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等犯罪的刑事案件進行審查起訴。截至今年3月底,義烏市人民檢察院已立案八件生態資源領域的公益訴訟案。
當然,公益訴訟并非坦途,實務操作仍有短板。比如,調查取證難。在排污類的民事公益訴訟中,要求對污染損害結果進行量化證明,這往往因時間拖沓導致難以固證損害后果的情況。司法解釋中關于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規定較簡單,缺乏剛性保障措施。這也給提起公益訴訟帶來了一定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司法實踐的不斷積累,公益訴訟為法律監督加碼的實效將會增大,公共利益維權的春天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