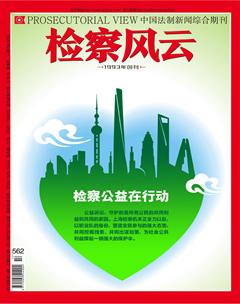智慧之路亟待縝密布局
源乘
隨著高新科技逐步融入我們的生活與工作,科幻電影中的人臉識別、語音控制、虹膜識別、VR/AR技術、人工智能機器人不再遙不可及。各國政府迫切冀望智慧之路可以引領他們應對形勢環境變化迅猛、隱患風險因素增多、城市要素高度聚集、社會矛盾紛繁復雜等多重挑戰。為了應對信息化時代的新格局,如何依托高新科技輔助城市發展已成為世界先進城市發展的必修課題。
智慧之風,如沐春風
自2013年11月國家智慧城市標準化總體組成立后,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便步入了飛速發展的快車道。國務院于2014年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智慧城市”將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三大目標之一。之后,《國務院關于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國發〔2015〕50號)、《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國發〔2016〕55號)、《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號)、《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工信部科〔2017〕315號)……各類涉及智慧城市的政策文件紛至沓來!
隨之而來,各地開始紛紛響應中央政策,著力發展智慧項目。2015年1月,重慶市推出“江北區智慧城管系統”,借助大數據中心、視頻智能分析、部件物聯智能感知,令城市巡查更智能、監督管理更精細、公共服務更便民。2016年10月,杭州市政府在云棲大會上宣布啟動城市數據大腦建設,于2018年5月正式發布我國首個城市數據大腦規劃。2017年8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阿里巴巴簽署《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引入阿里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在交通、旅游、醫療、環保等領域進行深度運用。2018年2月,上海市經信委與民生銀行上海分行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人民幣500億元的專項額度,支撐“上海制造”智能化轉型……另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德勤于2018年2月底發布的《超級智能城市》管理咨詢報告,“全球已啟動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達1000余個。而中國以500個試點城市位居榜首,成為全球建設規模最大的指揮城市國家”。
然而,無論是“互聯網+政務”,還是“大數據+云計算”,抑或“人工智能+精細管控”,再或者“區塊鏈+集成存儲”,無一不是屬于科學技術的范疇。從某種意義上,智慧建設就是向科技要支撐。以軌交安防為例。人臉識別、軌跡跟蹤、二維碼支付、智能攝像機等手段已經逐步融入其中,提高了軌交安防的信息化水平和服務效能。但在軌交安防智慧化的背后,除了高新技術的廣泛深度應用,更需要工作人員正確使用高新技術。否則,技術的運用者將會是更加嚴峻的危險源!
智慧建設背后的法律分析
高精尖技術的應用只是智慧建設的第一步,更關鍵的是如何為新技術的應用去風險。雖然我國智慧建設的頂層設計呈現政策多、試點多的良性趨勢,但智慧項目在具體設計、建設、運維等方面顯然存在諸多缺陷,尚不能匹配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以“數據安全問題”為例。據新華通訊社報道,上海已經建成了多個網絡式的大數據庫。其一,覆蓋2400萬常住人口、200多萬家企業及涵蓋全市域的人口、法人、空間地理等的基礎數據庫;其二,擁有250億條數據的全市醫聯數據共享系統;其三,每日新增30GB流量的全市交通數據庫;其四,日均數據交易量3000萬條的上海大數據交易數據庫。然而,面對海量的數據,如何給予制度供給,如何立法畫圈,如何確保數據安全,是時不待我的課題!目前,我國尚無關于公共安全數據采集應用管理的相關規定。這可能為數據的安全使用埋下隱患。
再以“人工智能的應用”為例。據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總工程師張英介紹,“在全球2600余家人工智能的初創企業和科技巨頭中,美國高居榜首,中國緊追其后。在中國,上海的人工智能發展最快,人才儲備占全國的1/3,在語音語義識別、計算機視覺、腦智工程等領域已經掌握了話語權,相關產業規模已達人民幣700億元”。由此可見,我國人工智能的基礎和前景在全球名列前茅。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將會對就業、教育、倫理、信息安全、法律法規、行業監管等產生難以估量的沖擊,引發新一輪社會管理模式的變革。如何理清人工智能的法律責任和邊界是當務之急。然而,目前我國并無相關法律法規給予界定。
近來被貼上金字招牌的區塊鏈同樣存在隱患。根據工信部發布的《中國區塊鏈技術和應用發展白皮書(2016)》,“區塊鏈是利用塊鏈式數據結構來驗證與存儲數據、利用分布式節點共識算法來生成和更新數據、利用密碼學的方式保證數據傳輸和訪問的安全、利用由自動化腳本代碼組成的智能合約來編程和操作數據的一種全新的分布式基礎架構與計算范式”。簡言之,區塊鏈本質上是一種更安全的數據庫存儲技術。騰訊金融科技智庫首席研究員王鈞曾指出,“區塊鏈采用的是分布式的存儲架構。因此,節點越多,數據存儲的安全級別就越高,可以有效防止隨意修改原始數據”。然而,區塊鏈的使用也是有條件的。目前,跨行業、跨部門的信息共享仍然存在信息壁壘,存在系統的封閉性,難以做到開放互通。在此種情況下,區塊鏈就難以發揮其最大的價值。上述種種,恰恰說明智慧之路并非坦途!
組合拳:左拳細則落地,右拳立法確責
云計算催生數據的深度應用,物聯網引導物品的網絡化聯動、人工智能推動機器的智力學習、區塊鏈深化數據的安全存儲……高新技術本身是好東西!但它就如同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正確運用。如果不為新生事物厘清邊界與責任,那么在智慧之風大行其道的時代,解決的問題真可能會比新生的問題多得多!因此,監管和法制亟須與時俱進,不能再繼續缺位。
顯而易見,我國的智慧建設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建立健全完善的標準體系引領智慧城市良性、高效發展的核心手段,是避免盲目跟風、重復建設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關于智慧城市建設標準體系最高規格的文件是國家標準化委員會與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于2015年10月22日聯合發布的《關于開展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及應用實施的指導意見》(國標委工二聯〔2015〕64號,以下簡稱:《智慧城市標準體系指導意見》)。其中,明確提出我國至2018年要初步建立智慧城市整體評價指標體系,到2020年實現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全面實施和應用。然而,《智慧城市標準體系指導意見》過于籠統,落地執行存在客觀難點,且細化的實施細則一直未能頒布。正如全國智能建筑及居住區數字化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張永剛所言,“目前各地智慧建設亟須統一的指導和規范,加快推進智慧城市標準化工作刻不容緩”。
當然,智慧城市的建設并非要大一統、全覆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是智慧建設必須考量的。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作為牽頭主體,可以結合自身實際需求,拓展地方特色,推行個性化配置,從而使智慧城市建設項目具備“揚長處、補短板、破痛點”的實效作用,可以參照“國標”但仍需“因城施策”!
此外,在具體技術的應用層面,亟待法制化,應通過立法厘清技術的應用邊界和責任主體。比如,公共安全數據領域。大數據采集必然會深入市民主體。如何在數據存儲、流轉、應用的過程中保障公民的隱私權,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供給。又比如,物聯網的主體責任。根據麥肯錫公司預測的數據,“到2025年,物聯網將在全球形成300億至500億個連接終端,廣泛應用于健康、家居、制造、城市管理等領域”。
但誠如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總工程師張英所言,“城域物聯網,目前在規劃布局、技術發展、管理模式等方面缺乏統一規劃,網絡管理職責尚不明確,運營主體權利義務有待細化”。這些高新技術都需要相關政策、法律法規予以細化界定。
面對智慧之風營造的巨大紅利,切忌跟風買單。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面對高新科技推動的新趨勢,我們既無歷史的借鑒,更無成熟的樣板。我們需要適應變革的未來,但發展的步子顯然要穩。因為智慧建設,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需要從試點中隨時總結經驗,摸著石頭過河,緩緩地穩步前行。或有如此,智慧之風才能在華夏大地如沐春風!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