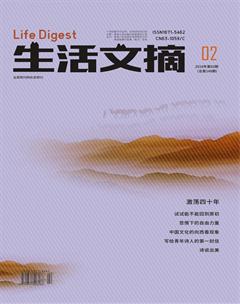文學的陷阱
王紅相
原詩: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對于《詩經》中具體作品的解讀,歷來爭議很大。很難說那一種解釋全無道理,也很難以一種解釋讓眾人皆服。但《詩經》的魅力卻是永恒的,這是文學的力量,同時又是文學的陷阱。《衛風·氓》是一首棄婦詩,這似乎已毋庸置疑,但在這首棄婦詩中到底都隱藏著什么神秘的內容,卻總是有不少可說的話題。筆者在仔細地品味了這篇作品后,卻發現了一個讓人頗為吃驚的文學現象。那么,讓我們以最傳統的方式來進入文本吧。
一、文學形象
分析文學形象是解析文學作品一種最常用的方法。《氓》一文中出現了兩個人物形象:氓和氓的妻子。在敘述的過程中,詩作是以女性的角度來切入的,因而,氓在文本中是一個隱匿的形象。也就是說,氓的形象如何并不妨礙我們對于這首詩歌的正確解讀。文本關注的是氓妻。按照政教詩學的傳統說法,氓妻并不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女人,因為她私奔在先,所以見棄是必然的結果。之所以寫她,是出于風正天下的意圖。這種教條的意見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去理睬了。人們開始同情氓妻,并進而指責氓的薄情寡信。單從人物形象上來說,這是無可厚非的理解。因為這兩個人物形象在文本中始終是對立出現的。未嫁少女的思嫁,氓的追求之急切,在文本的前兩章中交代得很清楚,同時也很形象,這是人們對他們寄予某種情感的形象基礎。后文,氓的形象藏在了文字的背后,成為人們不斷猜測的一個謎。有人說他是“二三其德”的無信小人,是不念舊情的負心漢,文中也剛好有類似的記述。也有人說得比較新奇,認為他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物,之所以棄妻是迫于某種他本人無可奈何的壓力,比如說因為其妻的無子等。但這種說法實在是只關注文本之外的巧論,于文本的理解本身并無太大的意義。本文認為,對于這兩個形象的理解,還是應該以文本為依據,這才是言之有據的文學方法,而不是把一篇文學作品最終搞成了一堆社會學的文字材料。基于此,我們可以對這兩個形象做出如下概括:氓妻從一個多情少女最終成為棄婦,前后形象截然不同,待嫁前對其夫充滿憧憬和期待,心情迫切而幸福,被棄后則充滿了后悔與自憐,甚至不乏哀怨,是一個任勞任怨、歷盡苦難的受害者。氓雖被隱在文后,但從第一章的描述可知,他婚前與婚后完全判若兩人,他從急切的追求者搖身一變而成為悲劇的制造者,至少是直接的制造者,無論如何,是不值得贊美的。那么這兩個在文本前后是對立的藝術形象,是一人之兩面,抑或是被迫而使然?這是真實再現現實的要求,抑或是文學寫作自覺的選擇?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本文提醒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必須高度注意的問題。
二、情感內容
對人物形象產生某種情感活動,這是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必然會產生的現象。但有一個問題是必須弄清楚的,即潛藏在文本之后的作者(或者說是假定的作者)的情感會不會對我們閱讀時自然產生的情感發生某種無意識的暗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制約?從接受美學的角度,文本一誕生,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感歷程,這是和作者無關的文學活動。閱讀者大可以從各種角度來闡述自己的不同理解,這種接受過程是類似于創作的一種再創造活動。其結果不受任何約束。因而,對《氓》中兩個人物的情感判斷便自然會有各種見解,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但仔細體會這種種意見后,我們發現對每一個人物的情感判斷不外乎兩種情況,要么同情,要么批評,很難見到居中騎墻的態度。除非是不介入文學欣賞之中。在文學觀念迥異于往昔的今天,我們可以不批判氓,但我們不可能對氓妻無動于衷,因為她實在是一個倍受傷害的女性形象。與其說她是一個單一的藝術形象,還不如說她是一個符號化的象征更合適。在她身上,體現的是整個中國女性的生命歷程。因而,對她的情感判斷自然而然地體現著對整個中國婦女的態度。在經學家(可以粗略地把他們認為是傳統文學觀念的代表)的文學視野中,氓妻的不受同情顯然是基于一種既成觀念的支配。我們并不關心這種觀念是什么,因為這對于解讀文本本身并無幫助。我們感興趣的是在對氓的所有行為不做指責和對氓妻受苦不落同情的對比中,文學在起著什么作用?或者說,他們對這種文學功能做了什么樣的改動?在這種角度上,我們發現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傳統文學對氓妻的情感立場很明顯地制約了后來人的情感判斷,跳出這個怪圈的事實是在經歷了近兩千年的苦苦掙扎后才得以實現的。所以,我們說,氓妻這一形象的情感內容,主要也還是在傳統文學的規范之內,甚至包括對于她的同情,也并未走出文學所為我們預設的一個前提判斷。由此可以看出,所謂不受節制的文學欣賞其實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因為我們無法擺脫文化或者文學傳統對我們潛移默化的、在無意識層面上的有力影響。
三、人物的命運
對于文本中人物命運的把握建立在社會所提供的規范認可之上,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傳統文學本身對我們所設立的前提判斷,即把人物放入一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中。這其實是對男女不同性別的人物所做出的不同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說,男人和女人都有一定的命運規定。在《氓》這篇文本中,氓是一個按照社會認可的秩序生存的個體,因而受到了大家的認可,或者說是默認。因此,在他拋棄了妻子后,也依然不受社會譴責。而氓的妻子也就只能按照既定的邏輯生存。否則,無論是一種怎樣的結局,也必然會受到眾多的非難,乃至無理的指責。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冰冷得讓很多溫情脈脈的人無法接受,但這就是傳統文學一種內在的鐵的邏輯。在這種情況下,氓妻因為勤勞或者是任勞任怨的品德而獲得丈夫重新的認可,是一種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如果本身并沒有過錯而被丈夫拋棄,也將成為一種社會所能接受的事實,沒有人會對此提出認為不該的質疑。我們在文本中看到的氓妻,除了自怨自艾之外,似乎也別無其他可以自救的好辦法。氓妻待嫁之前,尚且有著廣闊的生活背景,也有對未來的希望和憧憬。她對愛情的期待是發自肺腑的,也相信愛情的醇美甘甜,這從以鳩喻女的第三章可以得到證明。氓妻的感嘆里頭有對氓的失望,同時更有自己不能擺脫愛情的自白:“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說”在這里通作解脫之“脫”,這分明是在說與士的戀愛對于女來說是終其一生而無法擺脫的沉重的“十字架”,愛情是女人的全部。從急切想擁有愛情到失落愛情,這本身并不是女人自己的錯。我們很難想得出,把愛情當作生命的全部的氓妻在失去愛情后是如何生存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環境中,氓妻也只能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對于氓來說,他之所以急切地追求愛情,并不是把愛情當作一生的事業,而只是在生命過程中所必須解決的一件大事。因此,當這件事情得以解決之后,他自然表現出“二三其德”的本來面目。對于氓而言,擁有愛情只是生命的開始,他在愛情得以滿足的同時獲得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從這個意義上,從完整地擁有愛情的那一刻起,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放棄了愛情。至少我們在文本中看出的是,氓妻在全身心投入的時候,恰恰是氓得以解脫的時候,氓獲得了新生,而氓妻則被命運重創。這種命運安排決定了:無論如何努力,女人都是無法與其愛人的生命完整融合的,等待她們的只能是無盡的幽怨和困惑一生的失落。從《氓》這篇詩作,我們可以看出,棄婦(我們似乎可以把受到丈夫終生冷淡的妻子,比如被漢武帝打入冷宮的陳皇后,也粗略地視同棄婦)的命運,是一個必然注定的結果,這是預先設定的。
四、文本的深層意義
《禮記·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在這里,“德言容功”的次序安排說明了“以配君子”的女性應該是“溫良恭儉讓”的賢妻良母。也就是說,無論女人的命運是幸與不幸,都不應該抱怨這種不公平,這才是女人的“楷模”。而氓妻與這一點剛好不相符合,于是被形象地織入了詩作,受后人無盡的指責。《氓》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傳統文學中女性形象的絕好文本。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們在細品文本滋味之后,可以發現藏在文本背后的那個長期為人們忽視的解讀盲點:文學的陷阱,一件華麗的外衣其實是對后世無數癡情女子的無意識的誘導,同時也是對無數負心男子的最合情合理的解脫。文學在此的作用,其實就起了為不合理的現實涂脂抹粉的作用,也起了說服后人接受這種現實的作用。文學的巨大力量讓后人一代一代的躲在審美的,其實是實用的政教詩學的背后,對氓和氓妻以及其它的類似的境遇熟視無睹,并不斷用各種手段強化這種意識。我們不能斷言,掉進這種陷阱的無數讀者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對于男女而言都共同存在的這個陷阱,男人們躲在其中并不想走出來,而女人本身也是認可的,因為后世無數的可憐女子都是竭盡全力而又小心翼翼按照這種社會要求行事處世的。作為現代人,我們除了深深的遺憾外,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在解讀文學作品的時候,首先要消解傳統文學這種陷阱式的功能。
摘自《邰城王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