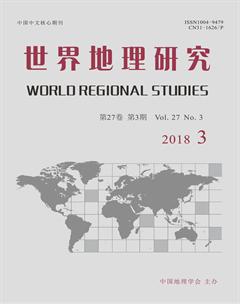符號(hào)權(quán)利下的城市街巷地名空間特征研究
楊曉俊 陳朋艷 朱凱凱 郭文浩

摘 要:通過收集整理西安主城區(qū)內(nèi)的街巷地名,運(yùn)用布迪厄符號(hào)權(quán)利理論和核密度估計(jì)法的空間平滑法,從空間可視化與量化角度分析西安街巷地名時(shí)空演變過程中地名景觀命名的變化規(guī)律及區(qū)域差異,揭示時(shí)代演進(jìn)中不同主體對(duì)地名賦予不同的政治立場(chǎng),認(rèn)為地名景觀意義的演變是各方協(xié)商和博弈的結(jié)果。研究發(fā)現(xiàn)地名分布上呈現(xiàn)新城區(qū)政治性較為鮮明,碑林區(qū)、雁塔區(qū)、蓮湖區(qū)較商業(yè)性,灞橋區(qū)和未央?yún)^(qū)主要以自然類景觀為主的差異性。不同時(shí)期的街道地名景觀意義表述了其符號(hào)生產(chǎn)者的政治空間,地名空間在日常生活下統(tǒng)治階層與民眾博弈呈現(xiàn)“官用”和“民用”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態(tài)勢(shì)。
關(guān)鍵詞:街巷地名;布迪厄理論;符號(hào)權(quán)利;核密度估計(jì)法;西安
中圖分類號(hào):K928.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0 引言
近年來空間解讀成為新文化地理學(xué)的研究熱點(diǎn),其關(guān)注人與空間之間的符號(hào)、映射及消費(fèi)意義[1]。特別是布迪厄符號(hào)權(quán)利理論將視角轉(zhuǎn)向文化顛覆政治的力量,研究空間、文化景觀如何運(yùn)作及其隱含的意識(shí)形態(tài)與權(quán)力關(guān)系,關(guān)注空間如何作為文本、意義系統(tǒng)來表達(dá)意識(shí)形態(tài)、價(jià)值觀,從符號(hào)維度出發(fā),解讀空間被賦予的文化意義,以及文化意義如何促進(jìn)特定社會(huì)實(shí)踐,并構(gòu)建社會(huì)關(guān)系與權(quán)力關(guān)系。
在符號(hào)權(quán)利理論下,符號(hào)是權(quán)力技術(shù)的工具,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jí)主導(dǎo)符號(hào)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 傳播新意義從而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秩序的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2]。政治符號(hào)的生產(chǎn)與傳播過程也是社會(huì)秩序再生產(chǎn)的過程[2]。在城市變遷過程中街巷地名是日常生活中與人們息息相關(guān)的場(chǎng)所,是人文展示場(chǎng)地,具有指示功能,同時(shí)也是嵌入體和政治話語(yǔ)的加載[3],且形成獨(dú)特的景觀和空間屬性,作為城市的符號(hào)系統(tǒng)與社會(huì)有緊密聯(lián)系。同時(shí)在官方治理過程中體現(xiàn)政治空間的變遷是城市地理和批判地名學(xué)者研究的重要文本。
20世紀(jì)80年代初,受人文地理學(xué)由經(jīng)驗(yàn)主義轉(zhuǎn)向后現(xiàn)代結(jié)構(gòu)批判主義的影響,國(guó)外學(xué)者對(duì)地名的研究由關(guān)注地名本身轉(zhuǎn)向關(guān)注地方命名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價(jià)值,以及地名在景觀中的符號(hào)特征,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文化價(jià)值觀、社會(huì)治理方式和政治意識(shí)對(duì)地方命名有深遠(yuǎn)影響[3,4]。國(guó)外對(duì)街道地名的研究已經(jīng)從傳統(tǒng)學(xué)詞源和分類研究轉(zhuǎn)向?qū)Φ孛臻g的批判研究[3]。認(rèn)為地名在塑造集體記憶中是創(chuàng)造和維持依戀感的重要組成部分[4,5],不同時(shí)期地名對(duì)民眾的情感維護(hù)、政權(quán)更迭背景具有集體記憶的重構(gòu)[6]。在社會(huì)治理上利用居民的地名感知及其差異來促進(jìn)當(dāng)?shù)厣鷳B(tài)可持續(xù)管理[7]。同時(shí)地名是象征權(quán)利的符號(hào),地名空間上的差異成為階級(jí)斗爭(zhēng)的重要場(chǎng)所[8]。受國(guó)外學(xué)術(shù)影響,我國(guó)學(xué)者對(duì)地名的研究視角由對(duì)其歷史淵源和空間分布的研究轉(zhuǎn)向關(guān)注地名本身構(gòu)建的過程。近年來的研究主要是通過GIS空間統(tǒng)計(jì)分析[9-12],分析技術(shù)與文獻(xiàn)對(duì)地名的研究開始轉(zhuǎn)向定量分析,在地名規(guī)劃管理方面關(guān)注地名文化價(jià)值的質(zhì)性分析[14-20]和定量評(píng)估建立,以及地方命名權(quán)與民主管理問題[21-30],進(jìn)一步揭示對(duì)不同政權(quán)治理下臺(tái)灣街道命名的分析[29]、不同階層對(duì)地方命名權(quán)利的博弈[29,30]。
由此看出,目前國(guó)外對(duì)地名的研究角度多聚焦于政治符號(hào)、社會(huì)正義的規(guī)范管理、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內(nèi)涵分析以及治理維度的研究。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地名的研究也從多視角多尺度進(jìn)行,但缺乏對(duì)地名時(shí)空變遷的質(zhì)性分析和符號(hào)解讀。本文從新文化地理學(xué)的視角,分析近代西安街道地名的變遷,探討不同主體在命名權(quán)利中的博弈,揭示權(quán)利因素如何在空間上呈現(xiàn)出來。
1 研究區(qū)概況、研究方法與數(shù)據(jù)來源
1.1 研究區(qū)概況
西安具有3500年的建城史,長(zhǎng)達(dá)1100年的建都史,先后經(jīng)歷了十三個(gè)王朝的更替,最終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形態(tài)。西安城的基本形態(tài)主要是基于隋唐大興城的基礎(chǔ)擴(kuò)建,明清時(shí)期有所增加。由于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不斷更替,目前城內(nèi)主要是隋唐明清、民國(guó)時(shí)期、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的道路(圖1)。
1.2 數(shù)據(jù)來源
本研究通過收集整理1986年《西安地名志》和2003年以來的區(qū)縣地方志中所涉及的近代以來西安主城區(qū)的街、路、坊、里等城市街巷地名與聚落地名并結(jié)合2016年行政區(qū)劃的行政代碼,獲得西安市轄主城區(qū)新城區(qū)、未央?yún)^(qū)、碑林區(qū)、蓮湖區(qū)、雁塔區(qū)、灞橋區(qū)6個(gè)區(qū),街坊巷里2234個(gè)地名。其中未給予出處詳細(xì)說明的地名均來源于《西安市地名志》。
1.3 研究方法
利用 ArcGIS10.2制圖功能對(duì)地名空間數(shù)據(jù)按照西安地方志所給的11項(xiàng)類別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并用核密度分析法展示分布格局。在此基礎(chǔ)上,研究搜集到保留至不同時(shí)期的西安主城區(qū)街巷地名,分析地名類型分布及其生存狀態(tài)。
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地名志等文獻(xiàn)資料,查詢主城區(qū)內(nèi)各行政區(qū)聚落地名,對(duì)其按照已給分類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將地名當(dāng)作離散點(diǎn),通過Xgeocoding得到各地名的地理坐標(biāo),并將坐標(biāo)導(dǎo)入Excel中。最后,將通過以上方法獲取的地理坐標(biāo)導(dǎo)入ArcGIS 中生成點(diǎn)文件,利用 GIS中基于核密度估計(jì)法的空間平滑法(Spatial Smoothing),得到西安各類地名核密度分布圖,進(jìn)而從空間可視化與量化角度分析西安地名空間差異性[13]。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計(jì)法的空間平滑法,它可以使離散點(diǎn)數(shù)據(jù)直觀并定量分析其空間趨勢(shì)。核密度估計(jì)空間變化可以客觀準(zhǔn)確地表達(dá)地名點(diǎn)的空間分布狀況。其基本表達(dá)式為:
2 西安市城市街巷地名的時(shí)空演變
通過地名數(shù)據(jù)庫(kù)統(tǒng)計(jì)得出(表1,圖2),西安主城區(qū)內(nèi)街巷地名大部分始于明清兩代,城外的街巷地名大部分始于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搜集了西安主城區(qū)街道地名保留至清朝滿城清光緒十九年的街道368條,清末西安作為北院,是政治軍事中心。命名以機(jī)構(gòu)建筑、宗教類、景觀類為主,且大部分保留至今的地名主要集中在蓮湖區(qū)和碑林區(qū)。
搜集保存至今的民國(guó)時(shí)期的主要街巷名607條,相比清末,民國(guó)時(shí)期機(jī)構(gòu)建筑類地名的比例下降了3.7%,而經(jīng)濟(jì)事物類、政德教化類分別上升了2.2% 和9.6%。民國(guó)時(shí)期以宗教類、經(jīng)濟(jì)類、述志類為主,經(jīng)濟(jì)實(shí)物類和政德教化類命名數(shù)量增多,國(guó)民政府開發(fā)西北的政策和抗戰(zhàn)爆發(fā)后使得沿海工商業(yè)內(nèi)遷,由于隴海鐵路的開通和民族企業(yè)內(nèi)遷,新城區(qū)東北部大部分荒地被開發(fā)為工廠,經(jīng)濟(jì)類地名迅速增加。在碑林區(qū)和蓮湖區(qū)內(nèi)作為主要的商業(yè)區(qū)保存的經(jīng)濟(jì)事物類命名的最多,地名變動(dòng)幅度也相對(duì)較小。而后由于其不再是陪都,政府對(duì)于其投資減少,道路便不再擴(kuò)建。
搜集到保留至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的街巷名1176條。相比民國(guó),宗教事物類、政德教化地名比例下降了3.1%,方位序數(shù)與祈愿類分別上升了6.4%和 1.7%,機(jī)構(gòu)建筑、宗教事物和政德教化地名的消失主要體現(xiàn)當(dāng)時(shí)的意識(shí)形態(tài)趨向淘汰帶有傳統(tǒng)意識(shí)的地名。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西安根據(jù)城市規(guī)劃方案,加快開展建設(sh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單位制”逐漸解體,計(jì)劃經(jīng)濟(jì)開始轉(zhuǎn)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觀念與社會(huì)組織方式多元化。城市建設(shè)開始引入市場(chǎng)資本,房地產(chǎn)業(yè)推動(dòng)城市面積急速擴(kuò)張,城市功能空間發(fā)生轉(zhuǎn)變。1990年后西安城市形態(tài)變化加劇,西安市的主體投資逐漸從基本建設(shè)轉(zhuǎn)向房地產(chǎn)主導(dǎo),道路和居民點(diǎn)及其地名急劇增加。其中,到1993年新城區(qū)有23條道路由民國(guó)時(shí)期的政德教化類命名改成方位序數(shù)類。
主城區(qū)內(nèi)地名的空間演變呈現(xiàn)出區(qū)域差異性(圖3),且主要是實(shí)體空間及其所虛化的指示空間的變化,地名的減少發(fā)生在實(shí)體景觀減少之后。如碑林區(qū)在1992年以后先后更新和更名了35條道路,有29條街巷佚名和消失,主要是街道合并雖然原巷尚存或部分存留,但名稱已經(jīng)不存在。在收集到的地名中實(shí)體景觀保存最久的是自然景觀類,這主要是自然景觀位置未變其地名就難以更改。清末保留的街道地名主要分布在碑林區(qū)、雁塔區(qū),主要以機(jī)構(gòu)建筑類如軍事、宗教、學(xué)府命名,經(jīng)濟(jì)事物類相對(duì)較多。新城區(qū)主要是民國(guó)時(shí)期道路為主以政德教化類命名居多,方位序數(shù)、移民因素和姓氏家族類也較多。蓮湖區(qū)多以經(jīng)濟(jì)事物類為主,地名實(shí)體景觀多已發(fā)生變化,但相對(duì)保留較多具有穩(wěn)定性和時(shí)代性。新城區(qū)政治性比較鮮明且變化幅度較大,碑林區(qū)、雁塔區(qū)、蓮湖區(qū)主要是商業(yè)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心,地名命名變化幅度較小。灞橋區(qū)和未央?yún)^(qū)主要以自然類景觀為主,變化幅度亦較小。
3 符號(hào)權(quán)力的產(chǎn)生與運(yùn)作機(jī)理
布迪厄的符號(hào)權(quán)力理論認(rèn)為符號(hào)不僅是知識(shí)與傳播的工具,符號(hào)產(chǎn)生后又將強(qiáng)化和塑造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秩序[36]。在社會(huì)秩序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過程中,統(tǒng)治者通過各種手段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符號(hào)體系,在政治斗爭(zhēng)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博弈中產(chǎn)生的符號(hào)資本形成特有的符號(hào)體系[37]。在特有符號(hào)體系里,實(shí)踐者對(duì)新秩序和意義產(chǎn)生新共識(shí),使被統(tǒng)治者將統(tǒng)治者的特殊利益當(dāng)成集體利益[36,37]。同時(shí)慣習(xí)維持著實(shí)踐者的共識(shí),使其自覺認(rèn)同符號(hào)體系所傳播的意義。在慣習(xí)作用下,共識(shí)嵌入了實(shí)踐者的內(nèi)在世界最終成為其感知體系, 進(jìn)而影響其日常實(shí)踐[36]。在近代城市化進(jìn)程中西安市的街道不斷更新,地名類型也相應(yīng)發(fā)生變化,不同的街道地名景觀意義表述了不同的政治空間(表2)。國(guó)家和政府對(duì)地名的管理與規(guī)劃不僅是為了滿足居民的需要,更關(guān)鍵的是使自己的權(quán)利合法化[36]。社會(huì)等級(jí)結(jié)構(gòu)的生產(chǎn),統(tǒng)治秩序受到被統(tǒng)治者自愿的擁護(hù),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命名時(shí)既有象征性抵抗也有習(xí)慣性沿用。
3.1 政治統(tǒng)治置換為符號(hào)統(tǒng)治
政治符號(hào)作為知識(shí)與溝通的工具,既是被塑造的結(jié)構(gòu)也具有塑造結(jié)構(gòu)的權(quán)力[36]。不同的統(tǒng)治階級(jí)在統(tǒng)治過程中,通過對(duì)地名符號(hào)系統(tǒng)的更改使民眾遵循其建立的新秩序。政治斗爭(zhēng)轉(zhuǎn)化為符號(hào)斗爭(zhēng),經(jīng)過武裝斗爭(zhēng)獲取的統(tǒng)治資本置換為符號(hào)資本[36]。
伴隨著不同朝代的更換和政治制度、社會(huì)階層的變遷帶有封建色彩的地名在民主意識(shí)不斷增強(qiáng)的過程中首先被淘汰。辛亥革命中西安滿城被毀,城內(nèi)空間功能置換,由原先的政治性轉(zhuǎn)換為商業(yè)性。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在推翻封建統(tǒng)治階級(jí)后,為讓其執(zhí)政具有合法性,執(zhí)政者開始通過地名的變更灌輸其執(zhí)政理念。因此政德教化類和經(jīng)濟(jì)類地名上升2.2%和9.6%。1933年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使東北部荒地被完全開發(fā),新建許多街道命名多以禮義仁忠等為主,地名景觀意義主要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儒家和“三民主義”思想,將帶有教化意義的地名嵌入日常生活中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新街道的命名暗含統(tǒng)治階級(jí)對(duì)空間的支配特權(quán)。新中國(guó)成立后,執(zhí)政階層傾向于用美好詞匯命名來引導(dǎo)平民階層對(duì)未來的憧憬,整個(gè)社會(huì)多次進(jìn)行移風(fēng)易俗的活動(dòng),將許多廟宇拆毀。新的執(zhí)政階層選擇用社會(huì)主義新秩序的地名嵌入新家園的命名中,試圖借助地名更替將宗教神圣從人們思想中抽離出去,從而弱化傳統(tǒng)文化所倡導(dǎo)的落后的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新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形成的沖擊。
3.2 權(quán)力主導(dǎo)下的地名空間博弈
西安城市街巷命名雖由權(quán)力主導(dǎo),但地名在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又被民眾力量操縱。社會(huì)實(shí)踐與日常生活中民眾亦可通過意義與價(jià)值的生產(chǎn),對(duì)已有權(quán)力進(jìn)行抵抗。地名空間成為階層博弈的場(chǎng)所,具有官用和民用兩者的相互競(jìng)爭(zhēng)性。
清末民間商業(yè)活動(dòng)發(fā)達(dá),商貿(mào)以東關(guān)為中心,主要是藥材、棉布及土特產(chǎn)品等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大量會(huì)館集聚在東關(guān),圍繞城郭二十多條商業(yè)街坊的居民大部分為農(nóng)戶。商業(yè)街道的命名多以商鋪和貨物為名,是平民階層作為邊緣群體日常生活場(chǎng)景在空間上的訴求。民國(guó)時(shí)期,大量移民遷入,居住在新城區(qū)進(jìn)行開墾,出現(xiàn)了“新桃園村”和“小農(nóng)村”等與農(nóng)業(yè)有關(guān)的地名,地名空間上呈現(xiàn)出民眾的日常活動(dòng)。馮玉祥將東城門命名為“中山門”,表述其向東進(jìn)擊中原的政治野心,但民眾層面多俗稱為“小東門”,其打通原有城墻建立“玉祥門”沿用至今,但民眾仍多俗稱為“小西門”。在政治經(jīng)濟(jì)因素影響下,新地名大量涌現(xiàn)、舊俗地名不斷消亡導(dǎo)致集體觀念弱化,集體記憶碎片化,地名和空間強(qiáng)烈割裂,城市歸屬感減少。城市開發(fā)過程中一些街道地名由原先的聚落名就地轉(zhuǎn)換演變過來。這些新地名在進(jìn)入日常生活實(shí)踐的過程中,普通民眾的集體記憶起到作用。例如東八里、魚化寨,雖然地名景觀的空間景觀實(shí)體已經(jīng)消失或邊界更改,但其空間意義以及其歷史記憶功能被保留。在使用新命名的過程中,老地名的集體記憶被保存,集體記憶使得民眾不容易接受其他地名,而在布迪厄看來這種集體記憶就是“共識(shí)”所導(dǎo)致的“慣習(xí)”。
3.3 資本介入下的地名文化空間博弈
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背景下,西安市經(jīng)濟(jì)迅速發(fā)展,造城運(yùn)動(dòng)盛行,主城區(qū)居民區(qū)的建設(shè)、道路的開拓,需要將小巷合并成一片或一條線,導(dǎo)致老城區(qū)市井氣息濃郁的老地名比例迅速下降,消失或雅化。在西安城的北郊、南郊等新發(fā)展的區(qū)域,以數(shù)字排序命名的街道比例增加迅猛,如從鳳城一路到鳳城十二路,方便記憶但使地名文化內(nèi)涵不足且單一化,是城市急速擴(kuò)張的具體體現(xiàn)。
資本要素的介入使地名日益商品化,在以人為本的后現(xiàn)代消費(fèi)社會(huì),地名價(jià)值體現(xiàn)日益多元化,并成為房地產(chǎn)商的營(yíng)銷手段之一。人們?cè)谶x擇居住區(qū)時(shí)重視居住區(qū)的文化品位,為了促進(jìn)當(dāng)?shù)氐纳虡I(yè)價(jià)值,街道命名被賦予一定的美好象征意義,如博士路、學(xué)士路、錦業(yè)路等。同時(shí)地方文化受到全球文化的沖擊,為迎合國(guó)際大都市的形象開發(fā)商對(duì)居民點(diǎn)命名多使用如丹尼爾、中海西岸等這些命名使得地名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重復(fù)率提高,沒有地方文化因子。地產(chǎn)商新開發(fā)的地區(qū)為展示和宣傳其品牌特色,街巷命名多與其商業(yè)品牌和企業(yè)文化相關(guān)聯(lián)。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資本要素介入,不同參與者的加入使地名在空間上愈發(fā)商業(yè)化,城市公共空間趨于私有化,城市地名文化生態(tài)同化,區(qū)域地方文化內(nèi)涵在這種模式下逐漸消失。
4 結(jié)論與討論
地名景觀意義的演變是各方協(xié)商和表征運(yùn)作的結(jié)果。街巷地名的變更受政治、文化、經(jīng)濟(jì)多元因素的影響。地名空間在日常生活下統(tǒng)治階層與民眾博弈呈現(xiàn)“官用”和“民用”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態(tài)勢(shì)。清末,城市平民階層通過不同地名來展現(xiàn)對(duì)統(tǒng)治階層的不滿,地名空間呈現(xiàn)階層化。民國(guó)時(shí)期,統(tǒng)治階層借助地名在公共空間傳播其執(zhí)政理念,將帶有教化意義的地名嵌入日常生活中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新中國(guó)成立后,政府有計(jì)劃地進(jìn)行街道命名與變更,地名被賦予更多政治教化功能。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城市街巷地名商業(yè)色彩較重,新增地名多元化。現(xiàn)階段城市化進(jìn)程加速,房地產(chǎn)等商業(yè)化過程使街道地名成為資本與商業(yè)文化博弈的空間。
地名在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既有慣性的沿用又具有象征性抵抗。如何在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過程中使街道新命名更加公平?如何與城市環(huán)境更好地融合,提升城市的人居環(huán)境,更好地傳承城市文脈?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制訂正確的城市地名規(guī)劃和管理制度,而正確的策略建立于對(duì)地名命名“機(jī)制”透徹、批判性的理解。
參考文獻(xiàn):
[1] 錢俊希,朱竑. 新文化地理學(xué)的理論統(tǒng)一性與話題多樣性[J]. 地理研究,2015(03):422-436.
[2] 曲艷華. 國(guó)內(nèi)研究布迪厄語(yǔ)言學(xué)、人類學(xué)思想文獻(xiàn)綜述[J]. 農(nóng)業(yè)圖書情報(bào)學(xué)刊,2012(05):49-52.
[3] Palonen E. The city-text in post-communist Budapest: street name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J]. GeoJournal, 2008,73(3):219-230.
[4] Azaryahu M. Street Name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The Case of East Berli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86,21(4):581-604.
[5] Rose-Redwood R, Alderman D, Azaryahu M.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34(4):453-470.
[6] Jones R, Merriman P. Hot,banal and everyday nationalism: Bilingual road signs in Wal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9,28(3):164-173.
[7] Alderman D H. Street names and the scaling of memory: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within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J]. Area, 2003,35(2):163-173.
[8] Cre?掎an R, Matthews P W. Popular responses to city-text changes: street na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practicality in a post-socialist martyr city[J]. Area, 2016,48(1):92–102.
[9] Azaryahu M.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ve street renaming: Berlin 1945–1948[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1,37(4):483-492.
[10] 王彬,岳輝. GIS支持的廣東地名景觀EOF模型分析[J]. 地理科學(xué),2007(2):281-28
[11] 李建華,米文寶,馮翠月,等. 基于GIS的寧夏中衛(wèi)縣地名文化景觀分析[J]. 人文地理,2011(1):100-104.
[12] 宋曉英,李文娟,傅學(xué)慶,等. 基于GIS的蔚縣地名文化景觀分析[J]. 干旱區(qū)資源與環(huán)境,2015,29(12):63-68
[13] 陳晨,修春亮,陳偉,等. 基于GIS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觀空間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 地理科學(xué),2014(04):420-429.
[14] 岳升陽(yáng),田鵬騁. 北京舊城改造中的地名保護(hù)問題[J]. 城市問題,2012(10):98-100.
[15] 陳碧笙. 日本殖民文化影響下的臺(tái)灣省部分地名——附有關(guān)西方殖民國(guó)家侵略活動(dòng)的地名[J]. 臺(tái)灣研究集刊,1984(1):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