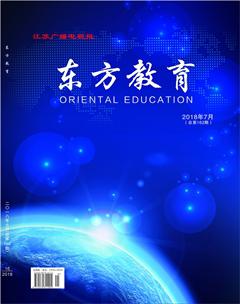對《野草在歌唱》瑪麗人生的簡析
張?zhí)?/p>
摘要:《野草在歌唱》說的是黑人摩西殺死白人女主人公瑪麗的故事。本文從瑪麗的視角以三十歲的某一天為分水嶺劃分為三十之前和之后對她的人生和悲劇成因進(jìn)行分析。
關(guān)鍵詞:野草在歌唱;瑪麗;悲劇;一生
本文的作者多麗絲·萊辛是二十世紀(jì)最偉大的文學(xué)家,她的這部《野草在歌唱》是第一部小說,以殖民主義為主題,書在當(dāng)年非常有爭議,甚至一段時間作為津巴布韋的禁書,因?yàn)樗g接的喚醒了黑人民族獨(dú)立意識。
在讀完整本書的時候,壓抑的情緒鋪面而來,粗略回憶一下會覺得瑪麗這個人從頭到腳都是悲劇的,但是細(xì)致劃分的話會發(fā)現(xiàn)30歲是瑪麗的一個人生分割線。直到30歲之前,她都過得不錯,瑪麗的父母是英國人卻在黑人的土地上謀生,那個時候黑人不能看白人主人的臉,經(jīng)常做活被鞭打,黑人吃的飯和白人是不一樣的,瑪麗在那種處境中生活盡管童年貧窮而寒酸但也應(yīng)該是順心的。而且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勤奮,在20歲時已經(jīng)在某個公司做到不錯的職位,能夠租得起屬于自己的獨(dú)立的小公寓,到了30歲,她已經(jīng)發(fā)展到有自己的獨(dú)自辦公桌,有自己的小汽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每周總有很多聚會,覺得盡管沒有婚姻,但還是很幸福的,童年時期的不幸,父母生活的嘈雜,似乎都離她遠(yuǎn)去了。
但是事情卻在30歲這個分水嶺的某一天發(fā)生了變化,她忽然聽到朋友們在客廳討論她不結(jié)婚的羞恥,說她的發(fā)帶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不符合年齡,男生說她可能沒有吸引力,女生說她可能有什么毛病,甚至擔(dān)心她勾搭自己的丈夫,要對她多加防備了。瑪麗在當(dāng)時真的傷心欲絕,一方面是被自以為堅(jiān)定的友情傷得體無完膚,一方面又覺得自己現(xiàn)在不結(jié)婚簡直就是一件極其不道德的事情。我覺得瑪麗這個時候的感覺很多女生都有體會吧,誰沒有被朋友在背后議論過?只是有人發(fā)現(xiàn)了,有人沒有察覺。
到了三十歲之后,她學(xué)會了思考。這種改變來源于大家對于她的種種議論和猜測。她是對男人那樣的懼怕,甚至在與男性朋友相處的過程中,對方想要親她,她都覺得惡心的跑開了,可是,她卻抵不住流言的力量。試想一個女生為自己打造的一個美好世界頃刻間瓦解了,2、30年樹立起來的自信瞬間破滅,這是一種怎樣的恐慌和無助,多么的可怕。所以她甚至沒有一點(diǎn)常識或者給予自己多一些時間去遇到一位適合自己的結(jié)婚對象,就辭去了公司,退掉了公寓,想要擺脫那些議論,和農(nóng)場主迪克結(jié)了婚。這個男人把她捧在手心里,她很迫切地需要這種情感,來恢復(fù)自已的自信。
只是,瑪麗的那種希望通過結(jié)婚換一個環(huán)境,安靜地生活的念想,與實(shí)際有著深深的落差。她所知道的婚姻生活與之想象的也是有落差的。多年的城市生活使她并不知道鄉(xiāng)村生活的貧窮是怎樣的貧窮。事實(shí)上,在她走進(jìn)那個“鄉(xiāng)村之家”時,她就后悔了,空曠的田野,寒酸破舊簡陋的家具,還有沒有天花板的房子,而她,只是迪克孤獨(dú)的單身生活的終結(jié)者、陪伴者。
但是,那時的瑪麗,對于新生活,畢竟還是充滿希望的。迪克對于她,低聲下氣,在這一點(diǎn)上,極大地滿足了她的自我優(yōu)越感。她用光了她的積蓄,來裝扮自己的新家,盡可能的減弱凄涼清苦的情景。但是,事情總是越做越難,當(dāng)她最后無事可做的時候,一種不安與心靈的荒蕪感便竄生出來。
有一句話特別能體現(xiàn)瑪麗當(dāng)時的情況“生活的真實(shí)面目絕對不是一個美女,隱藏著數(shù)不清的殘酷丑惡。”
這些落差她無法與附近的農(nóng)場主的妻子們溝通,她們的那種話題,引不起她的興趣,而她對于別人的自傲,也使自已被排斥在圈子的外面。她唯一可以相處的人,就是迪克。而迪克,卻將時間大把大把地花在了田地里。對于那些土人,她從小接受的種族觀念,也使她無法與之平等相處。她就這樣被拋棄在各個圈子的外面。
而迪克對于她,從開始的討好逐步變化為對她的冷漠。迪克嘗試養(yǎng)蜂、嘗試開小店、嘗試養(yǎng)豬養(yǎng)雞,可是,他總是半途而廢。生活不順心、貧苦、無所事事,在這樣的境遇,使瑪麗更加懷念起舊時時光的好來,她嘗試出逃,回到那個曾經(jīng)快樂的生活里。她一個人攜帶小箱子及所有的全部的家當(dāng)逃去城里,想要重新恢復(fù)從前的工作,她去見了從前租住公寓的房主,房主說不收留結(jié)婚的人,去見從前公司的老板,祈求恢復(fù)一份工作,那個老板,卻只是歉意地表示,已經(jīng)沒有空缺了。她覺得生活很殘忍的告訴她:之前的生活她已經(jīng)回不去了,她被拋棄了。她只能跟著來找他的迪克先生回到那個索然無味的世界里去。有些評論說“蒙蔽的主體意識使她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yùn)”。[1]這也是瑪麗性格中最大的缺點(diǎn):別人說什么都認(rèn)為是對的,當(dāng)有了自己的觀點(diǎn)和主張后遇到挫折或與之相反的觀點(diǎn)時,立刻覺得自己是錯的,不能很好的把握自我,不獨(dú)立。如果說瑪麗的一生中有過拯救自己的事情,那么也只有這么一件了,即使沒有成功。人生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風(fēng)順,一次的不成功不代表永遠(yuǎn)都喪失了這個機(jī)會,也許多試幾次瑪麗的結(jié)局就會很不一樣了。
她也曾努力地想要適應(yīng)生活,學(xué)習(xí)土語,管理黑人奴隸,但是事情為什么沒有朝著美好的方向發(fā)展呢?我覺得經(jīng)濟(jì)的持續(xù)貧困似乎是最重要因素,俗話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沒有了經(jīng)濟(jì)的支持,丈夫苦惱,妻子在這種惡劣的環(huán)境下無處可去無事可做,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直至最后,黑人家奴摩西反而成為了體恤太太的唯一來源,給她精心準(zhǔn)備飯菜,陪她說話,最終變成了跨越種族的戀情。而這段跨越種族之戀隨著種族歧視而死亡,作者也是想告訴讀者種族主義在當(dāng)時已經(jīng)到了不可調(diào)和的地步,種族主義已經(jīng)深深的腐蝕了白人的靈魂,即使窮困,限于崩潰邊緣的瑪麗也無法改變她成為種族主義的施暴者,最終,黑人會起來反抗,拿回他們作為人的人權(quán)。
在我要讀這本書之前,曾經(jīng)翻看過很多書評,我最喜歡這么一段話:“如果你30歲仍未婚,也許你就要像瑪麗一樣隨便嫁給一個只見過兩面的農(nóng)場主,去過別人需要你過得那種生活。如果你不愛自己懦弱無能的丈夫,卻不幸的愛上了一個安穩(wěn)給你安全感的黑人傭人,也許你也只能像瑪麗一樣活在強(qiáng)烈的自責(zé)不敢愛和倔強(qiáng)的想要愛的掙扎中變得恍如夢游,無神無助。也許你也試圖逃離,搭上火車回到城市,卻發(fā)現(xiàn)已被城市拒之門外,再也回不到少女時代的生活,你別無選擇,仍然要回到那個埋葬了夢想的破落農(nóng)場,繼續(xù)埋葬下半輩子的時光。那么,也許你也會像瑪麗一樣,在愛與不愛的矛盾中,清醒的意識到自己人生唯一可能的結(jié)局--毀滅。也許你也會像她一樣在臨死的那個早晨終于學(xué)會了欣賞生命的神奇和美麗:太陽從平原邊緣升起,清風(fēng)吹過樹林,無數(shù)的生靈在膜拜太陽,萬物自由生長充滿生機(jī)希望,生命的最后一天變得這么快這么短,黑夜里原來也蘊(yùn)藏著那么多的東西,閃亮的星空在閃耀,黑黑的樹林在低吼著毀滅,毀滅…… ”但是我并沒有覺得瑪麗她清醒的意識到自己的結(jié)局是毀滅,她到最后臨死前都是帶著希望的,在看到摩西的那一刻她就覺得自己錯了,她想要道歉,想要得到他的原諒,這一瞬間瑪麗性子中的不獨(dú)立看起來就要有所突破了,但是一切都已經(jīng)遲了,沒說出口的話終究哽在了喉嚨。
這本書在當(dāng)時的津巴布韋是本禁書,因?yàn)樗鼏拘蚜撕谌嗣宓姆纯挂庾R,也告訴白人,如果種族主義再這么繼續(xù)下去,那么他們的結(jié)果也會和瑪麗一樣。萊辛給了瑪麗和摩西這樣一個結(jié)局,正是象征著種族歧視這種局面將要被打破,已經(jīng)能看到曙光了。黑人開始反抗,白人開始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