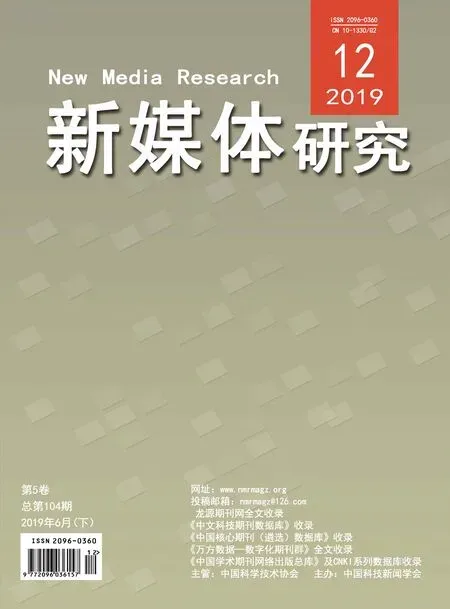擬劇論視角下泛娛樂直播中的表演行為
肖暢 郝永華
摘 要 泛娛樂直播是一種新興的高頻互動視頻娛樂內容產品,其特點主要為:內容廣泛、用戶異質和娛樂化。泛娛樂直播建構了后臺前置和跨越時空的多重虛擬場景,主播、場控和用戶在虛擬場景里扮演不同角色并進行自我呈現。其行為動機主要為:情感交流、獲得身份認同和物質回報。泛娛樂直播還需解決直播表演中前、后臺邊界模糊、真實人性缺失和表演可控性較弱等問題。
關鍵詞 擬劇論;泛娛樂直播;表演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12-0005-03
目前,各網絡直播平臺呈井噴之勢,其直播類型有:秀場直播、游戲直播、泛娛樂直播和垂直類直播。艾瑞咨詢在2017年的一份報告中,將泛娛樂直播定義為:“與主播高度相關的直播類型,直播內容在于觀眾和主播的交流互動,帶有較強的情感色彩與社交屬性。”[1]我國泛娛樂直播用戶主要分為:尋求陪伴型、放松消遣型、追逐潮流型、游戲電競型、消磨時間型和追星型[2]。其直播內容涵蓋秀場、興趣、競技、生活等多個領域,滿足異質用戶社會交往、信息獲取、自我實現等復雜多元的心理訴求。泛娛樂主播通過有意識的表演和做秀吸引觀眾,觀眾通過彈幕、虛擬禮物等方式呈現自我,二者表現出深度互動。因此,泛娛樂直播憑借內容廣泛、用戶異質和娛樂化等特點,順應時代潮流,處于直播行業發展的新階段。
1 表演區域:直播中的場景建構
戈夫曼是早期的“場景主義”者,他用戲劇理論描述社會生活中人們的交往行為,認為生活即舞臺,個體即演員。他把表演區域劃分為前區和后區,前區主要由舞臺設置及個人前臺構成,是演員扮演理想化角色的表演場景,后區則是演員休息,不被觀眾看見的后臺場景。泛娛樂直播中的表演場景作為虛擬的舞臺設置,主要體現為主播的真實場景與技術轉化的虛擬場景相融合而構成的舞臺。
1.1 技術設定的虛擬場景
美國學者斯考伯和伊斯雷爾在《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中指出:“互聯網即將進入新場景時代,由移動設備、社交媒體、大數據、傳感器、定位系統構成的‘場景五力會為人們營造獨特的在場感。”[3]泛娛樂直播的網頁設置通常為“窗口”形式,用戶能點擊感興趣的內容,“推門”進入直播間。直播間的窗口界面相當于“門”,點擊鼠標就是“推門”,用戶從自己所處的觀看場景進入主播展現的表演場景。戶外直播更把局限于電腦或手機屏幕的直播場景延伸到戶外,使用戶融入不同的新場景,實現主播場景的“虛擬到達”。另外,直播平臺“游客”用戶模式,即:使用社交賬號登錄,也增加了平臺與用戶的黏性,吸引用戶點擊收藏或關注主播,促使平臺推薦用戶感興趣的直播內容。2018年,武漢漢口江灘舉辦的斗魚嘉年華直播活動內容涵蓋電競、動漫、音樂、時尚等多方面。受眾能選擇觀看各種直播內容,同時獲得平臺的精準推送。打開直播窗口的大門,便可以構筑不同的新場景。
1.2 劇班共謀的表演場景
戈夫曼定義“劇班”為表演時相互協同配合的任何一組人[4]。在泛娛樂直播中,“劇班”角色主要由工會成員擔任(工會即直播平臺與網絡主播之間的中間機構,與娛樂圈的藝人經紀公司職能
相似[5])。不少新晉主播都會占據熱度值排名的前位,這離不開背后經紀公司及其工會的支持。泛娛樂主播通常被賦予舞臺和商業的雙重角色,其經紀公司對新晉主播進行專業培訓、推薦熱門,由工會負責維護主播的現場直播和粉絲互動。直播開始后,工會派遣其內部成員混跡在直播看客之中,為主播喝彩,對主播進行大額打賞,構建一種禮物滿天飛、主播高熱度的假象,意在吸引潛在用戶從眾打賞,幫助經紀公司獲得豐厚收益。因此,經濟公司對主播投入的商業資本比重越大,二者的共謀關系就越明顯,工會與主播的配合表演就更具迷惑性。劇班共謀的過程通常在后臺完成,不被觀眾知曉。他們往往自己撰寫表演“劇本”,設置特定表演情境,獲得受眾關注。
1.3 后臺前置的虛擬場景
泛娛樂直播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美食、旅游到興趣競技,不一而足。這意味著直播的真實場景在發生變化,直播內容也明顯區別于傳統的廣電節目。在擬劇論中,“前臺”“后臺”的概念使臺前幕后界限明晰,而在泛娛樂直播中,主播將直播視角私人化,將自己的后臺生活空間變為舞臺,把私人生活空間及行為展現給觀眾,在前臺的公共空間內談論原本屬于后臺的對話內容,完成后臺前置的轉換,導致前、后臺邊界逐漸模糊。在直播間內,虛擬時空逐漸侵入日常現實,導致前、后臺界限模糊。主播需要在多元自我中平衡妥協,修正自我行為,展現渴望被人發現、部分真實的自我,但這也會讓個體與現實的關系若即若離,逐漸麻醉人們的精神世界,使人暫時“迷失”。
2 表演策略:直播中的角色行為
人在不同情境下,其行為角色也會有所差異,他們依據不同的表演情境進行角色轉化。在泛娛樂直播的虛擬場景里,“明星主播”進行理想化表演、“邊際場控”進行補救性表演、“登場用戶”進行即時性表演。
2.1 “明星主播”的理想化表演
戈夫曼在擬劇論中提出印象管理的技巧,認為人們可以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行為,展現樂于被人接受的行為,隱藏屬于真實自我又不符合他人期望的行為[6]。泛娛樂主播通常為我們生活中的普通一員,在虛擬場景下他們是自帶光環的高位者,是直播間的“明星”。為保持觀眾的目光聚焦,主播精心裝扮外貌形象,反復斟酌直播內容,極力展示個人魅力,以維護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完美形象,期望獲得觀眾肯定。主播的理想化表演,即掩飾與社會規范、價值不一致的行為,有時也傾向、迎合那些已得到認同的價值。例如:無憂傳媒的人氣主播韓志恒是名在校大學生,憑借搞笑段子和幽默氣質擁有龐大粉絲群。韓志恒在接受沈陽晚報專訪時說:“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是個很靦腆的人,為吸引大量用戶關注,才轉向受眾普遍認可的幽默直播形式。”[7]然而,現實生活是客觀存在的,社會需要聆聽更多真實自我的聲音。直播間的主播似乎帶上了虛假面具,人際互動也好似一場“虛偽的表演”。長此以往,人們可能在習慣中逐漸隱匿真實的自我,逐漸喪失表達真實自我的勇氣。
2.2 “邊際場控”的補救性表演
戈夫曼提出某些人會被賦予指導和控制戲劇進程的權利[4]。直播間的“場控”就擔任這種安撫、制裁和協調的管理角色。場控具有禁言功能,能對直播間除主播外的不和諧表達或對直播場景造成威脅的行為進行管理和糾正。如果觀眾對場控的看法不一,則會造成二者關系的疏離,導致場控成為——協調管理的“邊際人”。表演過程中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當演員陷入險境“出丑”時,場控會幫助表演者補救表演。例如:斗魚女主播馮提莫是名才藝主播,憑借甜美的外表和嗓音位列直播榜首。在一次戶外直播的唱歌表演中,主播破音,表演失誤,而場控卻評論主播的失誤是“可愛”的表現,發送了比以往更多的彈幕和虛擬禮物,促使其他觀眾忽視失誤,幫助主播成功補救了此次表演。
2.3 “登場用戶”的即時性表演
在擬劇論中,沒有人是天生的演員,所有人的表演都建立在對角色認同的基礎上。只有完成對自身角色的訓練,才能在場景中完成角色扮演。演員和觀眾的界限在于他們是否表達[8]。發表評論或贈送禮物的觀眾是“登場演員”,用戶通過彈幕和虛擬禮物表達情緒,進行即時性表演。彈幕和虛擬禮物作為文本符號,其意義被舞臺上其他角色所解讀,就構成直播互動。主播是直播間聚焦目光的話語主體,主播表演時不僅會根據用戶的即時彈幕更改自己的表演內容,也會在直播屏幕出現彈幕或特效時,對“打賞”用戶進行情感回饋。此時,聚集在主播身上的注意力,就如聚光燈一般轉移至“登場用戶”,使之成為舞臺焦點,用戶的即時性表演就更加接近舞臺的互動中心。一般而言,在傳統的舞臺表演中,表演主體對表演內容和自我呈現方式有強大的控制力。而在泛娛樂直播中,主播和用戶的雙向互動增強,用戶的即時性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表演中的不可控因素,減少了主播對表演的可預期信息,導致表演可控性較弱。
3 表演動機:直播中的心理動機
泛娛樂直播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某種需求,導致人們在選擇觀看或進行直播時都產生了新的行為方式。泛娛樂直播中,主播和觀眾的行為動機主要為:情感交流、身份認同和物質追求。
3.1 排遣孤獨,情感交流
快節奏的生活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生活壓力,網絡媒介在豐富人們娛樂生活的同時抑制著人們的情感表達,使人們產生交往缺失的孤獨感。泛娛樂直播并不能根治人們的孤獨感,但能使人們分散對現實的注意力,暫時逃避現實的壓力。情感是個體無法剝離的一部分。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情感會促進人際間的互動。直播間是一個建立在實景基礎上的虛擬場景,聚合了所有“虛擬在場”的直播用戶,他們在“流動”與“聚合”的場景關系中分享彼此重疊的場景,完成虛擬社交;同時,通過彈幕等互動方式排遣孤獨、表達自我,分享彼此的信息、時間和情感,完成對彼此的“線上陪伴”,獲得內心的情感交流和自我滿足。
3.2 互動增強,身份認同
泛娛樂主播和用戶在彼此的雙向互動中構建臨時、短暫的新身份認同,在“看”與“被看”的主客體關系中實現心理上的“同類交互”。現實社會中的個體表達往往受階層、教育、收入等社會因素限制,使現實中的身份認同和自我呈現被約束。而在泛娛樂直播中,主播和用戶以興趣為互動交流的紐帶,讓擁有相同趣味、話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使進入直播間成為排他的重要手段,使在現實生活中缺少凸顯個性機會的人能通過評論、打賞的方式進行線上交往,肯定彼此價值,共享情感體驗,建構臨時、短暫的新身份認同。托馬斯是熊貓直播平臺的游戲主播,擁有169.4萬粉絲和8個粉絲交流群,直播累計收視3 269萬次[9]。志趣相投的游戲粉絲既是游戲的體驗主體,又是直播的觀看客體,他們彼此分享游戲攻略展現個人競技技術,以虛擬的游戲體驗分享相似或共同的經驗和情感,在游戲直播中鞏固自信,建構了一種暫時性、自我成就的新身份認同。
3.3 符號消費,物質回報
泛娛樂直播是互聯網時代的新產物,具有一定的經濟屬性。通常情況下,主播收入包括與直播平臺的簽約費和直播中獲得虛擬禮物的折現,高額收入吸引主播投身直播行業。另外,當用戶向主播送出一定量的禮物時,屏幕上會呈現特效,主播說出“打賞”用戶的名字,根據用戶打賞額度為其排名,激發用戶的消費欲望。實際上,用戶購買虛擬禮物的行為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而當虛擬的貨幣符號轉化為視覺符號時,這種模仿又具有更深刻的含義。因此,泛娛樂網絡主播為追求高額收入加入直播,用戶則在虛擬世界中滿足自我的消費欲望。
4 結束語
戈夫曼的“擬劇論”從微觀層面研究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行為,揭示了復雜個體的心理活動,為微觀社會行為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在泛娛樂直播興起之后,直播對人們的生活娛樂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擬劇論”對闡釋泛娛樂直播中的表演行為,依然有其適用性。從表演區域而言,泛娛樂直播構建了多重場景,營造了跨越時空的虛擬場景,使私人化的真實場景后臺前置,讓舞臺成為被劇班裝飾過的表演場。這些特殊的直播場景不僅滿足了“演員”的需求,同時也影響著“演員”的行為。主播、場控及用戶塑造自我角色并進行表演,主播擁有最高話語權,是呈現理想化表演的“舞臺明星”;場控負責協調、管理整場“演出”,以“邊際者”的角色對主播的偶爾失誤進行補救;用戶則通過彈幕、贈送禮物等方式登上直播舞臺,獲得其他用戶的目光聚焦,完成“即時性表演”。人們在其豐富的表演行為背后都有復雜的心理動機,主要為情感交流、身份認同和物質回報。在泛娛樂直播中,舞臺邊界模糊、真實人性缺失和表演可控性較弱等問題還亟待解決。
參考文獻
[1]2017年泛娛樂直播平臺發展盤點報告[EB/OL].[2018-05-31].http://www.iresearch.com/report/.
[2]2017年中國泛娛樂直播用戶白皮書[EB/OL].[2018-05-31].http://www.iresearch.com/report/.
[3]羅伯特·斯考伯,謝爾·伊斯雷爾.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移動、傳感、數據和未來隱私[M].趙乾坤,周寶曜,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4.
[4]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5]揭秘網絡主播背后那群人:經紀公司公會水更深[EB/OL].(2017-04-12)[2018-05-31].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7-04-12/doc-ifyeayzu7623706.shtml.
[6]田雅楠.戈夫曼“擬劇論”的再思考——從《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談起[J].中國報業,2017(8):83-84.
[7]騰訊網.95后學生高考后玩直播成網紅,兩個月賺15萬[EB/OL].(2016-09-02)[2018-05-31].http://new.qq.com/cmsn/20160902/20160902016121.
[8]楊冉.幕布后的表演——場景理論視角下的網絡直播[D].合肥:安徽大學,2017.
[9]主播排行榜:主播大數據服務平臺[EB/OL].[2018-04-16].http://live.chinaz.com/zhubo/panda/20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