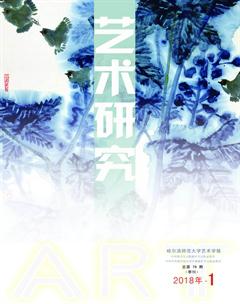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研究
張賓雁 汪磊
摘 要:本文圍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出現在黑龍江的地方藝術流派——印象派風景油畫展開研究,分析影響印象派風景油畫產生和發展的兩個主要因素,結合作品分析幾位油畫家的藝術特點,闡述這一地方藝術流派發展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黑龍江 印象派風景油畫 非主流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后期,在中國大陸的北部邊疆——黑龍江省出現一批有明顯印象主義特征的風景畫作品,雖然這些作品并非盡人皆知,這些作者也并非聲名顯赫,但他們的藝術實踐卻能說明,在獨尊現實主義和蘇派畫風的20世紀后半期中國美術創作中,也有另類探索的存在。只是由于地理區位和藝術風格的邊緣性質,了解這個特色鮮明的地方藝術流派的人并不多,相關研究也比較匱乏。本文主要研究兩個方面內容,一個是黑龍江印象主義畫家與其藝術特征,另一個是這種地方化的藝術現象有何歷史意義?
一、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的源起
黑龍江油畫家韓景生、孫云臺、李秀實、武英揚和劉治等人,在對景寫生中直接或大量借鑒印象派畫法完成的數量不算少的風景畫作品。他們對印象派畫法的接受和使用與他們的師承有關,也與黑龍江的自然環境有關。
韓景生(1912-1998)18歲時到俄羅斯畫家開辦的美專學習油畫,結識幾位俄人畫家,受斯捷巴諾夫(СтепановА.)和格林伯爾影響較深{1},與他們一起外出寫生,從完成的作品推斷韓景生受到俄僑畫家印象派外光表現技法的影響。三十年代末韓景生在哈爾濱工業大學任教,向同在此教授繪畫的日本名家佐藤功學習,佐藤功曾留學法國,受印象派影響{2}韓景生因此創作大量色調明亮光感強烈的印象派風景畫。
孫云臺(1923-2005)50年代結識在哈爾濱畫領袖像出名的日籍畫家古賀(古賀到中國時間不詳),向他學習繪畫基礎和畫像技能,之后古賀親自推薦孫云臺拜師哈市的俄僑外光派畫家洛巴諾夫(ЛобановМ.曾專門出版哈爾濱風景油畫集),洛巴諾夫作品色彩豐富,質感、量感和空間感的表現很強,孫云臺學習三年,能熟練運用外光派技巧{3},并喜歡在畫中強調肌理與筆法的特征。
李秀實(1933-)1956年考入中央美院,正是蘇聯專家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院教學的時候(1955-1957年),1959年李秀實進入董希文老師工作室中學習,董先生對于向蘇派、馬派一邊倒的做法不以為然{4},他鼓勵學生要接觸各種畫派,提倡藝術語言的多樣性,李秀實因此喜歡上印象派,并偷偷臨摹受批判的印象派畫冊,創作大量有印象派光色特點的風景畫。
武英揚(1936-2016)在魯迅美院附中時很喜歡印象派繪畫,在魯美上大學時師從烏叔養老師,烏叔養留學日本帝國美術學校{5},受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風格影響。后來在哈爾濱師范大學工作時,接觸另一位受印象派影響的留學日本的老師王微,在他指點下對印象派理解更加深入{6},之后一直采用印象派風格創作風景作品。
劉治(1941-)是自學成才的油畫家,六十年代結識張欽若和李秀實,深受兩人影響,(張欽若1929-2009,受蘇聯外光派畫家影響,欣賞印象派{7},早期作品對光色感覺敏銳{8},曾在哈爾濱藝術學院任教)。劉治的風景油畫作品強調色彩和筆法的表現力,具有印象派的光感和平面化特征。
黑龍江的地理條件指地貌和氣候上的獨有特點。因黑龍江地貌多樣,加上高寒區的氣候條件,樹木植被和自然光線都呈現豐富的變化,符合印象派捕捉自然景觀變化的創作目標,適合使用印象派的方法去表現。黑龍江印象派畫家就是圍繞當地景物色彩、光線和自然荒野等主題展開。韓景生用色彩記錄東北大地春綠秋黃夏風冬雪的這些變化{9}。李秀實說他的大多數風景畫就是由景物本身的造型、色彩所引起的沖動才畫下來的{10},例如林海雪原在日出日落時空氣特別清新透明,此刻的色彩艷麗無比,很少在其他地方看到這種景象{11},作品《八月興安嶺之三》就是表現雪地反射陽光的艷麗紅色與天空的灰綠形成強烈的補色對比效果。
版畫家晁楣曾描述北方森林四季的顏色截然不同{12}。用色彩表現自然光感正是印象派的主要手段,武英揚在柳樹河感受到陽光下的亮紅屋頂刺激周圍樹木綠得發藍而情不自禁地要去表現{13}。還有武英揚受印象派大師的城市風景畫影響,半個世紀里以哈爾濱中央大街為寫生對象,記錄哈爾濱獨有的異國情調{14}。
印象派風景畫多屬于借景抒情,主要表達對自然的熱愛之情。黑龍江的地貌原始,山川河流眾多,荒地廣袤,郝伯義描述北大荒是即荒蠻又迷人,天大地大、風大雪大{15},這種宏大的地域特點在幾位印象派風景畫家的作品中體現出同樣宏大雄偉的氣勢,例如《春到興安嶺》水平構圖,莊嚴雄偉,幽深的森林和遼闊的雪原蒼茫神秘。《草原黃昏》漆黑的平原大地上空無一人,濃重的筆墨豪邁而悲壯,充滿塞北邊疆特有的孤寂情感,這些地域特點令黑龍江大部分印象派風景油畫具有相同的審美特征。
二、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的藝術特征
與新中國美術中源于蘇俄式的現實主義風景畫不同,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在光線和色彩表現上有獨到的特征,其基本面貌是減弱素描關系,強調色彩的對比和平面效果,同時因為特定題材和創作者個人風格的原因,部分作品有深厚壯闊的美學傾向,有力地表達出黑龍江的自然面貌和沉浸其中的創作者個人的精神屬性。
一是撲捉現場的光線變化和空氣的清澈感覺,例如《四季春》(韓景生,1964年)表現開闊麥場的秋收景象,近處大地上陽光斑駁散落,省略房子和人物的細節,遠景灰蒙深遠充滿空氣感。《生產隊》(武英揚,1957年)描繪正午時的農家院,院中的牛、拉車和樹木簡約概括,唯有刺目的陽光布滿整幅畫面。
二是利用色彩對比,主要是補色、冷暖的對比關系,以強弱差別來界定空間順序。《街道》(劉治,七十年代末期)利用黃色和藍灰色對比表現冬季街道建筑和樹木的錯落關系,他同時期的作品《江岸》則采用濃重的大紅和土黃與淺淡的藍灰并置出強烈光感和空間距離。
三是運用厚密交織的筆觸以及線描、黑白對比等裝飾性手法增強畫面平面感,例如《鏡泊湖夜景》(韓景生,1957年),湖面和遠山采用裝飾性手法,表現水紋和樹叢的線描圖案感,減弱空間深遠效果。孫云臺《顧鄉大壩》(1973年)和《秋天榆樹林》(1975年)都是利用刮刀與筆觸的多樣變化,表現出掛毯一樣的豐富肌理。
在以上這些印象派風格特征基礎上黑龍江印象派風景還飽含厚重豪邁的激情。因北方地域性風景遼闊壯觀,蒼茫荒野,畫家為表達這種壯闊豪邁而采用沉穩色調和豐富多樣的筆法。例如《松雪》(韓景生,1967年)采用硬朗直率的筆觸表現雪后松柏堅毅挺拔的身姿,陰霾的天色、雜亂野草呈現出野外的荒涼與孤寂感。《春到興安嶺》(李秀實 ,1972年)中嫣紅的色調與寬闊的筆法體現林海雪原的壯闊厚重之美,《黑龍江金秋》(李秀實,1978年)中運用國畫的皴法表現山嶺的蒼勁雄偉。《幽靜的伊敏河》(孫云臺,1973年)以冷灰色調為主,刮刀重復涂抹顏色,經過反復疊加,產生豐富色層和樸拙效果,增強壯闊厚重的審美特征。
三、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的歷史意義
作為與當時現實主義藝術潮流不完全一致的藝術形式,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表達出個體藝術家最自然的真實感受和對非蘇俄式外來藝術技巧的學習和掌握,由此豐富了同時期的藝術創作樣式。這種源于地方美術家的藝術探索活動也能證明藝術史中的一種發展規律,即居于國家正統的主流藝術雖然能夠起到統領畫壇的巨大作用,但并非疏而不漏,邊緣和非主流藝術也能在合適的條件下得到發展,與主流藝術互為補充,使藝術發展呈現豐富多元之勢,其歷史意義有下面幾點:
首先是能夠表達真實的心理感受,他們的個性都有相似的地方,韓景生熱愛大自然,風景作品多為激情表現的油畫速寫{16}。孫云臺客觀再現對象的同時強調與自然的感情交流{17},作品表達出與個性相符的豪爽和雄放的氣勢{18}。李秀實認為風景更能反映自己的感受,使自己少說謊話{19}。武英揚通過寫生抒發內心的激情,體現耿直不流俗的個性{20},劉治盡管受到領導批評仍堅持對風景畫的形式探索{21}。幾位畫家都能保持相對較為獨立的心境,不追隨當時現實主義藝術潮流,筆下的風景即是胸中的真情流露。
其次,五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國油畫創作流行以巡回展覽畫派為標志的所謂現實主義畫風,重視教育作用,忽視審美功能。黑龍江這幾位油畫家以印象派手法描繪自然,追求形式美感,作品時代特征不鮮明,與北大荒版畫頌揚建設者的英雄氣概無法相比,基本上還是屬于借景抒情,形式探索多于社會意義,能彌補當時單一化的創作風格。例如:孫云臺的風景作品沒有太多文革時期流行的寫實畫風,而是一種舒放的心境{22}。在盛行以大主題人物畫為主流創作題材的時候,李秀實的《春到興安嶺》成為當時全國美展上唯一以自然風光為主題的作品{23},為當時繪畫體裁的多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24}。
最后是當時黑龍江文藝創作方向和美術活動都與時代主題密切相關,是黑龍江地方美術史的主要內容。而黑龍江印象派風景油畫以非主流的創作形式出現,其追求個性精神的藝術風格與政治氣氛下的主流藝術產生互補關系,不僅在形式手法上豐富了新中國美術史尤其是黑龍江地方美術史,還證明了在政治至上時代中看上去大一統的新中國美術創作中,不但有革命現實主義的主流藝術,也有并非完全革命現實主義的印象派藝術,后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只能算上非主流藝術,但它在客觀上起到了與革命化的主流藝術相輔相成、拾遺補缺的作用,填充了急劇發展的主流藝術所遺漏的藝術空白點,在新中國美術發展史中留下了一道異樣光彩。
注釋:
{1}《哈爾濱市志-文化文學藝術》,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2}《韓景生油畫集》,非正式出版物,2009年,第17頁。
{3}{22}《孫云臺油畫集》,非正式出版物,2009年,第14頁。
{4}{19}{23}馬鳳林《李秀實先生藝術訪談錄》。《中國油畫》,1997年第1期,第40頁。
{5}陳曉虎《留日學生與上海美專》中記錄烏叔養1933-1936年入日本帝國美術學校學習,《中國書畫》, 2010年1期。
{6}《武英揚畫集》,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0頁
{7}譚根雄《向前-永遠是戰士》。《美術》,2010年第8期,第67頁。
{8}錢流《胸中自然-張欽若風景油畫評析》。《美術》,2001年第9期,第64頁。
{9}劉曦林《韓景生藝術散論》。《韓景生油畫集》,非正式出版物,2009年,第13頁。
{10}李秀實《談談我對風景畫的一些看法》。《當代精神》,非正式出版物,2016年,第128頁
{11}李秀實口述《美麗妖嬈的大小興安嶺》。《當代精神》,非正式出版物,2016年,第60頁。
{12}晁楣 《我的版畫創作》。《龍江文史》,第九輯,第266頁。
{13}《武英揚畫集》。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10年,第164頁。
{14} 《武英揚畫集》。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10年,第12頁。
{15}郝伯義《拓荒者的藝術-北大荒版畫今昔》。《美術研究》,1982年第10期,第56頁。
{16}劉曦林《韓景生藝術散論》。《韓景生油畫集》,非正式出版物,2009年,第15頁。
{17}邵大箴《讀孫云臺的油畫》。《孫云臺油畫集》,非正式出版物,2009年,第5頁。
{18}劉曦林《孫云臺藝術散論》。《孫云臺油畫集》,非正式出版物,2009年,第12頁。
{20}《武英揚畫集》。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10年,第9頁。
{21}根據劉治老師口述,70年代他的風景畫曾被當時美協某領導批評是走形式主義錯誤路線。
{24}孫為民《李秀實‘京華遺韻系列作品研討會發言稿》。《美術》,1997年第1期,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