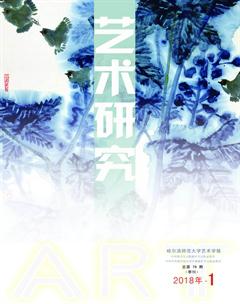論電影藝術中形式與內容的關系
羅碧瑤
摘 要:千百年來,學界關于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孰重孰輕的爭論從未偃旗息鼓。在電影藝術中,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問題更是關系到一個導演風格的形成。本文從內容與形式融合的成功之作《羅拉快跑》出發、結合電影藝術內容與形式關系的思考,并不斷尋找二者的契合點。
關鍵詞:內容 形式 電影 藝術
一、《羅拉快跑》:內容與形式的完美融合
湯姆·提克威的《羅拉快跑》是一部小成本的佳作,曾在世界各地斬獲了不俗的票房成績。影片講述了一個極為“陳舊”的故事:羅拉為了救她的男朋友要在10分鐘內籌到10萬馬克,于是羅拉為愛而開始奔跑。然而這卻是一部嶄新的電影,無論在視聽語言上還是結構上都具有先鋒色彩。導演能夠在1998年拍攝出這樣一部具有超前性與極強形式感的電影著實讓人欣喜和詫異。
這部影片無論在其內形式{1}還是其外形式{2}上都可圈可點。影片開頭第一個鏡頭是一個高度概念化的鐘表,預示著時間消逝與命運的未知性。接著是將近2分鐘的一個降格鏡頭,人潮快速涌動中將影片中即將出現的主要人物二次曝光在人群前,同時這個鏡頭中的色彩也經過特殊處理而呈現一種朦朧的淡黃色,只有即將出場人物的色彩異常鮮明。接下來導演將鏡頭一轉,變成一個動畫場景,一名紅衣女子在一個螺旋形狀的背景中不斷奔跑,好似在游戲中闖過一道道關卡。
影片角度在全知的上帝視點和羅拉的主觀視點之間來回切換。影片開頭處羅拉在腦海中搜索可以求助的對象時所使用的定格照片快速切換手法無疑是羅拉的主觀視點,觀眾可以感同身受的體驗到羅拉心中的焦躁不安的情緒。羅拉開始奔跑后的場景大部分為上帝視角,導演屢次將羅拉置于大全景中去,表現了羅拉的渺小與無助。這與游戲中游戲玩家看著游戲中的人物的設定也相符合,同時主觀視點又能將觀眾帶入游戲,增強觀眾的參與性。這樣一系列的游戲化場景是導演對電影可能性的一種探索,也是一種對生命可能性、世界可能性的探索。{3}
另外,影片色彩的使用也非常大膽。象征著熱情的紅色在影片中可謂被導演使用的淋漓盡致。首先羅拉接到男朋友消息的電話是紅色,奔跑中路過的消防車是紅色,錢袋的顏色也是紅色,當然最為突出的紅色是羅拉那一頭紅發,在人群中奔跑時顯得格外顯眼。這些紅色的運用象征著羅拉對男友熱情似火的愛,同時也是對羅拉奮力奔跑,永不放棄精神的歌頌。
影片為螺旋型結構,影片分為三段,三個故事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故事,羅拉在三段故事中的不同選擇召喚出這同一時間段的三種可能性結局,在每一段故事“闖關”結束時會回到開頭再次開始,直到二人都活著且成功拿到了10萬馬克贖金。這樣的一種結構時空在現實中顯然是不存在的,導演正是運用這樣一種結構形式解構了事件的嚴肅性,以一種更易于觀眾接受的頗具有時代感的形式表達出導演對人生未卜命運的哲理性思索。
我們能夠看出,《羅拉快跑》是一部內容與形式巧妙融合的電影,導演找到了電影藝術的主題內容與鏡語形式的精妙契合點,形成了其獨特的導演藝術風格。那么,電影藝術中形式與內容的關系究竟如何,導演應該做到拍出能為大眾所接受又不失風格的作品呢?筆者將在下文中論述。
二、服務于內容的形式或作為內容的形式
在經典電影觀念中,“題材決定論”似乎占據了更為重要的位子。形式必須要為內容服務,思想內涵比表現形式更為重要。愛森斯坦說:“你必須設法找到能表現出那些使你整個身心都為之感動的最初的生動印象的形式。這種形式必須能滿足你的意識。{4}”這種內容決定拍攝方式的思想對好萊塢電影產生過重大影響。例如希區柯克的懸疑片《精神病人》中出現過一段影響電影史的剪輯,即女主角浴室被殺一段。在這個片段中,導演運用了多種不同景別的鏡頭快速切換,來表現女主角被殺時候的驚恐。除此之外,他的影片多用好萊塢經典的三鏡頭法則來推進影片敘事,很少進行創新性實驗,影片的鏡語選擇也多為主題服務。
一些早期紀錄片也是一個形式服務于內容的佐證。與當代紀錄片不同,過去的紀錄片比如《北方的納努克》,使用的是傳統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全片幾乎關注不到鏡頭語言變化,導演弗拉哈迪將他的關注點全部集中在愛斯基摩人納努克一家的生活中去。影片就內容而言已經無可挑剔,而形式上缺陷得捉襟見肘的多。這樣的影片呈現在觀眾面前,觀眾更多會感到乏味,而降低了為其內容所吸引的可能性。
不過,傳統的電影觀念很快就受到了挑戰。尤其是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掀起了一場電影形式的革命,內容大于形式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沖擊。許多電影導演和理論家都聲稱電影形式同樣很重要,甚至比內容還要重要。曾經對愛森斯坦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俄國形式主義認為:形式是脫離內容獨立存在的,不是內容選擇形式,形式本身就是內容。法國電影大師羅貝爾 布列松稱:“藝術以純粹的形式震撼人心”{5}。蘇珊 桑塔格在談及布列松的電影創作時說:“他創造了一種完美表達他想表述的內容的形式,而且該形式與內容形影相隨,實際上,形式就是他想表述的內容{6}。”
早在20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先鋒派電影運動就已經對電影形式的革新進行過一番探索,布努埃爾、羅伯特·韋內、朗格、萊謝爾等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表現主義的代表性導演都極端強調形式。譬如影片《機械的舞蹈》,我們很難說清楚影片的思想內涵是什么,導演想要表達什么樣的內容,整部影片更像是一部對周圍事物的韻律性堆砌。
電影發展21世紀的今天,形式大于內容的現象更多演變成了技術大于內容。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3D、VR、數字化技術使得電影不斷發展出全新的創作形式,產生了所謂的“大片”。然而一些導演將技術的重要性過分強調,導致其拍出來的影片思想空洞、乏善可乘,只剩技術的空殼在苦苦支撐,這樣的電影也自然是不能為觀眾所喜愛的。例如,影片《環太平洋》在上映之時便打出了大制作的口號,宣傳也無非是大視覺場面,離不開如何拍攝無引力環境的問題,還未上映就已經戴上了形式大于內容的帽子。觀眾走進電影院大多只記住了打斗場面的激烈,滿足了視覺奇觀感受卻很少發現影片的劇情以及思想內核。
三、內容與形式對立統一
關于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問題,先秦時期的孔子有過精辟的論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說的“質”指的是內在,也就是藝術作品的內容,“文”所說的是文采,也就是是形式。孔子這句話則明確表示了內容與形式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應該是二者的精妙平衡。正如葛蘭西所強調:內容與形式兩者是有機統一的,藝術應當既有深厚的歷史內容,又能通過各種藝術手段把這些內容恰到好處的展現出來,使之具有高度的審美價值,從而使欣賞者從中獲得審美快感。而導演的藝術風格的形成的核心也正是要在如何拍與拍什么中尋找到合適的切入點,探索出一種獨特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統一。
縱觀中外異彩紛呈的電影寶庫我們不難發現,優秀的電影作品往往體現了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我們看電影《廣島之戀》,為了表現人類記憶與遺忘、夢境與現實、潛意識與行為的敘事主題,導演阿倫 雷乃采用了“意識流”式結構,通過大量閃回、非線性時間結構的運用,將電影引入另一個無比廣闊而深邃的世界——人的內心,開拓了現代電影的表現時空,使得影片能夠成為左岸派的代表之作。雷乃也因為對電影形式的極端注重而被稱為電影文體家,他使電影“成為一種可以在記錄與想象、情節劇和哲學之間自由跳躍的媒介”{7}
我國“第五代導演”的早期作品以其鮮明的風格特征贏得了世界電影人的關注。電影《黃土地》中,陳凱歌通過對構圖的陌生化處理,將鏡頭中的地平線或置于畫面的頂部,只留給天空一條縫隙,或讓地平線壓低到底部,使得天空占據整個畫面,以此表示天、地對人的創造力的束縛以及對生命力的禁錮。影片中黃色是大地的顏色,也是世世代代農民生命的顏色,是黃土高原希望的象征,表現的導演對黃土地的歌頌與敬畏之情。
四、結束語
綜上,內容重于形式,野也;形式終于內容,史也。由是觀之,電影藝術中的內容與形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合體,也是一名導演風格形成的核心。夸大或離開任何一個元素都不能成為經典之作。
注釋:
{1}即藝術作品的內在結構。
{2}即藝術作品的外顯的藝術語言。在電影藝術中表現為蒙太奇、剪輯手法、運鏡等。
{3}張藝莎. 從《羅拉,快跑》中淺析后現代語境中的電影美學[J]. 大眾文藝,2012,( 5):109.
{4} 【英】瑪麗·西頓,史敏圖譯.愛森斯坦評傳[M].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
{5}{6}{7}游飛.導演藝術觀念[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