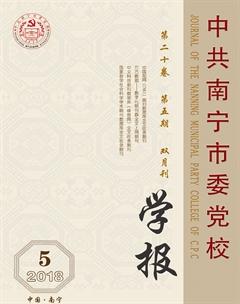《詩經(jīng)》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初探
艾新強
[摘要]《詩經(jīng)》中有大量涉及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詩篇,具有豐富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其尚賢重才、君臣共治;重民愛民、以民為本;撫主戰(zhàn)輔、妥處異族;愛國利國、生死以之等,對人們借鑒前人智慧和經(jīng)驗,以鞏固和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仍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關(guān)鍵詞]《詩經(jīng)》 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 尚賢 愛國主義
[中圖分類號]D6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9-4245(2018)05-0044-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5.009
《詩經(jīng)》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本屬文學作品,但其社會功用價值卻遠遠超越了它的文學藝術(shù)價值。孔子就曾指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而不達,出使四方而不能專對,學得再多也無用 [1 ]。這就突出強調(diào)了《詩經(jīng)》的治國理政和外交功能。孔子甚至還明確指出,《詩經(jīng)》具有興、觀、群、怨的四大功能,而其中的“群”,學術(shù)界一般解釋為聚攏、團結(jié)、合群。也就是說,《詩經(jīng)》具有妥善處理各種社會關(guān)系、聚攏人心、鞏固和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社會政治功用。這不僅是因為熟讀《詩經(jīng)》,可以提高官員的語言表達水平,有利于協(xié)調(diào)人際關(guān)系和國際關(guān)系,增強國內(nèi)外團結(jié)和諧,更是因為《詩經(jīng)》本身就有大量詩篇涉及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內(nèi)容,有利于人們借鑒前人的智慧和經(jīng)驗,更好地為鞏固和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服務(wù)。自《詩經(jīng)》問世以來,研究它的著作汗牛充棟,成果不可謂不豐碩,但至今尚無人對《詩經(jīng)》中蘊含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進行研究和論述,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為此,本文擬對《詩經(jīng)》中蘊含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進行初步梳理和探討。
一、 通過尚賢重才而達成君臣團結(jié),從而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內(nèi)部壁壘
君臣團結(jié)歷來都是治國理政所依賴的內(nèi)部壁壘,是團結(jié)人民、鞏固和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關(guān)鍵。而要實現(xiàn)君臣團結(jié),尚才重賢乃是最重要的途徑。孔子就曾深刻地指出:“舉直而錯諸枉,則民服;舉枉而錯諸直,則民不服。” [2 ]意即只有把正派的人提拔上來,放在邪惡的人之上,民眾才能服從,否則民眾就不會服從。
《詩經(jīng)》中有許多重才尚賢的詩篇。如《小雅·鹿鳴》言鹿得萍草為美食,以呦呦之聲呼喚其友的到來,以喻人君用美食、美樂、美酒款待賢者。“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意即誰若以美好的德行來對待我,示我以大道、正道,我就加以重用,言人君唯賢是用的迫切愿望;“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言人君有美酒招待嘉賓,且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則可效,可示天下之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3 ],是說人君愿意做出最大的努力來滿足嘉賓的需要,企盼賢能之士來輔佐自己,并竭盡全力為其提供治國良策。《秦風·蒹葭》中“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可看作主人公越過了迂回險阻的山路,一路追尋到最遠處的艱辛之苦;“白露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可看作主人公追尋“伊人”之長;“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 [4 ],可看作伊人的隱約縹緲和難以尋求之狀。詩中的“伊人”就是主人公朝思暮想的賢能之士。整首詩雖然顯示了追尋“伊人”的艱難及“伊人”位置的縹緲不定,但人君并未放棄對“伊人”的追尋,可見人君對賢者深切的思慕之情。《鄘風·干旄》詠唱的也是君主聘用賢能。先秦時代人君招賢納士,多以弓旌裝飾車乘,詩中“干旄”、“干旟”、“干旌”就是招賢者所制的儀仗彩旗;“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5 ],暗示衛(wèi)國官員出車聘賢場面的隆重和排場,寄托著君主的厚望和國人的期待。另外,《小雅·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式燕以衎”、“式燕綏之”、“式燕又思” [6 ],贊美君王能與賢者為伍,能夠禮賢下士;《小雅·南山有臺》贊美賢者,用美酒招待賢者,故賢者歸往也。
如果說上述幾篇詩往往以物起興、多用比喻,因而還顯得迂曲、委婉的話;那么,下面的幾篇詩就是直接贊頌賢君尚賢重才的。《小雅·菁菁者莪》稱賢人隱居山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我心則喜”、“賜我百朋”、“我心則休” [7 ],贊美君主能夠思賢若渴、延攬人才;《小雅·庭燎》稱“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8 ] ,贊美周宣王深夜燃起庭燎,盛宴迎接、款待賢者;《大雅·思齊》稱“古之人無斁,譽髦思士” [9 ],贊美周文王愛才育才、選賢舉能的圣德;《大雅·綿》稱“虞芮質(zhì)厥成,文王蹶蹶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10 ],不僅贊美周文王為政以德,使眾多諸侯歸附,而且人才齊備,故而得成大功,等等。由此可見,賢者是國家發(fā)展的強大推動力,無論是賢君或是賢臣,只有樂于與賢者為伍,樂于招賢納士并尊重賢能,賢能之士才會竭盡全力地為國家效力;也只有這樣,統(tǒng)一戰(zhàn)線才能得以鞏固,才會逐漸地強大起來,從而才能奪取并鞏固政權(quán)。
《詩經(jīng)》不僅贊美禮賢下士、選賢任能,而且對昏君重用奸佞、戕害疏遠賢臣以及奸佞禍亂國家的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這方面的詩篇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僅選幾篇進行論述。秦穆公卒,以秦國三位良臣奄息、中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而賦《秦風·黃鳥》。詩中寫道:“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維此仲行,百夫之防”、“維此鍼虎,百夫之御”。詩人呼天搶地地大聲呼喊:“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對此,秦穆公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責,《史記·秦本紀》就說他:“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因此,秦穆公“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 [11 ]周幽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貪戀女色,疏遠賢臣,重用奸佞,弄得民窮財盡,民怨沸騰。《小雅·十月之交》歷數(shù)自然災(zāi)異和“下民之孽” [12 ],明確地指出了周幽王寵幸褒姒與七個佞臣乃是國祚瀕危的直接原因。
盡管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社會歷史是復(fù)雜多變的,但從《詩經(jīng)》中的有關(guān)詩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國尚賢則興,近小人則危。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伊尹、仲虺,文王有姜尚、閎夭等賢臣,所以他們做到了由君臣團結(jié),而臣民團結(jié),而民族團結(jié),而國際關(guān)系和諧,并由統(tǒng)一戰(zhàn)線促進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被歷代人們所稱贊。
二、以愛民重民來調(diào)整統(tǒng)治者與民眾的關(guān)系,從而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礎(chǔ)
統(tǒng)治者與廣大民眾的關(guān)系,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關(guān)系。處理好這一關(guān)系,對于奪取政權(quán),對于國家政權(quán)的長治久安,都十分重要。在奴隸制社會里,統(tǒng)治者認為,國之存亡是由上天決定的,君主是“受天之命”治理國家、統(tǒng)治人民的,是代天行使權(quán)力的天之驕子。但周之代商,與商之代夏一樣,都變革了“天命”,這就使一些人感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于是他們在不動搖“天命”的前提下,強調(diào)了“人事”的重要性。同時,在推翻商王朝的斗爭中,人民群眾表現(xiàn)出了偉大的力量,這使周朝統(tǒng)治者認識到必須要重視和警惕“小民”的力量。《詩經(jīng)》在強調(diào)神的前提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民愛民,將民視為國本,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保民愛民
周初的統(tǒng)治者認為,“上天”只把統(tǒng)治人間的“天命”交給那些有“德”之人,一旦統(tǒng)治者“失德”,就會失去上天的認可和庇護,所以接受“天命”治理人間的統(tǒng)治者首先就應(yīng)該“敬天保民,以德配天”。《詩經(jīng)》中“德”字共出現(xiàn)了72次,其內(nèi)涵也很廣,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但其主要特點是對天要誠,對己要嚴,與人為善,施行德政,盡心治民等。只有施行德政,敬天保民,才能順天道,得民心。這既是上天意志的至善本性,又是人為了獲得天意眷顧所必須踐行的善的原則。所以說,人的“德”根源于天之“明德”,也就是說是否真正的“敬天”,要看其是否真正采取了“保民”的措施。“保民”就是“敬天”,“敬天”必須“保民”,人世權(quán)力的最高宗旨便是受命于天,為天養(yǎng)民。從古至今,人們習慣稱地方官為“父母官”,這大概源于《詩經(jīng)》。父母是子女的主宰,同時父母又疼愛自己的子女,所以對于民眾而言,父母官兼具了領(lǐng)導(dǎo)與愛護這兩項職責。而《詩經(jīng)》中多處都有“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 [13 ]的詩句,這些詩句將被歌頌者抬到了國之棟梁、民之父母的位置,表達了人們對愛民如子的統(tǒng)治者的愛戴。《大雅·泂酌》是召康公褒美成王的詩歌。詩中有“民之攸歸”、“民之攸塈” [14 ]之句。就是說,只要統(tǒng)治者施行仁政、德政,施德惠于民,民眾自然會安居樂業(yè)、感恩戴德,心悅誠服地前來歸附、柔遠能邇。
(二)重農(nóng)裕民
早在商周時期,統(tǒng)治者就認識到,民以食為天,國以農(nóng)為本,想要穩(wěn)固江山,就需要采取重農(nóng)裕民的政策。《詩經(jīng)》中保存了相當數(shù)量的農(nóng)事詩,如《周頌·噫嘻》說周王派農(nóng)官督查并指導(dǎo)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時農(nóng)夫,播厥百谷。駿發(fā)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15 ]。另外,還有《豳風·七月》、《周頌·載殳》、《周頌·良耜》等詩歌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統(tǒng)治者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農(nóng)民的重視。同時,為了讓農(nóng)民有一個更好的生產(chǎn)、生活環(huán)境,統(tǒng)治者在安排徭役、兵役時,注意不奪農(nóng)時。如《鄘風·定之方中》就記錄了衛(wèi)國營造都城的事情。詩起首就說:“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最末說:“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16 ]定,星宿名,又稱營室星,特指每年夏歷十月之交。因為此時乃是農(nóng)閑季節(jié),莊稼都已收割并脫粒入倉,天氣也還沒有轉(zhuǎn)冷。這充分說明在農(nóng)耕文明的作用下,統(tǒng)治者早就懂得了只有“揆之以日”、不侵奪農(nóng)時,才能不違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規(guī)律;只有尊重自然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才能使民眾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證,也才能協(xié)調(diào)好同農(nóng)民的關(guān)系,從而從根本上穩(wěn)固統(tǒng)治者自身的利益。
(三)君民和諧
愛民重民的目的是什么呢?君民和諧,君不擾民。這是《詩經(jīng)》所做的回答,如此明確的回答,在我國歷史上還是首次。如《大雅·板》:“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指出了君主只有實行恰當?shù)恼睿耜P(guān)系才會融洽,而正確的君民關(guān)系應(yīng)該像塤和篪一樣和諧其音,像圭與璋一樣契合不分,相得益彰。這首詩還提醒君主:“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17 ]善臣良民是國家藩蘺,大眾群黎是國家垣墻,諸侯大國是國家屏障,王族是國家圍墻,群宗之子是國家棟梁,若以德相和,國家便得安寧,不要使城垣毀壞,不要逞威,一意孤行。這段話提出要把民眾團結(jié)在自己的周圍,而團結(jié)的根本就在于“辭之輯矣”、“懷德維寧”,否則就會自毀城墻,使國家終歸滅亡。這里第一次把民眾比作國家的城墻,提出君民和諧的重要性,明確了實現(xiàn)君民和諧的根本途徑,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不容低估。
《詩經(jīng)》中的“民”、“庶民”,主要是指除了貴族奴隸主以及卿、大夫、士等官員以外的自由民,其中并不包括廣大的奴隸。在西周前中期,周朝統(tǒng)治者具有較強的愛民重民意識,自由民的生活相對比較安定,君民、臣民關(guān)系處理得較好,但到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時期,政治動蕩、戰(zhàn)爭頻仍、災(zāi)荒不斷,自由民的生活往往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這種情況,《國風》、《二雅》中有不少詩篇都有所反映,初步統(tǒng)計,《國風》中約有28篇,《二雅》中有22篇。例如《大雅·民勞》“民亦勞止” [18 ]、《大雅·板》“下民卒癉” [19 ]、《大雅·桑柔》“瘼此下民” [20 ]、《小雅·節(jié)南山》“俾民不寧”,“卒勞百姓” [21 ]等。最為可貴的是,《詩經(jīng)》對奴隸階級的痛苦生活及其愿望做了深刻的揭示,《魏風》之《伐檀》、《碩鼠》就是此類詩歌的典范。《伐檀》是一篇聲討奴隸主的檄文:“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22 ]本詩用回環(huán)重疊的章句形式,反復(fù)表現(xiàn)了奴隸們無限憤懣的思想感情,顯示出勞動者階級的初步覺醒,他們已敢于直斥榨干人民血汗的奴隸主了,已對那貧富懸殊、黑暗腐朽的奴隸制社會公開表示抗議了。《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23 ]這首詩把奴隸主比作可憎的大老鼠,對其不勞而食、驕奢淫逸的丑惡本質(zhì),進行了無情的揭發(fā)與尖銳的諷刺。而“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則充分表現(xiàn)了奴隸們要相率而去的反抗精神。雖然在當時的奴隸制度下,這種樂土是不存在的,但卻反映了他們樸素的階級意識。因此,如果說統(tǒng)治者的愛民重民是《詩經(jīng)》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那么,揭露統(tǒng)治者虐民、聲討奴隸主罪行就是其中的革命性精華了。
三、通過撫主戰(zhàn)輔來妥善處理與周邊民族的關(guān)系,鞏固民族團結(jié)
民族關(guān)系問題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問題之一,這一關(guān)系處理得如何,直接關(guān)系到政權(quán)的取得和鞏固,直接關(guān)系到民族的興衰和民眾的福祉。因此,我國歷代統(tǒng)治者都很重視民族關(guān)系問題。
堯、舜、禹對各諸侯和民族采取了恩威相濟,將軍事征服與政治安撫結(jié)合起來的謀略。堯在處理華夏聯(lián)盟與各諸侯、民族的關(guān)系時,能夠“光被四表”,“協(xié)和萬邦” [24 ],但三苗在江淮、荊州一帶多次發(fā)動叛亂,堯也對其發(fā)動征討,戰(zhàn)于舟水之浦,以服南蠻。這里的南蠻即為三苗及其附近的氏族部落。舜在位期間,對南方三苗仍然采取堯的恩威并施之策。舜派禹治水,但三苗不服,“苗頑弗即功” [25 ],不肯接受工作任務(wù)。因此禹打算征伐三苗。但舜認為德不厚而行武,不是最好的辦法,于是修教三年,執(zhí)干戚舞,有苗乃服。接著,舜命令分北三苗、更易其俗,有的分而治之,有的留在原地,有的流放,有的加以教化。為了對周邊三苗、北狄、南蠻、西戎進行自然同化,舜“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流放)于羽山,以變東夷。” [26 ]這樣不僅懲罰了犯罪的官員,而且有利于改變周邊各部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為了感化團結(jié)各部族,舜實施安撫政策,南撫交趾、北發(fā)、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fā)、息慎、東長、鳥夷,取得“蠻夷率服”的效果。禹在位時,也十分注重文治,對少數(shù)民族施行教化,但對不服教化,敢于稱兵作亂的部族,也不放棄武力征伐。禹曾征伐三苗部族,三苗首領(lǐng)被禹軍打死,苗軍潰退,從此一蹶不振,禹的勢力到達江淮流域,四方諸侯紛紛歸附。由此可見,憑強大勢力實行軍事征服和威懾,這是硬的一手,往往壓而不服;只有輔之以軟的一手,即施恩和安撫策略,才能贏得人心,實現(xiàn)爭取人、團結(jié)人的愿望,從而鞏固和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
《詩經(jīng)》繼承了堯、舜、禹處理民族關(guān)系的恩威相濟謀略,文德招撫為主,武力征伐為輔。西周和春秋前中期,少數(shù)民族即所謂的蠻、夷、戎、狄與華夏族交往比較密切,雖然二者之間有戰(zhàn)爭,但是他們?nèi)匀豢梢耘c華夏族通婚、朝拜周天子,甚至參加諸侯會盟。誠然,《詩經(jīng)》中收錄了不少民族戰(zhàn)爭詩篇,但這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觀念有關(guān),我們絕不能以此否認戰(zhàn)爭只是華夏族對待少數(shù)民族的一種輔助手段,其實質(zhì)仍是施行文德招撫。古人認為,兵為不祥之器,不可妄動,所以賓服遠人或四夷的方法是靠廣修文德,《周頌·綿》是一首歌頌太王古公亶父遷岐創(chuàng)業(yè)的史詩。《史記·周本紀》等史料記載:周人祖先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27 ]。后為避熏育戎狄攻伐,古公乃與私屬渡過漆、沮兩條河流,來到岐下。豳人俱扶老攜幼前來歸之,周邊其他邦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后來周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僅有百里,但他廣行仁政,懷柔西戎,不侮小國,不侮鰥寡,不仗勢奪人黍稷狗彘,深受廣大臣民和周邊諸侯擁戴,遂稱王天下。周武王滅商以后,欲廣布文王令德,吸引夷狄前來朝貢,但因路途太遠,未能即至,故致三年之喪,殯文王于兩楹之間,以俟遠方。這些記載可能有美化的成分,但至少反映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周的祖先為了生存和發(fā)展曾經(jīng)對周邊異族采取德化懷柔政策,而周初的統(tǒng)治者為鞏固周王朝的統(tǒng)治,繼承了這一民族政策。《魯頌·泮水》是一首寫魯僖公作泮宮平淮夷的詩。該詩第四章寫道:“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由于魯侯能明其德,效法先祖,所以結(jié)果是:“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28 ]勤勉的魯侯,能修文德,以懷遠人。“作泮宮”正是他廣施德政的具體表現(xiàn),故而淮夷聞之而懾服。德盛則政明,政明則和睦,這在“頌詩”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相反,德衰則政昏,政昏則心離,這在“國風”中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因此,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時期,華夏族與少數(shù)民族關(guān)系之所以緊張乃至兵戎相見,這與統(tǒng)治者自身德行的衰微有很大關(guān)系。
《詩經(jīng)》在堅持德主戰(zhàn)輔這一謀略時,特別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三種處理民族關(guān)系的成功模式。
(一)政治聯(lián)姻
政治聯(lián)姻是指兩個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結(jié)成的婚姻,是古人采取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手段之一。《詩經(jīng)》中記載的第一次政治聯(lián)姻就是周人和羌族聯(lián)姻。《大雅·緜》第二章:“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29 ]太王之妃姜女乃是羌族之女。太王與羌族通婚,是為了在西北方向?qū)ふ彝苏撸宕斯餐烙值遥⒐餐纯股坛5诙问菚x君與作為戎族的秦人聯(lián)姻。《秦風·渭陽》是外甥送別舅父的詩。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30 ]秦康公的母親秦穆夫人是重耳的姐姐。這篇詩就是秦穆公之子康公送晉文公重耳回國為君時所作。秦與晉接壤,秦與晉的聯(lián)姻在客觀上加強了兩國的聯(lián)盟,減少了戰(zhàn)爭,也促進了西方戎族與中原地區(qū)華夏族的交流、交融與合作。
(二)武力征服
周朝立國之初,殷紂王之子武庚與管蔡串通起來,聯(lián)合東方徐夷、淮夷發(fā)動叛亂,聲勢浩大,周公率兵東征,經(jīng)過三年苦戰(zhàn),終于平定叛亂,滅國十七,并迫使徐夷、淮夷、奄等族降服。《豳風·破斧》就是反映周公東征平叛這一史實的詩歌。詩中寫道:將士們努力奮戰(zhàn),砍壞了斧、斨、锜等武器,最終實現(xiàn)了“四國是皇”、“四國是吪”、“四國是遒”。 [31 ]“四國”是約數(shù),并非確指。就是很多諸侯和民族被征服,不得不歸順于周王朝了。《大雅·常武》是描寫周宣王親征徐戎的敘事詩。該詩第一、二章寫道:宣王和南仲率領(lǐng)的周軍“赫赫業(yè)業(yè),有嚴天子”“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致使“徐方繹騷,震驚徐方”。末章用欣喜的口吻寫道:“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32 ]徐國已經(jīng)被宣王的大軍征服,并來朝會同、歸附周朝,不再肆行邪僻了。
(三)武力懾服
《小雅·車攻》是描寫周宣王在洛邑大會諸侯、舉行大規(guī)模田獵活動的詩歌。古代天子、諸侯的田獵活動,常有軍事演習的作用,也有威懾安撫的作用。周宣王舉行這次活動,重在會諸侯,而不重在事田獵。借田獵以會諸侯,重修先王舊典,假狩獵以懾服列邦。因此,此詩前后雖然都寫狩獵之事,但其重點在于“會同有繹”和“展也大成” [33 ]這二句。《采芑》是寫周宣王大將方叔率軍威服荊楚之詩。詩中先極寫兵威之盛,“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最后寫“允顯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34 ]據(jù)前人分析,這次戰(zhàn)爭是以荊人自服而結(jié)束。武力懾服是一種“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必要手段之一,因為建立和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需要一定的實力為后盾。
四、歌頌熱愛祖國、生死以之,形成團結(jié)人民、凝聚人心的愛國主義主基調(diào)
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賴以生存與發(fā)展的一種基本精神,是有國有家者普遍具有的一種道德準則,也是古今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jié)人民、凝聚人心的感情紐帶和光輝旗幟。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如果追根溯源的話,這種傳統(tǒng)就是從《詩經(jīng)》開始奠定的。
(一)歌頌抵御外侮,維護華夏民族的統(tǒng)一
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中原地區(qū)不時受到周邊游牧民族的進犯和擄掠,其中尤以玁狁的破壞性最大、侵擾的時間也最長。《小雅·六月》是記述和贊揚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勝利的詩歌。第一章寫道:“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骙骙,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師,以匡王國。”詩句不僅道出了軍情緊急,有如烈火,而且還昭示這是一場保障國家安定的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正是因為這場戰(zhàn)爭的正義性,所以深得人民擁護,將士們上下一致,斗志旺盛,情緒昂揚,“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以奏膚公,”“以定王國” [35 ],贏得了巨大勝利。另外,《小雅》中的《出車》、《采薇》也是反映周宣王時期為保衛(wèi)國土、反擊玁狁侵略的愛國詩篇。《出車》歌頌了周宣王的大將南仲在“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玁狁入侵的危難時刻,率師出征,官兵同心協(xié)力,同仇敵愾,“不遑啟居”,“憂心悄悄,仆夫況瘁”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的英雄氣概以及“執(zhí)訊獲丑,薄言還歸”,“玁狁于夷”的赫赫戰(zhàn)功和勝利后的喜悅心情,“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自衛(wèi)戰(zhàn)爭是保家衛(wèi)國、抗御外侮的正義之戰(zhàn),它只有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才能取得勝利。周宣王時期,人民為了支持自衛(wèi)戰(zhàn)爭,參軍離家,不畏勞苦,“載饑載渴”,從“黍稷方華”到“載途”;從“楊柳依依”的新春時節(jié),到“雨雪霏霏”的歲末年終,與其他官兵一道出生入死,勇敢征戰(zhàn)。他們也思念家鄉(xiāng)和妻室父母,也想回去與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但是一想到“玁狁之故”,便打消了回家的念頭,顧全大局:“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36 ]他們十分清楚,是玁狁破壞了他們的正常生活和家庭幸福;因此,他們把仇恨集中在“玁狁”身上,自覺自愿地投入了戰(zhàn)斗,終于贏得了巨大勝利, 平定了玁狁的襲擾。《小雅·采薇》大概是周宣王時期出征戰(zhàn)士唱的歌,真切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玁狁犯邊的危急局勢,出征者的征戰(zhàn)過程,以及他們在歸途中的思想感情。“戎車既駕,四牡業(yè)業(yè);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展示了軍威之盛,也體現(xiàn)了將士們不顧個人安危、勇奪勝利的英雄主義精神;“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37 ]更是謳歌將士們英勇抗侮、不惜犧牲個人幸福的千古名句。民眾的愛國精神,既表現(xiàn)在參軍參戰(zhàn),直接投身反侵略戰(zhàn)爭方面,也體現(xiàn)在對正義戰(zhàn)爭的全力支持方面。《秦風》中的《小戎》和《無衣》就典型地反映了民眾對戰(zhàn)爭的積極支持。前詩描寫新婚丈夫為抗御外侮,保衛(wèi)家園,毅然割愛上了前線,這怎能不叫妻子“懷思”?每當她想起新婚生活“溫其如玉”的幸福情景,實在令人陶醉,而一想起他在遠方征戰(zhàn)歸期未卜的情形,又怎能不“亂我心曲”、牽腸掛肚:“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載寢載興。”但她一想到自己國家的軍隊軍威盛壯,丈夫英勇御敵的英雄形象,她就從內(nèi)心發(fā)出了由衷的贊美:“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38 ]。這就把思夫夸夫與頌揚國威兩種感情交織起來,把愛夫與愛國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并且做到了先國而后家,生動地表現(xiàn)了中國婦女不惜犧牲個人幸福,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賢淑美德。后詩則是反映了民眾參加衛(wèi)國戰(zhàn)爭的思想感情:“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39 ]人民和戰(zhàn)士親如一家,為了抗擊敵人,團結(jié)一致,并肩戰(zhàn)斗,同仇敵愾,為了國家的安寧統(tǒng)一,為了民族的生存發(fā)展,他們甘愿獻出一切。
(二)頌揚對祖國對故鄉(xiāng)的深情之愛
《鄘風·載馳》就是一篇充滿著愛國激情的偉大愛國詩篇。許穆夫人生于衛(wèi)國,得悉衛(wèi)國被狄人所滅,國人分散,廬于漕邑,她便決心沖破傳統(tǒng)禮俗的束縛和阻撓,親自前去吊唁其兄長戴公,并求助于大國齊,以拯救自己宗國。當她驅(qū)車來到漕邑時,驅(qū)車趕來的許國大夫所阻。于是她悲憤地寫下了《載馳》這篇詩,用以申述自己的救國之志及不可動搖的決心,批評指責許國大夫們拘于禮俗而因小失大的淺薄見識。許穆夫人沖破禮俗束縛,立志救國的非凡膽識與愛國精神,受到了歷代人們的贊許。國家危難之際,沖破重重阻撓,號召人民共赴國難,積極支持進步的正義戰(zhàn)爭,保家衛(wèi)國,這些無疑是愛國;而關(guān)注國家命運,支持統(tǒng)一,反對分裂,支持進步,反對倒退,支持安定,反對動亂,以及熱愛人民,關(guān)心人民疾苦,感世傷時,思鄉(xiāng)戀土,或緬懷故國,或為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而吶喊,也應(yīng)當屬于愛國主義的范疇。商朝滅亡后,宋微子啟偶過京城故址,看到往日繁華的宗廟社稷已成廢墟,只剩一片黍稷之苗,于是悲嘆商朝覆滅而寫下了《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40 ]詩人發(fā)出了悲愴的質(zhì)問:天呀,究竟是誰使繁華的京城化成了一片廢墟?回答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是統(tǒng)治者的腐朽,是外族的野蠻入侵!今天我們讀這首詩,對詩人的愛國之情依然感同身受。《衛(wèi)風·河廣》是流浪在衛(wèi)國的宋人所唱的思鄉(xiāng)曲:“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41 ]《小雅·黃鳥》也是一首流落異國之人的思鄉(xiāng)曲:“黃鳥黃鳥,無集于榖,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榖。言旋言歸,復(fù)我邦族……言旋言歸,復(fù)我諸兄……言旋言歸,復(fù)我諸父。”這兩首詩都深刻地抒發(fā)了詩人對故國的相思與苦戀。久居異鄉(xiāng)的游子,讀著這兩篇詩,也會體會到其中的愛國主義基調(diào),與詩人產(chǎn)生強烈的共鳴。
(三)熱情謳歌歷史上那些創(chuàng)造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人物及其業(yè)績,無情揭露并鞭笞昏君佞臣暴虐無道、禍亂天下的罪行
《大雅》之《文王》《大明》《棫樸》和《皇矣》《文王有聲》《生民》及《公劉》等,被人們稱之為周族英雄史詩。這些詩歌誕生于周人始祖后稷時期,教民始播五谷,到公劉遷豳,定居發(fā)展農(nóng)業(yè);到太王遷岐,創(chuàng)業(yè)興國;到文王求賢若渴,樂育賢才,廣施仁政,四方歸服;到武王滅紂,決勝牧野,肇造周朝,逐一進行了贊美與歌頌,肯定了他們篳路藍縷,艱苦創(chuàng)業(yè),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歷史功績。而另一些詩篇,如《小雅·正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仆,不輸爾載,終逾絕險,曾是不意。” [42 ]或直接痛斥殷紂王、周厲王和周幽王荒淫無道,聽信奸佞,縱容小人,施行暴政,最終禍亂天下,殃及眾生的罪行,或通過羅列種種亂象來勸諫這些統(tǒng)治者改弦更張,力挽頹勢;從另一側(cè)面,體現(xiàn)了《詩經(jīng)》愛國主義的主基調(diào)。《詩經(jīng)》中的愛國主義思想,哺育了我國一代又一代人民與惡勢力做斗爭,戰(zhàn)國時的屈原、漢代的賈誼、司馬遷,等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參考文獻]
[1][2]鄧伯球.論語通釋[M].北京:長征出版社,1996.
[3][4][5][6][7][8][9][10][12][13][14][15] [16][17][18][19][20][21][22][23][28][29][30] [31][32][33][34][35][35][36][37][38][39][40] [41][42]袁梅.詩經(jīng)譯注[M].濟南:齊魯書社,1985.
[11][26][27]蕭楓.史記全注全譯[M].延邊:延邊人民出版社,2000.
[24][25]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岳麓書社,1990.
責任編輯:李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