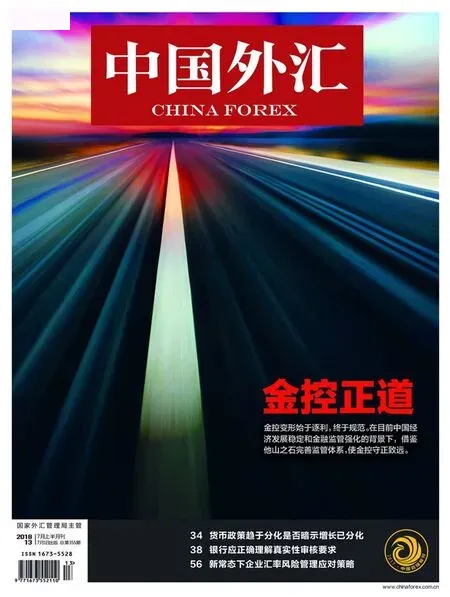澄清關于“實質重于形式”的幾個問題
文/肖勝 編輯/靖立坤
對于形式違規(guī)但實質合規(guī)的情形,不能因“實質重于形式”而免除其形式違規(guī)的責任。
目前“穿透式監(jiān)管” “實質重于形式”已成為監(jiān)管與檢查的原則。但在實際執(zhí)行中,對此仍存在一定模糊認識,不利于外匯業(yè)務監(jiān)管和檢查工作的開展,也不利于未來改革方向和政策的設計,亟待澄清相關認識。
“實質重于形式”原則下,“形式”是否仍然重要
筆者認為,“形式”是為服務實質管理而存在的,實質合規(guī)但形式違規(guī),仍應追究其責任。
從外匯監(jiān)管和檢查角度看,“穿透式監(jiān)管”或“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要堅持穿透業(yè)務的表面形式,結合資金來源、中間環(huán)節(jié)及最終去向,綜合判斷業(yè)務實質是否存在虛假、違法違規(guī)或不正當?shù)慕灰滓鈭D和目的。實踐中,業(yè)務形式和業(yè)務實質違規(guī)與否,可產生4種組合情形(見表1):
對于表1中情形1、3、4的處理,各方在適用“穿透式監(jiān)管”或“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上,一般不會產生分歧;但對于情形2(形式違規(guī)但實質合規(guī)),則容易產生模糊認識,即認為根據“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可不追究其形式違規(guī)責任。對此應從認識上予以澄清,即對于形式違規(guī)但實質合規(guī)的情形2,不能因“實質重于形式”而免除其形式違規(guī)責任。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從依法行政和執(zhí)法角度看,無論是形式違規(guī)還是實質違規(guī),均應追究法律責任。形式違規(guī)不予追究不符合法治精神,也不符合立法原意。
第二,有關業(yè)務手續(xù)、單證、賬戶管理、盡職審核等“形式”規(guī)定和要求,本身就是為了提高監(jiān)管效率、保障“實質”合規(guī)而設計出臺的,雖不能100%保證業(yè)務實質合規(guī),但能極大地提高監(jiān)管效率、保障多數(shù)業(yè)務合規(guī)。因此應通過監(jiān)管和檢查確保形式規(guī)定的貫徹執(zhí)行。
第三,一旦放棄對情形2的追責,會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意味著只要業(yè)務真實銀行就無需執(zhí)行形式規(guī)定,導致形式規(guī)定成為虛設;另一方面則意味著,監(jiān)管和檢查對違規(guī)的認定都不能再依賴于流程、賬戶、單證以及審核方面的形式規(guī)定,必須以穿透查實基礎交易虛假甚至是交易目的非法為根本要件。這不僅會加大監(jiān)管難度,而且意味著銀行問題只能通過對企業(yè)的檢查來反證,再也無法直接對銀行開展監(jiān)管和檢查。
銀行未盡職審核僅是形式責任嗎
在適用“實質重于形式”的過程中,還應進一步區(qū)分主體類型,充分認識到在同一個外匯業(yè)務中,企業(yè)和銀行具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實質和形式責任。
對于企業(yè)而言,作為外匯業(yè)務的發(fā)起者、控制者以及交易結果的承擔者,需要對其自身交易的真實性、合規(guī)性負責,其形式責任在于其是否按規(guī)定履行了相關手續(xù)、提交了相關單證、開立和使用了相關賬戶,以及是否滿足了其他程序性監(jiān)管要求等;其實質責任則在于,是否具有真實合規(guī)的交易背景、是否以欺騙等虛假手段或構造交易達到非法目的。
對于銀行而言,作為企業(yè)外匯業(yè)務的經辦者,由于本身并不是外匯業(yè)務發(fā)起、控制以及交易結果承擔的主體(故意與企業(yè)串通的情形除外),因而僅需對其經辦業(yè)務過程中是否合規(guī)盡職負責,相應,其形式責任和實質責任也均與企業(yè)不同。其形式責任在于,是否按規(guī)定落實單證審核、手續(xù)辦理、資金匯兌和結算、賬戶管理等程序性要求;其實質責任在于,是否對交易的真實合規(guī)履行了展業(yè)原則,是否對發(fā)現(xiàn)的或應發(fā)現(xiàn)的異常可疑情況進行了盡職審查。就后者而言,只要銀行未按規(guī)定盡職審核,客觀上造成企業(yè)違規(guī)業(yè)務通過審核并實施的潛在風險和隱患,銀行就構成了實質違規(guī)。至于最終企業(yè)行為是否真是虛假交易,并不會從實質上影響對銀行違規(guī)的認定,但會影響銀行違規(guī)導致后果的大小,進而影響對銀行的量罰(見表2)。

表2 銀行是否盡職審查的4種情形
以表2的情形2為例。銀行在為企業(yè)辦理業(yè)務過程中,雖然窮盡其手段做到了合理盡職審核,但最終在專項檢查中企業(yè)仍被查實交易背景虛假。在該情況下,雖未避免企業(yè)違規(guī),但銀行履行了其責任義務,應予以免責,不認定為違規(guī)。這里同時涉及以結果為導向的監(jiān)管問題(以結果為導向,主要指監(jiān)管部門讓銀行專注于試圖實現(xiàn)的結果,并據此自行決定實現(xiàn)結果的最有效方式)。以結果為導向并不意味著完全以最終結果作為銀行是否違規(guī)的判定標準,因為很多行政調查或刑事偵查手段遠遠超出銀行的權限,銀行不可能完全確保交易真實。
再看表2的情形3:銀行未對異常客戶及其業(yè)務可疑點盡職審核,盡管最終未能查實企業(yè)交易虛假,但銀行未盡職審核的行為客觀上存在放任虛假交易和違規(guī)業(yè)務發(fā)生的潛在風險和隱患,因此仍應認定銀行違規(guī)并予以處罰(未造成嚴重后果可從輕處理)。
在“實質重于形式”和便利化改革的要求下,是繼續(xù)堅持還是放松銀行審核
筆者認為,應繼續(xù)堅持優(yōu)化完善銀行審核。
第一,銀行審核不是簡單的管理形式,而是國際金融監(jiān)管的通行規(guī)則。無論是巴塞爾、FATF,還是各國金融監(jiān)管部門,都把“了解你的客戶(KYC)”與“盡職審查(CDD)”作為銀行業(yè)務辦理、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的重要規(guī)則,作為實現(xiàn)相關管理目標、防范相關風險的關鍵手段,且對銀行審核要求不斷趨嚴。外匯管理中銀行審核則是防范異常資金跨境流動的重要抓手,盡管不能100%地防范外匯違法違規(guī)行為發(fā)生,但確保了跨境資金流動的總體健康有序,也并不比國外監(jiān)管更嚴格,這從大量國外反洗錢監(jiān)管處罰案例中可以看出。
第二,銀行審核本質上不是便利化改革的障礙,而是適應我國當前可兌換狀況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采取了包括銀行真實性審核在內的大量政策措施,來維護尚未完全可兌換情況下外匯管理的有效性。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可兌換國家的情況和跨國企業(yè)訴求來評價和對標我國外匯便利化和銀行審核問題。在不具備完全可兌換基礎的情況下,為促進便利化而過度放松銀行審核,意味著外匯管理有效性的削弱和相關風險的放大,也喪失了部分監(jiān)管和調控的關鍵手段。
第三,應優(yōu)化和完善銀行審核,不能為了便利化而放松。當前外匯管理部分法規(guī)由于規(guī)定過于細致具體,不僅表現(xiàn)出彈性不足、監(jiān)管僵化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銀行業(yè)務辦理的便利化。對此,應優(yōu)化和完善銀行審核,更多運用結果導向的監(jiān)管理念,賦予銀行自主權和靈活度,使其專注于對風險的識別和風險管控措施的建立,自主決定審核要件和流程,從而為多數(shù)正常經營企業(yè)提供更多便利。但在此過程中,不能“過猶不及”,以放松銀行審核為代價來實現(xiàn)便利化,更不能主動放棄銀行審核的“前沿陣地”。這不僅無法管控風險,也與“三反”等其他領域監(jiān)管規(guī)則相悖。
相關操作建議
一是正確認識“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堅持形式違規(guī)和實質違規(guī)一起打擊,不能因為沒有查出實質違規(guī)結果而免除銀行形式違規(guī)的責任,切實維護外匯法規(guī)包括相關程序性要求的嚴肅性和執(zhí)行力,保障外匯監(jiān)管與檢查效率。
二是厘清銀行責任與企業(yè)責任的不同,加大對銀行審核責任的查處力度。要正確認識銀行責任,將是否盡職審核、是否造成風險隱患作為銀行實質性違規(guī)(而非程序性違規(guī))的考量因素,加大查處力度;將企業(yè)基礎交易是否虛假作為銀行違規(guī)后果的考量因素,切實督促銀行盡職審核,把好跨境資金流動閘門。
三是在深化改革和促進便利化中堅持將銀行挺在前面,切實防范風險。通過明確監(jiān)管目標,賦予銀行自行決定展業(yè)審核的權力,來優(yōu)化和加強銀行審核,達到既堅持防范風險,又避免僵化和教條導致的低效,為正常經營企業(yè)提供更多便利;同時,還應把握尺度,既不能簡單地以可兌換國家的情況來評價和對標我國外匯便利化程度,也要避免以放松甚至放棄銀行審核為代價來實現(xiàn)便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