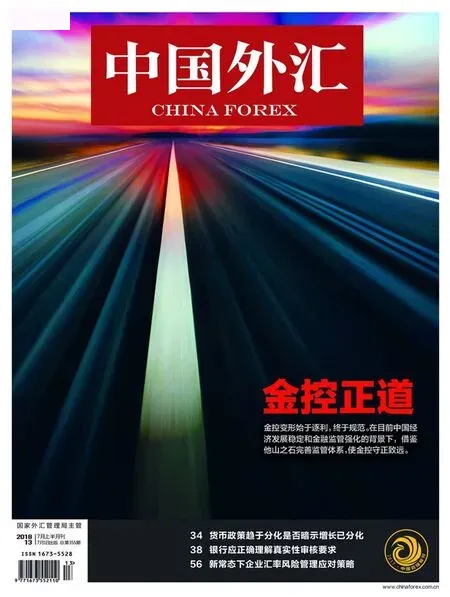探究通知行與轉讓行的關系
文/馮雪 編輯/韓英彤
明晰通知行與轉讓行二者之間的關系并合理處理相關業務,對可轉讓信用證業務的順利開展和規避相關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案例背景
國內某開證行開立一筆可轉讓信用證,通知行為A銀行。信用證指定通知行議付,同時還明確指定通知行為轉讓行。收到該信用證電文后,A銀行告知受益人,根據該行內部相關規定,不能對該信用證進行轉讓操作。鑒此,受益人與申請人溝通后決定修改信用證,添加第三方銀行B銀行來充當轉讓行,即修改信用證為指定B銀行議付,同時將轉讓條款修改為指定B銀行作為轉讓行。
然而,修改發出后,B銀行告知受益人,根據該行內部規定,其只有作為通知行時才接受指定作為信用證轉讓行。A銀行應受益人要求向開證行發送電文尋求再次修改信用證,將B銀行添加為第二通知行。但開證行認為,對已通知過的信用證增加第二通知行,不符合業務邏輯,也會產生相關風險。
案件分析
該案例出現兩個關鍵詞,即“通知行”與“轉讓行”。整個事件圍繞這兩方信用證當事人展開,厘清兩者的關系十分必要。
哪些銀行有資格擔任轉讓行角色
ICC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UCP600)第三十八條b款規定,轉讓行系指辦理信用證轉讓的指定銀行,或指當信用證規定可在任一銀行兌用時,開證行特別如此授權并實際辦理轉讓的銀行;此外,開證行也可擔任轉讓行。這就是說,三類銀行有資格擔任轉讓行角色——指定銀行、自由兌用信用證下特別被授權轉讓的銀行和開證行。
實務中,指定銀行往往是第一受益人的賬戶行,承擔向受益人承付或議付的責任;因此由指定銀行作為轉讓行,應第一受益人要求將信用證轉讓給第二受益人,是十分合理和順理成章的。而當信用證為在任一銀行自由兌用時,由于任何銀行都是指定銀行,為規避風險和加強業務可控性,需特別授權一家銀行作為轉讓行。至于開證行有資格成為轉讓行,則是由于轉讓信用證的指示不具有強制力,如果指定銀行或被授權轉讓銀行拒絕辦理轉讓,可能導致第一受益人的轉讓交易無法進行。因此,為保證信用證轉讓業務的順利開展,開證行也可以擔當轉讓行角色。
通知行與擁有轉讓資格的銀行具有怎樣的關系
第一種情況:當信用證指定在一家銀行兌用時,若指定銀行為通知行,則通知行具備轉讓行資格;若指定銀行非通知行,則該通知行不能參與轉讓(不是指定銀行),只能行使通知信用證的職能。此時,非通知行的指定銀行具備轉讓行資格。第二種情況:當信用證可在任一銀行自由兌用且信用證明確授權通知行轉讓時,如“通知行被授權作為轉讓行,轉讓業務發生時,轉讓行須通過經證實的電報方式通知開證行”,則通知行(在指定銀行之列)具備轉讓行資格;若信用證授權另一家非通知行的銀行轉讓,則通知行(未被特別授權)不能參與轉讓,只能行使通知信用證的職能。此時,非通知行的被授權轉讓銀行具備轉讓行資格。第三種情況:當信用證指定銀行、被授權轉讓的銀行不接受指定或授權而拒絕轉讓,或信用證限定開證行兌用時,則只有開證行具備轉讓資格。此時,只能是開證行“自開自通知”,即開證行與通知行為同一家銀行的特殊情況下,通知行才具備轉讓行資格。
通知行同時作為實際兌用銀行和轉讓行在實務中比較常見,是因為轉讓與通知、議付/承付、在同一家銀行辦理會更方便業務處理,簡化單據中轉流程;如果信用證后續有修改,經由轉讓行將修改通知第一受益人和第二受益人,可以有效增強業務的可控性。正是由于實務中信用證常常由通知行轉讓,這就容易給進出口企業造成一種“錯覺”,即通知行和轉讓行必須是同一家銀行。其實不然。國際商會在R246號意見結論中強調,自由議付信用證下,開證行必須指明轉讓行,通過某銀行通知的事實并不暗示該行就是被授權的轉讓行。由此可見,通知行擔當轉讓行角色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通知行作為唯一指定銀行,或者自由兌用信用證項下授權通知行作為轉讓行。而且,不管是哪種情況,通知行還必須是已經對信用證辦理了轉讓,該行才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了轉讓行。
至此,通知行與轉讓行的角色關系已然理清:當通知行為以上分析中三種情況下具有轉讓行資格的銀行,且實際辦理轉讓時,通知行才同時成為轉讓行;而轉讓行則并不必然為通知行。
再回到案例中:原信用證中,因指定通知行議付,因此只有通知行A銀行(同時為指定銀行)具有轉讓資格。但A銀行向受益人表示其拒絕對該信用證進行轉讓,而根據UCP600第38條a款關于“銀行無辦理信用證轉讓的義務,除非其明確同意”的規定,A銀行也確實無必須辦理信用證轉讓的義務。
于是受益人與申請人溝通后想添加第三方銀行B銀行來充當轉讓行,但B銀行為非指定銀行,不能滿足上述第一種情況下的條件。
為了實現B銀行成為轉讓行的目的,申請人與受益人協商后對信用證進行首次修改,將信用證修改為指定B銀行議付,同時將可轉讓條款修改為指定B銀行作為轉讓行。此時B銀行因成為指定銀行而具備了轉讓行的資格。然而實務中有些銀行對于是否接受指定進行信用證轉讓有其自身的特別風險內控標準,B銀行雖已具備轉讓行資格,但根據其內部特別規定,其須同時擔任通知行才接受指定對信用證進行轉讓。為實現這一目標,通知行A銀行向開證行發電文要求將B銀行添加為第二通知行,而開證行考慮到A銀行應已將信用證及第一次修改通知給了受益人,若再添加第二通知行可能會出現重復通知情況而易引發重復交單等風險,故表示拒絕。
經協商后,A銀行向開證行發送電文聲明其不會重復通知。在此條件下,開證行發起修改,將B銀行添加為第二通知行。而 B銀行因由此取得了通知行的地位,遂同意擔任轉讓行。最終,該業務得以順利進行。
案例啟示
通過以上對案例及相關慣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對于受益人來說,開證前應充分了解自己往來銀行對于信用證通知、議付、承付、轉讓等業務的具體要求,選擇恰當的銀行擔任信用證通知行、轉讓行等角色;同時,將銀行信息告知申請人,以便申請人給開證行準確的開證指示,保證信用證后續各環節的順利開展。
其次,對于開證行來說,應發揮自身專業優勢,為信用證申請人提供轉讓業務方面的咨詢及建議;如果出現指定銀行或被授權轉讓銀行拒絕接受指定或授權成為轉讓行的情況,開證行則可根據相關國際慣例,對申請人進行業務指導,為其與信用證相關方的溝通提供專業支持。此外,開證行對于受益人及通知行的特殊要求,也應進行專業分析,在盡量滿足對方要求以保證業務開展的同時,注意避免產生相關風險。
最后,對于通知行、指定銀行及被授權的轉讓行來說,各方銀行應充分了解國際慣例的相關規定,明確自身在可轉讓信用證業務中的權利與責任:轉讓行可以同時是通知行,但不必須是通知行。對于非自由兌用信用證,只有指定銀行具備轉讓行資格,若通知行為非指定銀行,則不應被授權作為轉讓行。各銀行只有了解相關慣例規定,按照慣例行事,才能確保操作的合規性。某些銀行如果對于可轉讓業務存在特殊規定與要求,應提前告知申請人與受益人,為其選擇正確的通知行、轉讓行提供參考,避免對后續業務造成不便與風險。如果被授權轉讓行拒絕進行信用證轉讓,相關銀行應通過電報等多種途徑積極溝通,盡可能在規避風險的同時,尋求促進業務繼續開展的解決方案。
總之,國際慣例為信用證業務的順利開展指明了原則性大方向,但實務中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信用證業務各當事人及相關方應以國際慣例為指導,結合實際情況,靈活應變、積極溝通。特別是作為處理信用證業務專業性較強、經驗較豐富的銀行,應及時為客戶提供準確、專業、高效的業務指導及建議,在業務之初就指導客戶制訂明確、清晰、合理的信用證條款,以避免后續再通過反復修改、往復電文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