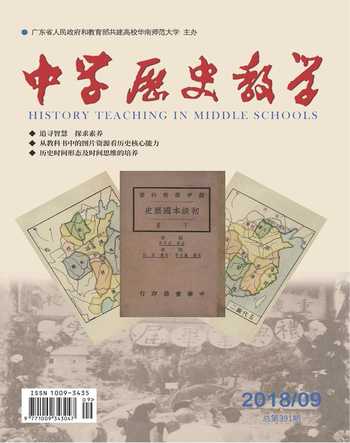追尋歷史人物足跡 激活傳統文化基因*
沈美蓮
基因,是內在的成因,是根脈,是抗體。正如人長得像自己的父母是因為遺傳基因的作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正因為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基因,才形成不同于他國、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習慣。[1]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脈就根植在傳統文化里,融入在人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中。
弘揚傳統文化是歷史教學的育人職責,也是歷史課程的學科優勢。2011年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強調“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傳承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使學生了解和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2]為了在歷史教學中更好地發揮歷史學科的人文特性,弘揚傳統文化的主流價值觀,筆者嘗試以人帶史,追尋歷史人物的足跡,激活傳統文化的基因,滋養歷史課堂的精神。以統編教材八年級上冊 第12課 《新文化運動》教學為例:
課標要求“知道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3]然而,何為“新”文化?“舊”文化又是什么?為什么要提倡新文化?如何看待舊文化?學生對這些問題都很陌生,更難以理解。鑒于此,筆者以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為主線,引導學生跟隨他的足跡,感受文化的力量。
1. 懵懂少年,在傳統文化中浸潤成長。1879年陳獨秀出生于安徽懷寧(今安慶市),當時社會最大的傳統就是“科舉”,從六歲到八九歲,由祖父直接教他讀書。陳獨秀與祖父的關系很緊張,嚴厲的祖父“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陳獨秀對母親十分敬愛,當祖父生氣時,他的母親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權威……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
2. 勵志青年,在家國情懷中啟蒙蛻變。1895年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戰敗的消息讓陳獨秀夜不能寐,他在《說國家》一文中寫道:“國家是個什么東西,和我又有什么關系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么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就在那時,他開始思考一個小國為什么會把中國打敗?他開始關注國家命運,主動接觸西方文化,參加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從1901年開始,陳獨秀先后五次到日本,除因去日本比較經濟和方便之外,主要是因為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就是一個由落后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他曾說:“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生也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
3.一枝獨秀,樹時代青年風標。1915年初夏,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此時距離甲午中日戰爭失敗20年,中華民國成立4年,大總統袁世凱正忙著復辟帝制。陳獨秀對中國的問題有了新的反思:“欲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須辦雜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創刊號印發,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一文,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揭開了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序幕。然而,《青年雜志》(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從創刊到1917年1月,都在上海出版,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主筆,儼然“獨人雜志”,寂寞獨行。正如魯迅后來所描寫的“不特沒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 。[4]
4.群星璀璨,閃亮文化“新”空。1917年1月,陳獨秀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后《新青年》雜志社也遷到北京,這成為陳獨秀一生的轉折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折點。1917年,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后兼文科教授;1917年7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后來成為陳獨秀與魯迅的牽線人;1917年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1918年1月,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當時像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這樣與陳獨秀志同道合的“新文化”好友還有許多,幾乎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從此,新文化運動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由寂寞的行者,蓬勃發展為輻射全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5.蕩滌神州,培育一代“新青年”。由于《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使新文化運動很快成為蕩滌神州大地的沖擊波,培養了一代“新青年”。例如:
魯迅,從《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在雜志上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及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還有多則隨感錄、通信等。特別是他的五部小說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巨匠地位。
毛澤東說:“……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1917年4月,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發表的《體育之研究》,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一生中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1918年4月,毛澤東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的團體“新民學會”。
《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周恩來立志救國,但對如何救國很茫然,直到1918年才漸漸走出痛苦。他在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5]
……
歷史是一部書,它書寫著前人的智慧、勇氣和毅力;足跡是前行的印記,它見證了前人的艱辛、奮斗和創造。千百年來,中國人創造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又塑造了中國人。因此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奧秘,就必須了解歷史實踐的中國人。同樣,要了解中國人,則必須懂得中國的傳統文化。
1.沿著人物的生活軌跡,還原傳統文化的時空坐標。所謂傳統文化,首先是指一種時間存在狀態的文化,即文化的過去式。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各個歷史時期的哲學、宗教、科技、教育、文學、藝術,以及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等。[6]探討傳統文化首先就要沿著時間的維度,尋找文化的蹤跡和成果。正如上述課例中節選了陳獨秀在1879年-1917年的時間維度,展示了他的求學、成長和工作,他所處的家庭、時局和朋友圈,凸顯了這一時空坐標下的教育、科技、文化氛圍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等。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在古代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統治中國長達幾千年。但近代工業文明使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的力量空前強大起來,并迅速走上了殖民擴張道路,將西方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陳獨秀所處的時代正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發生沖突的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遭遇西方近代文化沖擊的時代,在這一時空坐標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正是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是學習西方的近代化探索,陳獨秀等人將這種探索推向了縱深,從經濟、政治制度發展到思想文化領域。
2.追尋人物的視角路徑,感受傳統文化的基因裂變。從某種意義上看,“傳統”文化也是文化的現在式或正在進行式,即從過去一直綿延到現在的文化觀念。那些出現在過去且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文化,方能稱之為“傳統文化”。[7]例如:在教學《新文化運動》時,學生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幾乎一無所知,這些封建社會時期的核心理念之所以銷聲匿跡,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基因裂變的結果,具體來說,也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重大成果之一。上述課例透過陳獨秀的視角,使時代變遷歷歷在目:僵化落后的傳統教育,埋下了少年的逆反之心;列強欺凌下的失敗使大國形象轟然倒塌,刺激了少年的國家之思;革命的艱難曲折促使他探求救國之路;留學經歷使他找到了“民主”“科學”大旗;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使他走上了思想文化運動之路。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抨擊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恰是一場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裂變之戰。
3.思辨人物的心路歷程,感悟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傳統”文化,也可以是指文化的將來式,即對未來的文化建構產生影響的文化觀念,它們會成為未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8]今天的文化,是昨天的文化演變過來的;同樣,明天的文化,是今天文化的延續。因此,未來的傳統文化是怎樣的面目,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今天的傳承與創新,在這一方面,陳獨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運動堪稱傳承與創新傳統文化的樣本。聚焦陳獨秀的心路歷程,他對傳統文化表現出了逆反承受,即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承受著某些傳統,使一些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早已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母親的眼淚能打動倔強少年,正是他尊老孝親的傳統美德;甲午戰敗使他痛苦憤懣,一次次到那個曾打敗中國的“小國”學習,其內在動力正是他深深的家國情懷;創辦《新青年》,面對資金、人力、經驗等重重困難,他憑著熱情和膽識“革故鼎新”,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另一方面,他又以敏銳而挑剔的眼光,激烈反對那些他認為是錯誤的傳統,例如:厭惡《四書》《五經》和八股文,不滿祖父刻板的教學方式等。然而,對傳統文化的“逆反”,不僅需要勇氣和膽識,更需要有傳承與創新的前瞻和智慧:陳獨秀等人抨擊儒家道德和文化而非全盤否定孔子,提倡白話文也非全盤否定文言文,新文化運動在保留傳統文化優秀基因的同時,又注入了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的新鮮血液,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如今,我們正處在開放的時代,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各國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競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融為一體,我們既要用開放包容的心態擁抱世界,又要弘揚傳統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初中階段正是學生價值觀形成的模糊期,歷史教學必須發揮歷史學科的人文作用,挖掘歷史課程的傳統文化資源,將傳統文化的基因在學生的精神世界里激活并根植、發揚。
【注釋】
[1]葉小文:《激活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基因》,《 中國青年報 》2014年3月17日第2 版。
[2][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9頁。
[4]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274頁。
[5]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以上文中內容均選編自該作。
[6][7][8]朱漢民:《中國傳統文化導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