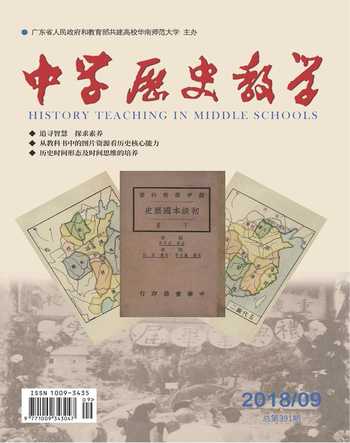歷史學科核心素養視野下的讖謠文化解讀
王穎怡

讖是中國古代常見的一種文化現象,多指能夠靈驗地預測未來的文字或符號。讖謠是讖的一種傳播形式,它具有讖的性質,又有自己的特點。在學習王朝更替歷史時,往往會看到讖謠。比如陳勝、吳廣起義之時,就有 “大楚興,陳勝王”的讖謠;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時,也有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一讖言;而隋唐之際,則出現了“桃李子,洪水繞楊山” 一類的“桃李子”讖謠。雖然讖謠不是中學課堂教學的內容,但是與所學內容相關,可以作為培養學生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素材。本文將對課堂知識進行拓展,對 “桃李子”讖謠進行解讀,從而發掘培養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方法。
一、時空觀念與史料實證是基礎
時空觀念是歷史最基本的特質,也是歷史學習的起點。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間和地點上發生的。只有將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放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去思考,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而可靠的史料則是得出正確認識的依據。“桃李子”讖謠產生于隋末唐初,要理解“桃李子”讖謠就要將其置于這一時空背景之中,并合理運用相關史料。
隋煬帝即位后,“初造東都,窮諸巨麗……長城御河,不計于人力,運驢武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傷于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挽秣,水陸交至”[1]。其暴政導致百姓奮起反抗,進而造成了隋末的動蕩局勢,為“李弘之讖”的傳播與“桃李子”讖謠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與此同時,李氏勢力逐漸抬頭。“由于關隴集團仍是當時政治社會的主導者,在此集團之中最有可能承繼隋王朝者,在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之中,以李弼、李虎、李遠三家后裔最有可能。”[2]李弼是八柱國之一,其去世之時“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旗,陳軍至墓。”[3]可見其圣眷之深、權勢之盛;李虎一族同樣權傾朝野,《舊唐書》記載:“皇祖諱虎,后魏左仆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為‘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4];李遠、李賢、李穆三兄弟更是深受高祖寵信。高祖“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侄女”[5]。其弟李穆則因為“密表勸進”而“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 ”,“其一門執象笏者百余人,貴盛當時無比”[6]。陳寅恪就曾感慨:“大約周隋李賢、李穆族最盛,所以當時有‘李氏將興之說。”[7]
隋煬帝的暴政和李氏勢力的膨脹使“桃李子”讖謠從李弘之讖中抽離出來。這一時空背景是把握“桃李子”讖謠與其產生的特定時間、地點之間關系的基礎。梁啟超曾說:“自然科學的事項為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反是,恒以時間空間關系為主要基件。”[8]在理解“桃李子”讖謠時必須基于相關史料去把握歷史文化的時空特性,歷史學習之中亦是如此。
二、歷史解釋是關鍵
正如英國史學家卡爾所言:“歷史就意味著解釋”[9]。歷史學習的過程實際上是依托教材,在史料實證和歷史理解的基礎之上建構歷史解釋的過程。新版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頒布以后,歷史解釋更是成為了劃分學業質量水平的重要標準,可見其重要性。在“桃李子”讖謠的解讀之中,最為關鍵的也是對歷史的解釋。
“桃李子”讖謠最早的應讖者是李敏。《隋書》記載:“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10]此處只提到李敏小名“洪”字應讖,并未提及“桃李子”讖謠。而《舊唐書》明確記載:“隋末有謠云:‘桃李子,洪水繞楊山。煬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11]。可見李敏所應之讖即“桃李子”之讖。根據唐長孺先生考證,北魏獻文帝名“弘”,為避諱,改“弘”為“洪”。而且魏末就有“陽城李洪”反叛之事,“李洪”可能就是“李弘諱改”[12]。所以“桃李子”讖謠中的 “洪水”極有可能指的是李弘。而“桃李子”讖謠則是“李弘之讖”的一個變種。
“桃李子”雖然是由“李弘之讖”演變而來,但“桃李子”更容易為人所用,所以在預言“李氏將興”的讖謠之中脫穎而出。繼李敏之后,又有李密應讖。《資治通鑒》記載:
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里,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里”,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于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 [13]
這一記載與“洪水繞楊山”之讖相比,對“桃李子”讖謠進行了一定的變通。融入了隋煬帝南下揚州之事,并將讖謠對應在了李密身上。此外,《隋書》也提及了李密應讖之事: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里。莫浪語,誰道許。”其后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為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群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后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14]
這一記載也在原來版本上進行了改造。“鴻鵠繞陽山”,象征著李密從陽城山而來。“莫浪語,誰道許”之句則對應李密和宇文化及建許之事。整體而言,李密所應之讖與社會現實聯系更加緊密,與李密的貼合程度也更高。這也說明“桃李子”之讖已經開始擺脫“李弘之讖”的影響,更多地受到社會現實的左右。
《大唐創業起居注》中也有關于李密應讖的記載:“密是逃刑之人,同守沖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于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15]溫大雅提到,李密應“桃李子”之讖,隋主尚且懼之。這些記載看似在為李密搖旗吶喊,但實際上要證明的是“桃李子”讖謠的真實性。當是時群雄逐鹿天下,李唐政權雖然實力強勁,但只是眾多割據勢力中的一個。所以李淵仍然要借助李密應讖之事對“桃李子”等建構其政權合法性的因素進行宣傳。
由此可見,不同的政治勢力對“桃李子”讖謠的附會使其有著多個版本,根據不同的史料我們又能對其進行不同的解讀。在探討“桃李子”讖謠的演變與解讀問題的過程之中,歷史解釋的能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歷史解釋落實到歷史學習之中,就要求我們“通過查閱歷史資料尋找證據,鑒別資料的真偽和可靠性,將資料加工整理,解答歷史問題,形成自己對歷史的認識”[16];落實到歷史教學之中,則要求教師培養學生搜集、篩選、使用史料的能力,做到史由證來,論從史出。
三、唯物史觀是核心
西方史學觀念的傳入帶來了諸多不同的看待歷史的視角,比如近代化史觀、全球史觀等,但是在中學歷史教學之中仍然要堅持唯物史觀。因為唯物史觀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種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的歷史觀念。堅持唯物史觀體現了我們對于歷史的尊重,也有利于我們得出正確的歷史認識。在理解讖謠文化,尤其是“桃李子”讖謠時更應是如此。
唐《五行志》云:“高祖諱淵,洪水也。”[17]這是李淵對“桃李子,洪水繞楊山”一讖的附會。李淵家族擁有崇高的社會威望和強大的政治權力,天意是將李淵推上皇位的重要力量,而“桃李子”讖謠則是天意的體現。《大唐創業起居注》又云:
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里。”案:李為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歌在耳……自爾已后,義兵日有千余集焉。[18]
此處溫大雅將“桃李子”的“李”解釋為國姓,將“桃”解釋為堯的姓氏,意在將李唐政權比附為人們心中的理想社會。描述晉汾地區百姓目睹讖謠靈驗時的歡欣雀躍之狀以及群眾歸附李唐之事,則表明李唐政權受到百姓擁戴。溫大雅對于“桃李子”的再解釋,使得原本為李密“量身定制”的“桃李子”讖謠成為了李唐政權合法性的重要證明。
不難發現,李敏和李密所應之“桃李子”讖謠,最終都被附會在了李淵身上。那這是否表明李淵就是“承天命”之人呢?回答這一問題就需要我們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科學地分析讖謠文化的本質。李淵在隋末起義之中幾乎處于一個領導有成功把握的叛亂的理想地位。 [19]如果再加上廣大民眾的支持,李淵就離成功更近一步了,所以李淵一直在宣傳自身的合法性。而“桃李子”讖謠只是李淵建構其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并不是所謂的“天命” 。在研究“桃李子”讖謠的過程之中,我們需要積極用聯系、發展的觀點看待讖謠文化,采用科學的方法論研究讖謠文化,通過建立史料之間的聯系深入理解讖謠文化的內涵。同時也要堅持唯物主義的觀點,揭開讖謠文化的神秘面紗,了解其背后的政治意圖以及其工具本質。只有這樣才能對于歷史發展形成正確的認識和理解,掌握客觀、準確的歷史知識。
四、結語
歷史學科核心素養是“學生在歷史學習中獲知的關鍵能力和個人修養品質, 是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方面的綜合體現”[20]。無論是解讀“桃李子”讖謠還是解決其他歷史問題,我們都應該充分利用學科核心素養,以時空觀念和史料實證為基礎,堅持唯物史觀,對歷史事物進行科學的歷史解釋。
【注釋】
[1]魏徵:《隋書》卷24《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672頁。
[2]毛漢光:《李淵崛起之分析 論隋末“李氏當王”與三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0年,第1037-1049頁。
[3]李延壽:《北史》卷60《李弼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0頁。
[4]劉昫:《舊唐書》卷1《高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頁。
[5]令狐德棻:《周書》卷25《李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417頁。
[6]李延壽:《北史》卷59《李賢傳》,第2116頁。
[7]陳寅恪:《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6頁。
[8]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
[9](英)卡爾著,吳柱存譯:《歷史是什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1頁。
[10]魏徵:《隋書》卷37《李穆傳》,第1124頁。
[11]劉昫:《舊唐書》卷37《五行志》,第1375頁。
[12]唐長孺:《唐長孺社會文化史論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7-182頁。
[13]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3《隋紀七》,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709頁。
[14] 魏徵:《隋書》卷22《五行志》,第638頁。
[15]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頁。
[16]鄭林:《中學生歷史學科能力構成及表現研究》,《課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8期。
[17]彭定求:《 全唐詩 》(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39頁。
[18]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1,第11頁。
[19](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52頁。
[20]朱漢國:《淺議21世紀以來歷史課程目標的變化》,《歷史教學》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