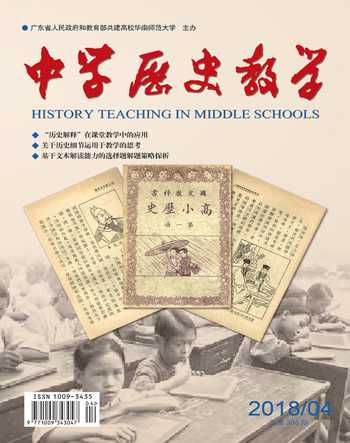歷史解釋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的運用
張茂源
在教育部最新頒布的《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中“實施建議”部分明確指出:“學生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發展,絕不是取決于對現成的歷史結論記憶,而是要在解決學習問題的過程中理解歷史,在說明自己對學習問題的看 法中解釋歷史。教師要認識到,任何一種教學方法的實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與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可見,讓學生在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形成歷史認知,培養歷史解釋的能力是歷史教學的重點。如何培養學生的歷史學科問題意識和歷史解釋能力,筆者以人教版“美國三權分立”教學為例,進行了一次探索。
一、巧妙的設疑——歷史解釋培養的前提
三權分立是美國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1787年憲法對三權分立體制做出了相對明確的規定,然而作為權利制衡重要一環的“司法權對于其他權力的制約在憲法上沒有明文規定”[1]。事實上,包括聯邦最高法院對國會和總統進行違憲審查權在內的制衡權,都是在1803年大法官馬歇爾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中所確立的。“馬歇爾借用判例法首次明確地提出了法律解釋權歸司法機關的原則” [2],這就與人教版高中歷史教材中關于 1787年憲法“最高法院……對法律具有最高的解釋權”的敘述存在著明顯的偏差。這為本課培養學生歷史問題意識,進行歷史解釋創造了條件。
在引入1787年憲法原文后,引導學生初步構建憲法所建立的三權分立體制。隨后,將學生帶入一場建國之初涉及權利制衡的案件之中,讓學生當一次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的“構建者”。
在1800年底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聯邦黨人亞當斯未獲連任,共和黨人杰弗遜獲勝。在亞當斯總統任期即將屆滿之前,亞當斯迅速提名委任多位聯邦黨人出任聯邦法官,并迅速獲得由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批準。在任職總統的最后一天,他正式簽署了這些法官的委任書。隨后國務卿抓緊送發委任狀,但是由于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仍有幾位法官的委任狀未能送出。其中一位就是馬伯里。杰弗遜就任總統后,下令立即停發尚未發出的法官委任狀。馬伯里隨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最高法院對新國務卿麥迪遜下達法院強制令,強制他向馬伯里等人發出委任狀,故此案被稱為“馬伯里訴麥迪遜”。
馬伯里等人的請求依據的是美國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規定:在法的一般原則和慣例允許的情況下,最高法院有權向美國管轄下的法院或官職人員發出強制令。
——摘編自任東來等:《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基于上述材料和分析,問題自然形成:在當時環境下,大法官馬歇爾如何審理此案?判決的依據是1787年憲法嗎?根據材料所顯示的內容,學生比較容易得出馬歇爾會依據《司法法》第十三條規定判決國務卿應當將任命狀下發給馬伯里。憲法因對此訴求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故無法適用。
然而,客觀的歷史事實是大法官馬歇爾卻做出了“扣押他的委任書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而是違背了既得法律權利”[3],但卻并不同意下達強制執行令的裁決。課堂教學中問題意識再次形成,并最大程度激發學生歷史學習的興趣,為本課教學的關鍵——探尋歷史的解釋創造了條件。
二、合理的解釋——歷史解釋培養的關鍵
歷史課堂教學的本質是求真。面對教材中的歷史敘述與客觀史實之間的差異,學生認知與歷史判決的差異,還必須回歸到特定的歷史時空中,深入分析美國歷史上的經典司法案件——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進行合理的歷史解釋。此時,教師應發揮必要的作用,巧引相關的史料,借用歷史的細節,“使已經逝去了的歷史重現出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原狀,使學生感受到歷史的真實。”[4]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進行合理的解釋,邁出歷史解釋培養的關鍵。
馬歇爾認為,如果按照這一規定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則違反了美國憲法的規定。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對于涉及大使、其他公使和領事的一切案件,以一州為當事人的案件,最高法院有初審管轄權。對于前述一切其他案件,最高法院有關于法律與事實的上訴管轄權。”馬歇爾認為,馬伯里的法律請求顯屬憲法所指的“其他案件”,也就是說,最高法對此案只有上訴管轄權,沒有初審管轄權。
——摘編自徐炳:《美國司法審查的起源——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述評》
基于材料的展示,我們知道馬歇爾做出這樣判決的緣由。但同時也會引發新的問題,法官馬歇爾的判決引發了國會制定的法律與憲法在司法案件的適用時發生了沖突怎么辦?
[判詞]“將既定規則適用于特定案件的人必然要解釋這種規則。如果兩個法律相互抵觸,法院必須決定適用其中哪個法律。如果一部法律是違憲的,而該法與憲法都適用于同一案件,那么法院必然要么無視憲法,適用該法,要么無視該法,適用憲法。”
——摘編自徐炳:《美國司法審查的起源——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述評》
學生在閱讀馬歇爾判詞的基礎上認識到,這關鍵要看法官的抉擇。基于憲法的地位,法官的選擇必定是國家憲法。那么又涉及到另一個基本問題,誰有權認定什么是違憲的法律?在這一案件中聯邦黨人大法官馬歇爾毫無疑問的直接指出——聯邦法官擁有這一權利。這也符合了當時以漢密爾頓為首的力求實施三權分立體制的聯邦黨人對“法院必須有權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如無此項規定,則一切保留特定權利與特權的條款將形同虛設”[5]的一貫態度。
通過對案件判詞的巧析,最終讓學生在歷史解釋的過程中認識到了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的確立,不僅僅基于美國的1787年憲法,還有賴于像馬歇爾一樣杰出的法官在涉及國家體制的一系列案件中努力維持權力制衡的司法實踐,逐步共同構建、維護并發展起來了具有美國特色的并相對完善的三權分立機制。這樣就避免了基于教材敘述所形成的對歷史認知的機械性,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對學生歷史解釋能力的培養。
三、不斷接近歷史真實——歷史解釋的靈魂
在問題的引領下,通過不斷的歷史解釋,學生對美國三權分立體制建立的歷史認知更加清晰。1787年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使得司法在三權中處于弱勢,使三權分立下的制衡形同虛設。但大法官馬歇爾卻憑借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巧妙的避開了與國會和總統直接沖突,捍衛了相對獨立于選民、又比較弱小的法院系統的權威,補齊了憲法所確立的三權分立體制中缺失的“短板”。此后,美國聯邦法院系統不斷借用判決所形成的法律效力,將制衡國會乃至總統的重要權利——法律解釋權和違憲審查權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國憲法雖然沒有一字提到司法機關對立法的違憲審查,實踐中這一制度都得到認真的執行,成為美國憲法一大特色。”[6]這樣,基本實現了歷史解釋“不斷接近歷史真實”的學科素養培育要求。
基于歷史學科求真的本質,教師應當對學生指出,對于馬歇爾的判決所形成的司法解釋權以及違憲審查權,自一誕生就飽受政治家、法律人士的爭議。如吉布森指出“司法機關則是特殊的部門,可以修改立法,可以糾正立法機關的錯誤,我們在憲法的哪個條文中可以找到這種特殊地位呢?……宣布一部根據憲法規定的形式制定的法律無效,這不是篡奪立法權嗎?……司法機關的職責是解釋法律,而不是審查立法者的權力。”[7]然而,支持馬歇爾的判決始終是美國憲政發展中的主流。隨著歷史的不斷向前發展,該案對三權分立體制形成的歷史意義將會在現實政治中持久的發揮力量。正如特萊伯所說的“關于司法審查的合法性的各種論點最終是超越憲法的,這些論點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哲學的和歷史的。”[8]
【注釋】
程梧:《馬伯里訴麥迪遜》,《外國法議評》1994年第3期。
徐炳:《美國司法審查的起源——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述評》,《外國法議評》1995年第1期。
同上。
葉小兵:《細節的重要》,《歷史教學》2015年第9期。
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北京:商務印務館,1982年,第392頁。
同[2]。
Gibsons dissent in Eokin V·ruab,12s,and R.330(Pa,1825)
Laurence Tribe.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M].The Foundation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