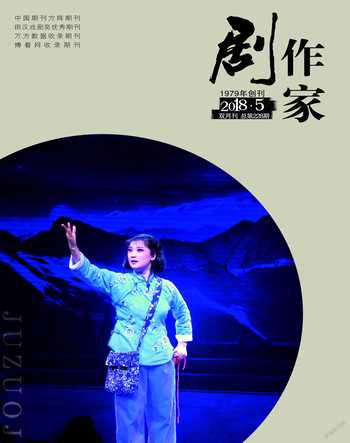阿爾托的遺產:一場丟掉文字拐杖的意象探尋
桂菡
《親愛的我們》開演前一天,劇院方在其官方微信平臺推送了一條字幕說明,告知觀眾演出期間將無字幕播放。因劇中對白采用意大利語,字幕缺失基本會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觀眾聽不懂臺上說的是什么。不少觀眾對此表示不解,但無疑卡斯特魯奇及其團隊是為了使觀眾將注意力集中于舞臺,有意削減文字類語言在戲劇作品中的作用。在筆者看來,這一舉動甚至頗有些幫助作品擺脫被文字支配的意味。
文藝復興以來劇作依賴臺詞、劇情靠角色間對話向前推進已成戲劇狀態,戲劇同文學關系日益緊密,觀眾也習慣了借助語言文字來理解作品。20世紀80年代,當“戲劇學”這一概念提出時,戲劇在絕大程度上依舊被認作文學的分支。甚至到了當下,不少觀眾進入劇院看的依舊是故事。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戲劇藝術賴以支撐的拐杖,那么《親愛的我們》顯然是將這把“拐”丟到了一邊,向使用既定語匯表情達意的傳統戲劇發起了挑戰。
卡斯特魯奇的戲劇難免會讓人聯想到法國戲劇理論家安托南·阿爾托。阿爾托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殘酷戲劇理論,因其理念過于顛覆且難付諸實踐,直到30年后才逐漸為戲劇界所接受。卡斯特魯奇的戲劇常被批評界冠以“殘酷”之名,無論是從驚世駭俗的表現手法還是震撼刺激的演出效果來看,殘酷戲劇理論主張在卡斯特魯奇的作品中確實可見一斑,阿爾托可謂后繼有人。在《親愛的我們》中,演員在眾目睽睽之下三次拉屎,屎漿不僅沾滿了白色睡衣、白色地板,還不時滴滴答答地順著演員大腿根部與家具滑落。怪不得在該戲開演前廣播特意提醒觀眾:演出可能引起不適,若接受不了,可從劇場側門離開。
除了強調作品給人以感官刺激,阿爾托對后世戲劇做出的最大貢獻應在于其對文字在戲劇中的地位做了顛覆性調整并擴展了戲劇語言的范疇。在《親愛的我們》中對語言的運用也是讓筆者感觸最深。該劇演出期間大量使用圖像、音響、燈光等非語言元素,對白在其中的比重相較于在傳統戲劇中明顯降低,那份字幕說明大概可以被視為作品在語言層面反叛的勝利號角。
當科學在19世紀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后,理性成為社會的主導,似乎一切都有原理可循,理智與情感也被人們冠以字句形式加以表達,再通過解剖字句被加以分析。然而無論字句多么繁多,語言多么精準,總有一些情緒意識是無法言說的。“當‘非語言方面的情緒和感官被強迫塞入語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之中,將流失掉許多情感的精髓。這些被沖刷去的,才是最可貴的。”[1]阿爾托認為戲劇最大的功效不在于影響人的理智而是震撼觀眾的感官,作為理性工具用來傳達意識的語言文字理應從戲劇寶座上下來。他在《劇場及其復象》一書中呼吁──戲劇不應依賴已僵化的劇本,更不可屈從于文本之下。說到底,文字語言只是戲劇諸多元素之一,對于戲劇藝術整體它只可輔佐,無權主導。卡斯特魯奇也表示過同樣的看法。2017年《俄狄浦斯》到訪中國時他接受了相關的媒體采訪,在談及文本問題時曾表示:“如果你問我,在我的作品里,文本和意象,以及其他戲劇元素之間,是不是會排出一個先后重要的順序,我想說我沒有。”[2]
前面已有所提及,《親愛的我們》一劇中文本力量微乎其微。該劇時長六十分鐘,前后分為兩個段落。前一個段落呈現的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兒子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年邁父親的場景,全劇僅有的對白即出現在這一段落中,導演安排角色之間進行溝通。
子 爸,沒事吧?
子 爸,沒事吧?
父 ……
子 今天早上還好嗎?睡得好嗎? 看到什么好東西了嗎?電視上播了什么?
父 ……動……動……動物。
子 太好了!紀錄片是我的最愛。 是什么動物?企鵝?好吧,我已經準備了你的糖果……
子 真是一團糟!嗯……
嗯……嗯……
子 那好吧,爸,我出發了,一會 兒見。怎么了,感覺不太好?
父 不,只是……
子 你拉了嗎?你拉了嗎?嘿,沒 問 題。如果你拉了,我會幫你換尿布。
父 ……[3]
上述對話空有溝通的形式人,人物雖有發聲實則卻處在失語狀態中。兒子一直在講話,但與其說他是在試圖同父親溝通不如說他是在自言自語;父親的臺詞非常少,更像是斷斷續續的囈語。二人對話達不到交流的作用,既不能表情也不能達意,字詞在這里失去了語法含義,僅僅發揮了聲音固有的音效功能。無論是對于臺上角色還是臺下原本就聽不懂意大利語的觀眾,與其說他們在接收劇作傳遞的確切文本含義,不如說是在接聽聲音的本身。該劇第二個段落干脆完全消除了文本,十個天真的孩童依次走上舞臺向舞臺后方巨大的耶穌肖像投擲手榴彈,整個過程中無論是孩子還是上一段落中滯留在舞臺右側的年邁父親,均緘默無言。
戲劇不僅要作用于觀眾的心智,更需要作用于他們的感官,而文本所傳達的永遠是固定、僵死的理念類信息。所以要將文本拉下“戲劇陛下”的寶座,阻斷觀眾借助文字的拐杖去挖掘作品所謂的思想內涵,要調動起觀者的感官,使之達到感性活躍帶。要擺脫文字掌控,戲劇應使用一種與“姿態、符號、動作、物體的需要互相結合而成的”[4]泛性語言。在《親愛的我們》第二個段落中,孩童向耶穌肖像每投擲一枚手榴彈都會引發一聲巨大轟鳴,當孩童離場后耶穌肖像被從背后撕扯開來,每一下撕扯產生的聲音都被上千倍放大,直逼觀眾耳膜。與此同時燈光縈繞,襲擊著觀眾的感官,其力量隱藏在劇場空間內。這些聲音沒有作用于觀眾的理性,而是強烈刺激其感官,沒有文字的傳譯功能但依舊可以傳遞信息。卡斯特魯奇說:“我的很多作品,有純意象的,有純文本的,有純燈光的,也有燈光和語言相結合的和燈光和意象相結合的。它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你甚至可以把燈光理解成一種文本,把文本理解成一種燈光。舞臺上的各種元素都是可以相互轉換的。”燈光、文本、服飾、音響以及它們彼此結合的產物正是阿爾托所提倡的新型語言。2013年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戲劇節上,卡斯特魯奇獲得“金獅終身成就獎”,以此表彰其“創造一種融合戲劇、音樂以及造型藝術的戲劇語言的能力”。
這種新型語言的一大體現是舞臺意象。
阿爾托曾對意象加以闡釋:它是建立在符號而非文字之上的;它存在于舞臺空間,是一種在空間運作的動作的語言;它不可通過字詞掌握,浮現在四肢、空氣以及一些叫喊、色彩和動作之間。[5]《親愛的我們》第二個段落便是由意象組成。舞臺上懸掛著的巨幅耶穌肖像首先就奠定了一種宗教式的神圣與神秘感,十個孩童持續不斷地朝肖像投擲玩具手榴彈的行為也有特定的含義。在該劇的導演手記中,卡斯特魯奇對這一幕做了詳細說明:“這個行為的意義可以回溯至耶穌受難,此舉并非是對耶穌像不敬,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借助純真的孩童的手完成的以向圣像扔擲玩具武器的‘受難行為再一次去喚醒和贖罪的祝禱。”[6]耶穌肖像也有特定含義:“耶穌直視觀者的雙眼中帶有強大的戲劇性的審問眼神,對視所產生的反問讓我們看到的這一幅圣像也化身成一幅人像、一個人甚至觀者自己。這幅名為‘上帝之子的作品,卻透露著屬于人類的、普通觀者的眼神。所以我相信,從這一班孩童身上做出的看似暴力的行為瞬時變成了祈禱者的呼喊。”[7]這場戲充滿肢體與聲音上的張力,觀眾感受到的是一種意識狀態的具象外顯,流溢在空間中的生命能量直接沖擊、壓迫、滲入觀眾的潛意識中。投擲與撕裂的過程是一場儀式的洗禮,觀眾通過戲劇這一中介感受到形而上的力量,看到美的逝去、終結的神秘。
意象使戲劇語言從扁平化轉為立體化,從作用于人的理性心智轉為作用于人的直接感官。但意象遠比文字難以理解,它從來不會直接暴露本質,而是需要觀眾憑借直覺去感知且不設有標準答案。卡斯特魯奇被媒體稱為意象派戲劇導演,出身繪畫專業的教育背景使其戲劇作品趨向于充滿視覺感。他非常擅長利用圖像、聲音、燈光、音響、舞臺造型,通過造型藝術的形態將挖掘自神話或宗教的故事本質加以呈現。由于熱衷于讓戲劇回歸原始與神秘,借鑒人類的集體無意識去觸碰理智無法掌握的神話、夢境、脆弱、神秘等非理性內在特質,已經習慣于借助臺詞理解戲劇的觀眾感到想要理解卡斯特魯奇的戲難上加難。倘若贈這些觀眾予觀劇忠告,只需一點——卡斯特魯奇的作品并非為人講述,而是帶人去感受,感受比理解更為重要。
蘇珊·桑塔格將阿爾托作為西方當代戲劇的分界線,阿爾托開啟了戲劇新的紀元;而卡斯特魯奇則是在阿爾托抽象的理論之下創造出一種具體的新型戲劇呈現方式。在前后戲劇家的努力下,我們看到的戲劇藝術不再是一個平面的畫面,而是一個立體的印象。劇場輸送給觀眾的不再局限于理性心智層面,還有一種由意象而來的感官體驗。就像是《親愛的我們》,它丟掉了傳統戲劇敘事故事的文字拐杖,讓觀眾身處劇場,在導演的帶領下展開一場探尋,通過繪畫、色彩、聲音、動作合成的意象,重新感受、發覺、呼吸所在的空間。
參考文獻:
[1]朱靜美:《集體即興創作:約瑟夫·柴金與開放劇場》,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11,第40頁
[2]《西方最當紅的戲劇導演卡斯特魯奇:戲劇最重要的是觀眾》,來源自澎湃新聞網站,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32908
[3] [6][7] 來源自中國大戲院官方微信平臺推送《關于〈親愛的我們〉的字幕說明》
[4]翁托南·阿鐸著,劉俐譯:《劇場及其復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第132頁
[5]翁托南·阿鐸著,劉俐譯:《劇場及其復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第69頁
責任編輯 姜藝藝